《四次》剧情介绍
这是一个卡拉布里亚岛的小村子,依山傍海,从山麓间,你可以看到远处的伊奥尼亚海。这是一个好似时间停止的地方,这里的石头有权改变事件的发生,而山羊们则会停下来思考天空的由来。 这里住着一个已经时日不多的老牧羊人,他病了,他坚信他找到了续命的良药,他从教堂的地板上收集灰尘,每晚就水喝下。 在一个羊圈里的一小片黑土地上,一只山羊生下了一只小白山羊,生命最初的不适只持续了一小段时间,它的眼睛立刻便睁开了,它的蹄子已经可以支撑身体的重量。整个村子的生活都被这个新生命的到来而充满了希望。小羊在逐渐成长,它变得强壮起来,开始玩耍。 一次疏忽,它独自离开了在休息的羊群抛开,它在厚厚的植被中迷失了方向,直到精疲力尽,在一株雄伟的杉树下歇脚。 这棵巨大的树随着山间的微风摇摆。时间流逝,季节快速地更替,这棵巨大的杉树失去了枝叶摇摆的声音,取而代之的,是机械的轰鸣。 杉树倒在...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戴维斯夫人漆黑雄风千分之一怪兽湖伴郎食锈末世录仙岩女高侦探团无敌当家5御天无常传山里山外狗镇噪乐江湖疑雾公堂绝夜逢生第二季你迟到的许多年寻梦环游记风之画员战寇带我去个好地方十字追杀令3永远-永远我们村的指导员御饭团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杜鹃山无主之城晴雅集轮回派对第二季斗室最不情愿的转换
《四次》长篇影评
1 ) 看轻死亡,热爱生活
意义深远的电影!
这电影告诉我们能不要再害怕死亡,热爱生活!
影评反映了公元6世纪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的灵魂不朽、灵魂轮回的思想!
和我国的佛教里说的:死亡,只是此期生命形式的消失,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却离不开轮回不息的六道!
毕达哥拉斯灵魂不朽,在四种生命形态动物、植物、矿物和人中循环重生。
对很多人来说,在年轻时就经历最亲的人离世是很痛苦的,对死亡异常恐惧,害怕亲人一个个都离自己而去!
不管灵魂轮回是不是真,但是如果走不出亲人离世的阴影可以选择去相信,去自我安慰!
2 ) 灵魂的四次旅程
带着恐惧和矛盾的心看完的一部电影。
它不是一部电影,也不是一种表达和告诉,因为没有表达和告诉。
生命有四次的旅程,平静的,平凡的,平静的,平凡的。
故事是隐喻,平静和平凡是本质。
活着就是一种方式的活着,生命没有意义,生命就是一种意义。
灵魂真实地存在,在宇宙中,在自然界中,在生命中。
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换,高空上白云的飘浮,大树和万物生灵一样静默。
3 ) 生命轮回
四次中,弗兰马汀诺在意大利卡布里亚岛的一个小村庄演绎记录了毕达哥拉斯的生命四循环。
一个行将死亡的老牧羊人,一颗大树,一只小羊羔,一堆木炭,构成了简单,质朴,却充满哲思的故事元素。
弗兰马汀诺的镜头就像上帝视角,俯瞰,审视,观察自然万物。
着实安静,大量的固定机位远景,少量的特写镜头,安静到稍微没有耐心就看瞌睡了。
但就是这么安静的镜头,让画面在安静中充满灵性,充满生命的喧闹,充满人情味。
每一帧都像诗,每一帧都像意大利油画般唯美。
如老牧羊人虚倒小林荫道旁,牧羊犬折回然在老人旁边胆怯而又谨慎的望着老人。
除了长镜头外,弗兰马汀诺调度动物场面真是神一般的存在。
第二个故事中,动物表演真自然,全部都是演技派。
小山羊特写镜头在那一瞬间让人感动,而小羊走失的那段着实让人心碎。
在剧情及画面语言处理上,弗兰马汀诺别有用心加入了一个幽默段子,很有趣味,让本片的主题不那么沉重。
比如牧羊犬拦住想去玩的小孩的路,对着一阵孩子一阵叫,之后又叼走了垫卡车轮的东西,导致卡车撞坏了羊圈的栅栏;山羊跳上牧羊人的桌子掀翻了桌子上的篮子。
全片中,人类演员没有台词,表演那么淳朴自然。
从叙事风格上看,四次更像一部纪录片,有着天地玄黄般的镜头语言,人文,安静而又充满感染力和冲击力,也有着BBC的那种敏锐而独特的视角。
无声,却更有声。
另外,片子没有配乐,如果加了配乐,觉得都会破坏了画面的安静美。
我们本是生态系统循环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我们从自然中来,最终要回到自然中去。
我们无法超越自然生态系统,即便超越了,最终承受结果的还是我们。
我们所能做的接受自己所在的位置,与自然和谐共处。
4 ) 乱语《四次》(1)——消失的摄影机
这或许是电影史上唯一一部“没有”摄影机的电影,同时也可以看成第一部,如果我们相信这位名叫弗兰马汀诺(甚至还不怎么名见经传)的意大利导演仍然饱有旺盛的创造力,同时具有改写电影史的野心。
电影史从未缺少企图让摄影机消失的导演,却没有一位曾经真正做到。
比如在费里尼的电影中,方法是不断地加重影像的繁杂度,运用无从捉摸的镜头处理,用巴洛克式影像不断轰击观众感官以达到崩溃效果,观众来不及意识到摄影机存在便被影像裹挟而去。
但这是一种障眼法,摄影机只是在观影中逃脱了意识,却没有被真正消灭。
又比如小津安二郎,独辟蹊径地使用低角度摄影机位,以此来消除导演意识的介入,以一个全知的视角模拟超脱者的视角,但其固定镜头间的剪辑手法依然有着明显“切”痕。
究其原因,是因为摄影机永远都不会“被消失”,而只会“自我消失”。
这就如同欲望,永远无法借由压抑来将其消灭,只能经由我们对欲望的彻底觉知(认清了所有的欲望组成),才会自行消失。
弗兰马汀诺或许是第一位认识到此点的导演,并将这一理念完美落实,从而创造出这部名叫《四次》的杰作。
我们应当感慨是一位意大利人发现了这份原本属于东方世界的秘密,同时作为后人也应当汗颜,我们如此彻底地将其忽视恰恰是因为它深刻地裹挟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因为一切都太过熟悉了。
上个世纪,一位来自印度的圣人将这份遗产从远古带回现代,这位超然的觉知者最振聋发聩的话语之一是“观察者即被观察者”,弗兰马汀诺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在电影中将这一观念完美契行,从而让摄影机自行消失。
于是,我们可以来谈谈《四次》是如何做到将摄影机消失。
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就是电影里仅仅出现的两处主观镜头,它们的主体都不是人,而是羊。
第一处主观镜头由两个画面组成:前一画面是一只羊仰望天空,紧接着就是飘着云彩的蓝天。
为什么全片只有羊的主观镜头?
这值得深思;为什么电影从头到尾只出现老人的正脸特写?
同样值得深思。
我们可以作出的解释如下:主观镜头一旦是人发出了,观众也就意识到一个观察者,即观众自己;但如果镜头是来自动物的视角,观众就不再有自己是观察者的意识,代入感自行消失。
这就是这部电影带予观众的奇妙观感:无法被以往任何观影经验所污染,它是纯粹、再生的:是自然万象自己叠印于胶片之上,像是浑然天成的上帝之作。
因而,摄影机不再模拟人的眼睛,而是动物的眼睛(羊),甚至可以看成是物质(碳)和一个不再有思维能力的老人(仅剩感知)。
对于动物来说,观察者这一词汇本身即不存在,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分离纯属基于人类的话语之谈。
只有当摄影机在模拟人(有观察能力的人)的眼睛之时,它才无法被消失,它时刻观察被观察者。
但是,一旦摄影机模拟动物(或物质)的观察,也就只有观察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浑然一体,无谈分离。
正是于这种非人类(更准确说,非人类经验)的观察视角中,人类所有的观察经验自行消失,所有观众都在观影中恍惚间唤回原初动物之本性,我们生成-动物,以一只动物的眼睛观察眼前展开的一切,这些景象不再能唤起我们于生活中积累下的经验——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在作身体的移动:换不起我们的同情;羊群的骚动:换不起我们驱赶的欲望等等——我们即是他们的一部分,观察者消失了,只有纯然的观察。
于是乎,电影成了对人类存在之前的原始窥视,那时一切都遵从着万物本性,在宇宙和谐奥秘中活动。
就是以这般简单又极端的手法,弗兰马汀诺创造性地让摄影机自行消失,从而创造出空间-影像的典范。
他的方法很简单:给予摄影机生命,让它全然地觉知。
于是乎,我们也就明白费里尼和小津安二郎失败的真正原因。
只有到弗兰马汀诺的手下,主客体间的界限被打破:只余观察,不再有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分离;只有电影,而不再有摄影机与被摄录画面的分离。
这两者本质为一,它们以绝然清澈的视角自现于这个世界。
注:“观察者即被观察者”,克里希那穆提的教诲之一。
照我个人理解的深意是:彻底全然的觉知可以把人类从时间的深渊中解救,人类内心所有的痛苦均可以归结为“我”,当时间不在,“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我”消失了,主体消失了,只客体留存,主体与客体融为一体,心理问题的产生与作用都在一个对象上,就好比一个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施在同一物体上,它不会有任何变化。
克里希那穆提的这句话可以终结全人类的痛苦,不是靠信仰,靠的是人类自性之光。
只可惜,到现在人类依然活在自我痛苦的深渊里,他没意识到这份痛苦的根本来源正是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作了分离。
5 ) 尘埃是不可能真正落定的
{1}没有语言,只有自然的声响米开朗基罗·弗兰马汀诺的电影《四次》,是一部超绝的“默片”:全然克制的沉默,全片没有语言。
如果只是无对白电影,那并不新鲜,《四次》的独特在于,它并不是简单地取消台词(进而费力地在剧情、表演、镜头、音乐上做强调,以使电影依靠强烈的形式感而成立),弗兰马汀诺从根本上取消了观众习惯的各种电影语言:散文般的日常场景的松弛排列取消了故事和戏剧冲突、非专业演员和动植物的自然出演取消了表演范式、自然光下的直白影像取消了人造光对摄影机的干预、只用自然声响和同期录音取消了配乐在抒情上的霸权。
尤其对白和音乐,在自然界的声音系统里,是极小的特例,只属于人类,在别处并不通用。
上帝以巴别塔[1]造成语言的不通,而弗兰马汀诺以沉默无言的方式将塔拆解:没有语言,只有自然的声响,人、羊、树、炭在生死轮替中相互关联,发出本能的声音(咳嗽和喘息,铃铛响和咩叫,风吹树叶声,木炭细碎的开裂声),只有从自然里发出的声响才是无差别的、通行的“语言”,而仅仅人类的语言,并不能满足电影的表达需求,因此要被略去。
摄影机也是“沉默的”——纪录片式的白描影像,绝大多数镜头为固定机位,几乎没有主观视角的介入。
抛弃了喧哗的、模式化的技法,弗兰马汀诺将摄影简化到极致,而电影也在此时停顿、呼吸,回到诞生之初——《四次》成为默片时代未曾发出的余响。
{2}物是平等的,物尽其用弗兰马汀诺建了一个毕达哥拉斯循环理论[2]的实例模型,以客观、自然的视角陈述了物物平等、平凡和平静的事实。
电影分为四个段落,以四次黑屏为标记,记述了死与生的替变:第一次(40min处):老牧羊人死去,骨灰盒被封存时,黑屏,接下来,是羊羔诞生。
第二次(59min处):小羊在杉树下因饥寒死去,黑屏,接下来,是杉树被伐为木材。
第三次(75min处):杉木被焚烧,黑屏,接下来,是形成木炭的过程。
第四次(84min、2min处):木炭被燃烧,成为烟,黑屏,黑屏,烟灰和尘埃也是老牧羊人用于治疗咳嗽和延续生命之物。
影片结尾和开头是重复的、闭合的,在形式上也完成了四次一轮的循环。
四个段落记述的对象分别是牧羊人、羊、树和木炭,四者皆物,物与物是相互影响的,它们以“关系”作为存在的证据,每一物都有自己的时间线,每条线又关系着别的物,物尽其用,时间交叠,这一切关系的总和就构成自然。
除了四个主线上明显的时间流和相互关系外,电影在细节上也严谨地对待每一个出现的物体,这里举两个例子(由于这是一部几无剧情的电影,所以你丝毫不用担心剧透,预知的细节会让你更好的体会它):【砖块】牧羊人在羊圈旁拾起砖块,带回家用来压盛蜗牛的铝锅锅盖;回家时发现砖落,压不住锅盖,就把它扔出窗外;受难日仪式的演员把车停在路边,捡起这砖用来卡住车轮;游行中掉队的小孩被牧羊犬阻住,扔石子支开它,它衔起砖;车滑走撞毁羊圈,羊涌入房间,参与了牧羊人死去的过程。
【尘埃】木炭燃烧后,灰烬参与形成了教堂里的尘埃;修女清扫收集尘埃,作为药物与牧羊人交换羊奶;牧羊人在草地排便时遗落尘埃包,被蚂蚁搬走(尘埃遗失是牧羊人之死的一个缘由);蚂蚁在牧羊人的脸上爬;蚂蚁也在树皮上爬,这棵树是羊死去之处、将被砍伐并制成木炭;{3}尘埃是不可能真正落定的村民们路过牧羊人的房子,在举行耶稣受难日的游行,是对死亡的纪念。
牧羊人在游行进行之后的片刻死去,是对死亡的临摹、再现。
不久之后,人们还将庆祝复活节,还会有新的仪式和游行,但牧羊人不会以宗教的传说形式复活,弗兰马汀诺也不会临摹奇迹,他用电影给出的,是哲学上和自然上的重生方式:物(质)的转换和流变。
我们的生活,由一些庆生与祭死的仪式构成意义,死亡意味着结束,诞生意味着开始,但在自然中,它们不值得被专门提起,因为它们只是生命流转、时间更替的进程中的一瞬,和别的每一瞬并无多大不同。
一个死或一个生,都是沉默、平凡的事,是不可能作为生活结论的。
如同尘埃是不可能真正落定的。
--[1]《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巴别塔,希望能通往天堂,上帝便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之不能沟通,人类因此失败。
[2]毕达哥拉斯认为灵魂不朽,并在人、动物、植物和矿物的形态之间循环。
6 ) Perspectives on Michelangelo Frammartino's Le Quattro Volte (2010) and Laura McMahon's 'Animal Agency in Le Quattro Volte
Directed by Michelangelo Frammartino and filmed in his hometown in southern Italy, Le Quattro Volte (2010) presents a meditative exploration of the cyclical nature of life. With a runtime of 88 minutes and devoid of dialogue, the film seamlessly merges the sounds of humans and animals into the broader soundscape of nature, illustra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human to animal, to plant, and finally to inanimate charcoal.The film’s perspective is innovative, employing experimental cinematography and conceptual boldness. By minimizing dialogue, blending human and natural sounds, and utilizing distant camera angles that strip humans of their subjectivity, Frammartino presents all forms of life—the elderly man, the goat, the pine tree, the charcoal, and even the smoke rising from the burnt wood—with equal weight. This four-stage structure is remarkably comprehensive, encapsulating intelligence, degrees of vitality,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birth to death. While offering a fresh perspective on life, the film also captures the environment and landscape of an Italian village of its time, creating an atmosphere that is tranquil yet melancholic, silent yet profoundly moving.After reading Laura McMahon’s critique, Animal Agency in Le Quattro Volte, I developed new reflections on the film.McMahon states, “If I film from one metre off the ground, I’m taking a viewpoint which is no longer human but mechanical—the viewpoint of the camera. It’s like trying to see the world through the eyes of someone who is not capable of making distinctions, of discriminating between things—who can’t therefore establish hierarchies.” I agree that this cinematographic approach is a compelling and effective means of decentering the human perspective. However, the existence of the camera itself is inherently anthropocentric—created for human use, controlled by human hands, and serving human purposes, whether as a tool for commemoration or artistic expression. Animals do not share this need; a goat cannot operate a camera. While we may strive to overcome ingrained hierarchies, certain barriers remain inevitable, shaped by a fundamentally subjective framework. Yet, should these barriers be deemed unbreakable? This question reminds me of interspecies interactions such as pharmaceuticals derived from animals, genetic exchanges within food chains, and even the concept of the cyborg—beings that merge organic and biomechatronic components. Perhaps, as Natasha Myers’ suggestion “Dilate Your Morphological Imaginary", we should expand our sensory perception, attempting to embody other life forms—to become, for instance, a blade of grass and experience the world through its form.McMahon also observes, “This effect of auditory merger is suggested further when the goatherd starts wearing a bell like the goats; during these sequences, human movement sounds like animal movement.” While I find this moment to be a wise artistic choice, it reads more as performance art than a genuine act of transformation. Beyond our analytical lens, such an action would have little practical impact in real life. If we were to encounter a person wearing a goat’s bell, we might perceive them as mentally unwell or as engaging in performance art rather than contemplating the implications of sound or drawing connections to animal existence. This reveals how perception is shaped not only by sensory input but also by societal conventions, which often lead to immediate bias rather than introspective reflection.Frammartino stated, “I wanted to film animals because it was something that I could not control.” While this is an admirable intention, the nature of filmmaking itself renders such control unavoidable. The long take in which a dog dislodges a stone, causing a truck to crash into the goat enclosure, is a meticulously choreographed sequence that required significant production effort. The dog’s performance, rather than being purely spontaneous, becomes part of what could be termed “entertainment capital”—a commodified display rather than an entirely organic event. Cinema is inherently shaped by direction, rehearsal, and control. Framing choices, camera technology, and shot compositions are deliberate and intensely subjective. The placement of landscapes and objects, the orchestration of movement—these all preclude true preservation of nature in its rawest form. Moreover, randomness, when captured on film, does not escape human intention; instead, it serves the filmmaker’s purpose, reinforcing rather than dismantling the director’s vision.Regarding the theme of “Interspecies Politics: How Film Redefines the Value of Life,” my perspective is as follows: If life’s value must be defined, then non-human life is immediately devalued, for it becomes an object rather than a participant in this definitional process. Definition itself is a human construct that does not alter the fundamental reality of life or its conditions.I acknowledge that my critique may be overly harsh, as it stems from an idealized pursuit of definitions. The challenge of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made constructs and uncontrollable, non-communicative life forms parallels the question of distinguishing wilderness from civilization. Civilization is human-made, but humans are animals—so is an environment shaped by animals wilderness or civilization?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artificiality of cinema may not necessarily be a flaw; rather, it provides a medium through which collective human emotions and ideas can be expressed. Le Quattro Volte offers profound philosophical insights, and it need not be scrutinized too harshly.
7 ) 这是个宗教与哲学、艺术与文学的结合体艺术品
意大利有基督天主教 《四次》,韩国有金基德导演的佛教《春夏秋冬又一春》,希望这个时代还有这样的大师,否则生活太无聊了,这是个美味的精神食粮,影片里的树、羊、车、人群、狗、小孩、送货人 等 角色都是电影语言,需要观众和知音们思考,越思考越。。。。。
回味无穷。。。。。。。。。。。。。。。。。。。。。。。。。。。。。。。。。。。。。。。。。。。。。。。。。。。。。。。。。。。。。。。。。。。。。。。。。。。。。。。。。。。。。。。。。。。。。。。。。。。。。。。。。。。。。。。
总之就是好看,嘿嘿
8 ) 灵魂不朽,轮回不止
无对白,全片采用自然音效和固定机位,成就了这部用长镜头堆砌起来的电影,一切浑然天成。
这是一部让我觉得震撼而又有点害怕的电影。
看完全片以后才能理解为什么电影的名字叫做《四次》。
这两个字是再明显不过的提示,绝对有“关键情节透漏”之嫌。
如果题目在结尾才出现,那样的顿悟未免来得太慢,唯有在片头出现,才让让观者带着一种逐渐脱离了困顿的释然走向结局,逐渐体会到宿命的压迫感。
很难不对这部貌似有着“上帝视角”的电影肃然起敬。
要我说,这绝对是关于轮回的电影。
牧羊老人日复一日过着最平凡最平静的生活,如果不是羊跑出了羊圈并有几只聚集在老人床榻前,村民不会发现老人已经死在自己的家中。
老人生前悉心照料着羊群,死后他投胎成为一只小羊羔。
小羊羔从母羊腹中一下子就来到了地上,它挣扎着去适应(或者说重新适应)地面上的生活。
此后的某天,小羊羔在树林里迷了路,最后死在一棵树下,尸体被大雪掩埋。
接下来,冬去春来,人们砍伐了一棵树放到村中央作为某种节日的庆祝仪式。
庆典给人们带来了空前的欢乐,节日过后,人们把树砍倒,之后把树运到村外,和其他的树一并烧制成乌黑的木炭。
影片的最后,卡车拉着木炭回到村内,车上的男人把木炭分给各家各户。
电影里所呈现的四段不同的生命经历,正是同一个灵魂在不同的生命形态中的四段故事。
我个人特别喜欢电影里面的三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是出现了两次的蚂蚁。
电影里的蚂蚁似乎相当于某种信号,或者说是使者,两次出现均给两种生命形态之间的转换带来了相当大的转折。
蚂蚁第一次出现是在老人的面部,由额头爬到老人鼻头,再爬到老人眉头。
随后老人起身离去,镜头对准一群正在准备搬走老人的“药”的蚂蚁。
这时老人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坐在那片他熟悉的草地上牧羊。
当天晚上,老人的生命终结,第一次轮回即将到来。
蚂蚁第二次出现是在死去的小羊羔所依偎的那棵树的树干上,蚂蚁由上而下爬着。
这一次,生命由运动走向静止,由最开始的依附在人和动物上的生命,变为依附在植物上的生命。
第二个细节是焚烧。
老人死后,村民们用火葬的方式处理老人的尸体,由此第一次轮回真正开始。
第三段故事中树木即将转变为木炭,也是通过用火焚烧的方式才能完成转变。
而第一次火葬有一个镜头是从老人所躺的内部向外看去,门被重重关上,画面由明亮干脆地变为黑暗。
第二次焚烧也有一个镜头是由堆放的木材向外看去,能看到眼前逐渐被刚刚搭上来的木材所遮挡,画面再次由明亮变为黑暗。
从前后两次焚烧也能看出两个不同生命形态之间的联系。
第三个细节是轮回。
这里所提到的轮回不仅仅是四次生命的轮回,也是电影开头和结尾相接所形成的环状结构。
两次焚烧也是情节的关键点,第一次焚烧象征轮回开始,但第二次焚烧并不是象征轮回的终结,相反,轮回似乎永无终结。
由第二次焚烧开始,随着卡车运回村庄,也使那一个灵魂回到故土,故事重新开始,也可以看做是回到开头。
无论是哪种观点,整个电影的头和尾都正式相接起来,形成一个无懈可击的圆环。
有意思的是导演对待宗教的态度似乎模糊不明。
老人一开始对教堂里的香灰可以治病这一点坚信不疑,直到有一天他发现病情并没有好转,想去教堂寻求答案,然而教堂的门却没有向他敞开。
之后一包香灰被老人遗弃在草地上,随即香灰被蚂蚁搬走,而老人也在当天晚上悄无声息地死去。
这似乎暗示着信仰的土崩瓦解。
而老人的尸体之所以被发现是由于一位扮成虔诚的教徒的男子无意中把车拉动、车冲向羊圈、羊逃出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然而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街上正有列队在进行某种宗教仪式。
老人尸体被发现后,神父为其主持了简单的葬礼。
这一些事件,是否是导演的刻意安排?
(对宗教了解太少,如有理解错误请谅解。
)电影结尾最后一个镜头几乎和老人第一次从教堂回家所用的镜头一模一样,或许导演在暗示着,他所认为的轮回只不过是不断重新出发,最终都会得到回归。
业余水平 见笑见笑
9 ) 生命的力量,灵魂的轮回,命运的循环
村子里的石堆在冒烟,牧羊的老人在干咳,他去教堂里收集灰尘每天喝下想让自己恢复生命力。
可老人还是逃不过衰老,没起来的老人最后看到的是模糊中羊群占领了他的房间。
老人离去时一只小羊仔诞生了。
他长大,玩耍,然后在一次出游时掉了队迷了路,最终走到了一棵树下,冻死了。
那棵树茁壮成长,冬去春来,树被砍倒成了村民庆祝节日的道具,狂欢过后,高耸的树被运到了工厂分解成木条,然后,成为了那冒烟的石堆成为了炭火,炭回到了老人的房子,一切成了一圈。
几个月前看了这个导演的新片《洞》,当时的评论那部妙片说的就是只靠视觉也能讲好一个故事。
今天再次打开十几年前的导演的作品,依然感叹这句话的同时也能看到很多变化与不同。
【无台词无配乐固定机位】依然是该导演的特点,但《四次》要讲述的是飘渺的灵魂经历的四次游荡,从人到羊(动物)到树再到碳(矿物),这在哲学中意味着灵魂不朽不断循环。
也因此相比起新作品,镜头的变化要多得多,依然在每一个对象的表述上有重复镜头,但整个故事的讲述上变化多了,要比《洞》好接受很多,也有趣很多。
特别是老人离开后的一切都让人激动,仿佛透过镜头我真的触碰到了那个虚无缥缈的灵魂,我看到了它在不同的生命体中的表达和感受,这是这部片子的影响所带给我的最妙的体验。
我特别喜欢这种灵魂不灭的观点,让我想起莫言老师的作品《生死疲劳》。
当灵魂附着在不同的生命中去观察和看待相同的世界和环境的时候所看到的事情和感受会是不同的,也因此能更加直观的去体会自然宇宙甚至灵魂的广阔与深度。
而这些都通过纯粹的影像和导演的镜头语言传递给了观众。
特别是我看到结尾的碳的时候,我很难描述我那一刻的心潮澎湃。
就故事开头的冒着浓烟的土堆一下子有了答案,电影用一个半小时在我的心头画了一个圆,在这里连接上了。
那种命运感和释然都让我长叹一声,然后大呼妙哇!
不管别人喜不喜欢,我要推荐这一部!
特别是相信命运的人一定要看!
10 ) 意大利版“隐入尘烟”……
最近国内一部《隐入尘烟》出其不意地成为话题之作,掀起一波波观影热潮,没想到早在 10 年前,意大利就有一部类似的作品,其影片的主人公最后更化作一缕青烟,真真正正地“隐入尘烟”……米开朗基罗·弗兰马汀诺在处女作长片《礼物》后,再次回到了同一个意大利南部小村镇,继续用独特的美学角度观察这个地区的人文自然风光,造就出他令人惊叹的代表作《四次》。
这部当年入选戛纳“导演双周”的作品是导演挑战“现代默片”的又一次尝试。
同样是现实主义的记录视角,从一个年老的牧羊人开始讲述,他每天带着牧羊犬去放羊,也去教堂领取咳嗽的药方,直至某一天再也起不了床。
然后,情节奇怪地转向一头刚出生的小羊羔,眼看活泼好动的羊羔日渐长大,有一天没跟上放牧的队伍,被孤独地遗留在山林中,最终它找到一棵参天大树作为落脚处。
此后,影片再次转移视角,将这棵参天大树作为观察对象,讲述当地人如何砍伐树木作为一种节庆祭祀仪式。
祭祀仪式完成后,人们将树砍伐成木材,运往偏僻的郊外;工人们用古老原始的方法烧毁木材获取木炭,最终将木炭送回到小村庄,卖给当地人作为燃料。
这表面上是四段毫不相关的纪录素材,导演客观记录下这个村落的日常生活:人的生老病死,动物牲口的成长,以及树木的各种实际用途。
当作是意大利南方小镇的纪录片来看也许乏味了些,然而细心观察的话,渐渐发现这四段素材的内在有着一种生命的延续性。
这种跨越了人、动物和植物形态的延续感,难免不叫人叹为观止。
导演运用超然锐利的眼光,捕捉到生命在四种形态里的轮回变化,不仅让人沉思人与自然的共存关系,还悄然在这些思考中融入些许哲学的意味。
弗兰马汀诺暗示了生命在这个南方小村落里是生生不息的,尽管人类在老去死亡,却会以其他的不同形态“复活”,再次延续其生命力,周而复始地循环下去。
影片花去最多的篇幅来描写老牧羊人的生活情节,然而影片主旨显然是要打破以人为中心的论调,这也许是从导演的处女作《礼物》中延伸过来。
在处女作中,承受现代与科技的冲击,年轻人为了谋生发展逐渐离开家乡,只留下一座死气沉沉的空城。
《四次》中依然可见人口稀少的村镇,却摒弃了死气沉沉的意味,人与动植物、大自然已悄然融为一体,生命力并不因人的消亡而流逝,只不过是转换了另一种存在形式而绵延下去。
这种哲学思考给影片增添上一种玄妙的氛围,一种超脱的诗意,一种东方的思维价值观。
导演的视角引领观众去重新观看稀松平常的生活细节,在现实主义中发掘出富于象征色彩与超现实主义的高光时刻,令我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全新的感悟和理解。
导演沿用《礼物》中混合纪录与虚构的方式,采用非职业演员营造朴实的生活质感,当地不少村民自然成为了剧中角色。
相比起真人演员,这部作品里动物的表演更加出色,绝对要归功于动物训导员与动物声音的捕捉,在一连串意外的的场景里炮制出忍俊不禁的幽默效果,比如小羊羔们一起玩耍,或者是牧羊犬搬走石头让车子撞坏羊圈。
不论是动物出其不意的行为,还是人与动物对视的时刻,都充分展现了动物也具有了灵性的一面。
得益于题材的关系,空镜头在此运用得行云流水而无比贴切,例如参天大树在不同季节背景的画面里矗立和轻轻摇曳暗示着时光的流逝。
而相似镜头画面的反复重现更是凸显生命轮回的意味,比如一开头工人们在烧木材的情景,牧羊人家中装满蜗牛的小锅,货车经过小村镇路口售卖木炭给村民的镜头。
这些充满暗示的镜头实则具有叙事上的深思熟虑,由此,立刻与传统的纪录片拉开了距离,大大提升了这个题材的表现力。
不论你是从地方人物志的角度,还是当作超现实的科幻故事来看,这部作品都能给予你意想不到的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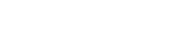






























6.5。死亡与新生。
无聊的人,狗,羊,木头还有那无聊的烟火。
好看的电影绝不沉闷,不想对生命,轮回作何评价。唯独最有感触的是,老人日复一日的放羊,回家,黑夜,再次出门。。。一大群的牛羊当然意味着财富,可是富有的主人生活和陪伴他终日的牛羊又有什么区别。为财富所累,为生活所累,是不是我也就是那羊群里的一只
三星半。自然系的电影,且未经任何雕琢,以纪录的方式表达一个天地万物周而复始的自然情节,我很喜欢小羊的段落,原始的笨拙的可爱,这部电影区别于那些商业片,这个世上最真实的东西,电影死了,他们还在,所以可以通过电影这样的媒介给孩子们观看,地球生命本身的样子,没有剪辑,没有调色,没有失真的灯光,要发现,而不是被迫注视。
没有看出回环,倒是觉得尘埃落定,灰飞烟灭
我用88分钟看了一场4×100的接力,起点即终点,而生命则是那根接力棒。声音很棒
关于生命形态与轮回的电影,安静内敛,很多细节出彩。看完顿增对生命的敬畏。
我只覺得,現如今我得是多無聊和多無所事事,才能夠心平氣和地把這部電影好好的看完呢?
从开始的明朗宁静到最后的难言的诗意。垂暮老人(搬演基督)、迷途羔羊、庆典之树、木炭之烟。
天地不仁万物刍狗嘛
熵增不可逆。
太闷,不推荐
对不起艺术我睡着了
万物,生生不息。如果万物皆有灵,真的会在一种状态消逝后转变成各种状态的万物呢?
牧羊人-小羊羔-松柏-黑碳,四次的更迭亦是宇宙中永恒的不变。无需对白,纯粹影像即可展示生命轮回。到头来,一切都会烟飞云散
能看下去,但并未被打动
真正“隐入尘烟”的故事。同样是现代默片的形式,留给观众广阔的想象空间。当作是意大利南方小镇的四段记录短片来看也许乏味了些,不过有一股贯穿人、动物和植物内在的生命延续感,难免令人赞叹。四种形态的轮回变化,不仅轻易打破了自然界生物的固定界限,还悄然勾起些许哲学沉思的意味。
小白羊怎么从沟里出来的?
12.10.15.虽然闷。还是好看的。。
这样的科幻片少拍点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