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实验》热门推荐
《死亡实验》剧情介绍
失业不久的特拉维斯(阿德里安·布洛迪 Adrien Brody 饰)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招工启事,酬劳为两周14000美元。为此所吸引,特拉维斯欣然前往。原来这是某机构发起的实验,研究者宣称实验将在州立监狱进行,包括特拉维斯在内的26名参与者被分成狱警和囚 犯,狱警必须按照严格的规定来管理囚犯,不服从命令者将受到惩罚。原本只以为是一场有钱可拿的角色扮演游戏,但随着实验的进行,权力的意志渐渐得到体现,所有的人都似乎迷失在角色之中…… 本片根据2001年的德国影片《Das Experiment》改编,故事取材自马利奥·乔丹努(Mario Giordano)的小说《黑盒子》。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王子的本命是反派大小姐黄石第四季人面鱼:红衣小女孩外传老公万岁奥林匹克之环少侠快跑只要在一起八侍卫之英雄崛起白河夜船爱情开始的地方之遇见印第安夏日扎职3:义薄云天左轮手枪莉莉小巷人家蹂躏柏林一区公主小妹幽灵船顽石之拳八月:奥色治郡夺命剑之喋血江湖断魂枪声舞动布鲁克林宋慈之草人案宴会寻宝假期万圣节群魔无意背叛局中人第三季捍卫者
《死亡实验》长篇影评
1 ) 依旧坚信人性中的美好
骜宝大人说:影片探讨的是对人性的思考,善良无公害的人在权利获取后会怎样。
很明显有人扭曲了。
然后片子over。
最后,黑胖子演的不错。
(水宝补充:咳咳,注意种族歧视问题)推荐指数:★★★水宝大人说:死亡实验很明显是在探讨人性, Travis始终代表着正义和善良,即使在压迫到一定境界后,他奋起反抗,并且使用了暴力,但从头至尾他并没有取人性命的打算,仍旧保留了最后一丝的人性。
(主角光环啊,人性美好大前提的作用吧)在最后那场打斗中,他先扔掉了撬棍,徒手与Barris打斗。
后面Barris拿出了刀子,Travis夺到了餐刀,仍然扔掉了,只是用拳头狠狠得打了Barris一顿。
由始至终,Travis所代表的人性的美好并没有消失,这大概是这部片子唯一的安慰了吧。
再说Barris,我和骜宝看得时候都对这个角色咬牙切齿,一致认为这是个最扭曲的角色。
最开始出场,Barris是唯一一个西装革履的人,与人说话彬彬有礼,并且在面试中说到他有强烈的宗教信仰,看似是绝对的道德楷模。
但是随后在家里面妈妈对他的呼来喝去,说明他是不被尊重的,他所拥有的是非常没有地位的生活。
在那一声声“chickenshit”后,Barris的喜悦一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麻木,无奈,和深深的压抑后的平静。
在美国,没有男生会在成年后或者有工作后会继续与父母同住,这本身就是独立的代表。
在面试里面,提到他42岁还与母亲同住,是个彻头彻尾的mama boy,他的反应非常不自然,而我猜测这是挑中他作为狱警的原因。
常年的压抑生活,各种人生的不如意,都会在这个无道德,无法律的地方得到充分的发泄,最完美的展示何为人性的本源。
Barris在第一次品尝了权力的滋味后,第二次是他主动提出如何惩戒犯人。
随后他减掉了胡子,最后剃掉了头发,代表着一步步地摆脱了束缚在自己身上的枷锁,尽情地享受着权力带给自己的快感,这是在外面世界他所没有的,这也是为什么他是最忠实于这个狱警角色的原因。
记得第一次实行了他的提议去惩戒罪犯后,Barris发现自己勃起了,而这似乎让他明白了什么。
我推测在现实生活中他的生活极度压抑,他极度自卑,根据心理学来说,他完全感受不到作为男人的骄傲,他内心否定自己,所以心理性阳痿。
而在实验里,他又再一次获得了作为一个男人应有的尊严,这前所未有的快感致使他对这个角色愈发的投入,欲罢不能。
最后在红灯亮了的一刻,所有人走出了仓库,看到了行驶过来的巴士,Barris又挺了挺脊背,把狱警制服当作西服一样系上了扣子。
如果Travis代表的是人性的美好,那么Barris则充分体现了衣冠禽兽四个字。
再讲一下糖尿病小哥,Benjy。
在等车之前,有一个非常秒的画面,Barris,Travis和Benjy是坐在一起的,Travis坐在两人中间,形成了一条线,大家有说有笑。
可是结局却是Barris打死了Benjy,Travis发起了最后的反抗,冲向了Barris。
如果说Travis和Barris代表了绝对的正义与邪恶,那么Benjy就是两方较量的牺牲品,是一个猎物,一方要拼命保护,而另一方要拼命摧残,以此来显示双方的力量。
最后说一下狱警中最有良心的小黑哥,Bosch。
他是最为反对狱警们的暴力行动的,从头至尾体现出了人类应有的道德底线。
正是因为如此,他被同类-狱警所驱逐,成为了犯人的一方。
他代表了道德底线,不同意暴力,可是最后他却拿上了撬棍和众犯人一起殴打狱警,和当初的狱警一样,把自己的不满诉诸了暴力。
(个人认为,如果最后是他递给了Travis那根撬棍,讽刺意味会更明显一点)死亡实验从片头开始说的就是困兽之斗,无非是想证明人类和动物一样,在笼中会做困兽之斗,无关道德,无关法律。
一开始看似狱警是强势的一方,可是最后打斗起来拥有压倒性胜利的是犯人。
Barris到最后都在坚持自己是authority,可是却在满脸的不能置信中被Travis击倒在地。
这部电影取自于真实的实验,是斯坦福大学当年进行的一个实验。
当年的狱警和犯人全部都是学生来扮演,最后好像也诉诸法律了,但是无论如何,那些学生的一辈子因此而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最后这类实验被永久禁止了。
电影的结局还是给我们美好的一面,彰显人性中的真善美。
虽然通篇都是扭曲的人性,或称之为兽性,但是在此我要说一句,即使是动物,在每每搏斗之后(尤其是斗兽场那种)都会发出哀鸣,也是有物伤其类的感情的。
我非常庆幸Travis最后扔掉了撬棍,扔掉了餐刀,这让我依旧坚信人性中的美好。
推荐指数:★★★
2 ) 著名的实验–【A Class Divided】 (分裂的一班)
On the day after 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murdered in April 1968, Jane Elliott's third graders from the small, all-white town of Riceville, Iowa, came to class confused and upset. They recently had made King their "Hero of the Month," and they couldn't understand why someone would kill him. So Elliott decided to teach her class a daring lesson in the meaning of discrimination. She wanted to show her pupils what discrimination feels like, and what it can do to people. Elliott divided her class by eye color -- those with blue eyes and those with brown. On the first day, the blue-eyed children were told they were smarter, nicer, neater, and better than those with brown eyes. Throughout the day, Elliott praised them and allowed them privileges such as a taking a longer recess and being first in the lunch line. In contrast, the brown-eyed children had to wear collars around their necks and their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were criticized and ridiculed by Elliott. On the second day, the roles were reversed and the blue-eyed children were made to feel inferior while the brown eyes were designated the dominant group. What happene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unique two-day exercise astonished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 On both days, children who were designated as inferior took on the look and behavior of genuinely inferior students, performing poorly on tests and other work. In contrast, the "superior" students -- students who had been sweet and tolerant before the exercise -- became mean-spirited and seemed to like discriminating against the "inferior" group. "I watched what had been marvelous, cooperative, wonderful, thoughtful children turn into nasty, vicious, discriminating little third-graders in a space of fifteen minutes," says Elliott. She says she realized then that she had "created a microcosm of society in a third-grade classroom." Elliott repeated the exercise with her new classes in the following year. The third time, in 1970, cameras were present. Fourteen years later, FRONTLINE's "A Class Divided" chronicled a mini-reunion of that 1970 third-grade class. As young adults, Elliott's former students watch themselves on film and talk about the impact Elliott's lesson in bigotry has had on their lives and attitudes. It is Jane Elliott's first chance to find out how much of her lesson her students had retained. "Nobody likes to be looked down upon. Nobody likes to be hated, teased or discriminated against," says Verla, one of the former students. Another, Sandra, tells Elliott: "You hear these people talking about different people and how they'd like to have them out of the country. And sometimes I just wish I had that collar in my pocket. I could whip it out and put it on and say 'Wear this, and put yourself in their place.' I wish they would go through what I went through, you know." In the last part of "A Class Divided," FRONTLINE's cameras follow Jane Elliott as she takes her exercise to employees of the Iowa prison system. During a daylong workshop in human relations she teaches the same lesson to the adults. Their reactions to the blue-eye, brown-eye exercise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children. "After you do this exercise, when the debriefing starts, when the pain is over and they're all back together, you find out how society could be if we really believed all this stuff that we preach, if we really acted that way, you could feel as good about one another as those kids feel about one another after this exercise is over. You create instant cousins," says Elliott. "The kids said over and over, 'We're kind of like a family now.' They found out how to hurt one another and they found out how it feels to be hurt in that way and they refuse to hurt one another in that way again." 官方网站: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divided/导演: William Peters主演: Jane Elliott官方网站: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divided/制片国家/地区: 美国语言: 英语上映日期: 1985-03-26IMDb链接: tt0257489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3883396/
3 ) 电影的原型:斯坦福监狱实验 详细介绍
斯坦福监狱实验是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当时津巴多正在斯坦福大学任教。
津巴多把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改装成监狱,花15美元一天请来了一批学生参与实验。
这批学生要参加实验必须先通过一次测试,以证明他们是“心理健康、没有疾病的正常人”。
一共有70名来自美国各地的学生申请参与这个为期两周的实验,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莱大学参加夏季课程的学生。
24名学生通过了测试,学生以随机的方式被分成了两组角色:其中9名学生担任监狱中的“囚犯”和9名学生则以三人一组轮班担任“看守”的角色。
津巴多本人则担任监狱长的角色。
为了实验更真实地模拟现实,担任“囚犯”的学生身份以数字代替,每个人都穿上犯人的衣服,戴上脚镣和手铐,有些学生是在家里被逮捕的,被铐上手铐,戴上牛皮纸头套,而执行逮捕行为的是同意与津巴多合作进行实验的加州警方,面对呼啸而去的警方,不明就里的邻里大为惊讶;而担任“看守”角色的学生则是穿着警服,戴上黑色的墨镜以增加权威感,在囚犯进牢时,按照监狱的正式程序对犯人进行裸体的搜身,他们拥有一切真实狱警所拥有的权力。
而自愿参加实验的学生们则被告知实验过程中,他们所拥有的部分人权可能被侵犯。
一切如此真实,为的是让双方可以真正进入预置的角色。
津巴多的模拟监狱应该不会发生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毕竟这批所谓的看守和囚犯都是通过心理测试证明是“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
津巴多也在1996年多伦多举行的讨论会上坦诚,在实验进行之前,觉得有可能只是无聊的两个星期。
实验开始的相遇是尴尬,毕竟对于看守和囚犯双方而言,都需要时间进入角色。
无聊的时光如何打发?
于是这群耳濡目染于当时美国反越战学潮的学生囚犯开始挑战权威:撕掉缝制于衣服身上的编号,把自己锁在牢房内不理会看守的命令,并取笑看守。
看守一下子变得不知所措,作为监狱长和实验负责人的津巴多则告知看守们要自行解决问题。
于是看守们采取措施对囚犯进行“镇压”:脱光囚犯的衣服、把囚犯进行数个小时的禁闭、没收枕头和被褥、取消囚犯的进餐、强迫囚犯用手清洗马桶、进行俯卧撑或者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活动而羞辱囚犯、剥夺囚犯的睡眠、半夜把囚犯拉出来清点人数和进行各种屈辱性的活动。
他们还采用了心理上的分化策略:服从管理的好囚犯会被提供特权,更好的牢房和伙食。
这些“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看守”学得好快,如果看过任何一部关于监狱电影的话,这都是看守的狱警常用的策略。
随着实验进行,看守们采用的惩戒措施日益加重,以至于实验人员不得不对他们进行提醒。
在实验进行到36个小时的时候,一名囚犯因受到极度精神压力而出现哭泣、咒骂等各种各样的歇斯底里症状而退出了实验。
实验仅仅进行了不到两天的时间,“正常的、心理健康”的一个好人已经被一群“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折磨得濒临崩溃。
该名编号为8612的囚犯是第一天率领囚犯反抗和挑战看守权利的领导者,因此在看守们的反击中受到了“特别的照顾”。
当一系列的惩罚加诸于身后,8612已经察觉这不是一场模拟的实验、一个虚拟的监狱,而是一个“不是由政府、而是由心理学家设置的真正监狱”。
当8612向津巴多当面提出要求的时候,津巴多也已经完全进入了监狱长的角色,他考虑的已经不是8612的精神状态,而是如果8612退出,会引起更多人退出,实验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于是津巴多像所有的监狱电影中的监狱长会做得一样,向8612承诺让看守不再折磨他,给他好的待遇,同时他提出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让8612回到监狱做他的眼线,向他提供监狱中的信息,如果同意,津巴多就会迟一点的时候“释放”8612。
8612答应了津巴多,重新回到实验当中。
当8612回到监狱中,其他的囚犯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无法退出,实验负责人员不会让他们退出实验。
希望就此幻灭。
津巴多事后回忆他当时的判断,他觉得8612是心理上过于软弱,无法承受哪怕是一丁点的压力,毕竟实验只进行了大概一天的时间,怎么可能会那么快就要求退出实验呢?
实验还有13天的时间啊!
作为实验设计者、心理学家的津巴多,本应客观地评价8612的状态,结果也被监狱长的角色所逐渐控制被影响他的判断。
这种控制一直持续到第六天,直到一个局外人的出现,才把津巴多从监狱长的角色中“挽救”了出来。
而就在8612提出退出的当晚(36小时),当津巴多的研究生Craig Haney作为实验负责人之一轮值夜班时,发现8612“精神已经崩溃,强烈要求退出”,8612无法承受“看守们持续不断地骚扰,仅仅是因为他在第一天领导了囚犯对看守的对抗。
”在同意8612离开监狱进行短暂的休息后,Craig Haney要做出一个外人看来很容易,但当时他感觉极度困难的决定:是同意8612离开还是拒绝他的要求?
津巴多是他的导师和“老板”,午夜时分,不能够骚扰他的休息。
同意?
毕竟我只是个二年级的研究生,这个实验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资金进行筹备,让8612轻易退出便意味着实验设计受到影响,无疑结果的准确性也成疑问。
但当前这个年轻人的状态是他们在设计实验时无法想象的,不放的话行吗?
经过一番挣扎后,Craig Haney还是决定同意8612退出实验。
津巴多和他的同事第二天早上回到了实验室,质疑为什么Craig Haney同意让8612退出实验。
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津巴多认可了Haney的决定。
同时,在后备名单中,他们挑选了一位学生,让他在当天下午加入实验,填补8612的空缺。
而在斯坦福大学古老而庄严的心理学大楼地下室,敌对情绪日益升级:看守们还在继续着他们的游戏,想方设法折磨囚犯;囚犯们则继续承受着折磨,以行尸走肉般的顺从回应。
这已经不是一场cosplay了,不是一次愉快的暑假回忆,不是一次舒服的打工经验,而是一次噩梦。
在试验开始的时候,“看守和囚犯之间没有任何的差异性;而在试验持续了一周以后,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
” 魔鬼已经被释放出来了。
它狞笑注视着这群曾经“健康的、心理正常”的好人,它让一些“看守们”沉醉于规训与惩罚的快感;让部分尽管心理感觉不对、但迫于角色与承诺所赋予的服从义务而不得不配合其他看守,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和反对,只是私下向囚犯提供帮助;它让仇恨在“囚犯”心中播种,以致试验结束之后,当“看守”们和“囚犯们”同坐一起讨论时,敌对的情绪让讨论变成了凶恶的对质,当他们在试验过程中接受试验人员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时,他们呈现均是怀疑的情绪,在他们看来,这群最初友好善良的试验人员就是铁笼的制造者;它让本应客观的心理学家失去了判断。
试验一直持续到第六天。
监狱情况渐进式的恶化启动了所有参与者的心理适应机制:一切都是正常的,一切都是如试验设计所安排的进行。
连接替8612进入试验的代号为416的候补学生最初的“这是个疯人院”的印象也已经被“这理应是个疯人院”的看法所代替,尽管他最初的时候以绝食进行反抗,但经历了黑房幽禁、狱友在看守鼓动下对他进行羞辱的经历后,本应最是正常的他换来的是彻底的孤立,他的绝食对抗让看守和囚犯们从某种意义上站到了一起。
囚犯们以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接受看守们的各种要求。
也有些囚犯以“疯狂的表演”模仿8612,希望以此换取退出试验的机会:在试验的第三、第四和第五天,各有一名囚犯被同意退出了试验。
第五名囚犯在退出的请求被拒绝后,全身出现皮疹的症状,最终退出了试验。
试验过程中,囚犯们实际上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外界。
在只持续了六天的试验中,大约有100多人以不同的身份接触这群囚犯:包括一名真正的典狱官,在接触了所有的囚犯后,他观察到这场模拟试验在这批学生囚犯身上造成的反应与首次坐牢的人非常相似;20 多名心理系的学生从视频监视器和窗户中观察试验;24名囚犯的父母和朋友在探监的时间和囚犯接触,而其中一位母亲在探访之后寻访了一位神父,在神父找到了一位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如何让她的孩子脱离“斯坦福监狱”,这名律师在试验的最后一天与所有的囚犯进行了访谈。
这100多个人,包括看守和囚犯,试验的设计者、心理学家津巴多,都没有想过还有一个选择:中止试验。
他们已经成为局中人,被困在以理性和科学为借口所编织的铁笼之中,无法脱身,唯有服从,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直到试验的第六天,一名年轻的女士的到访。
当Christina Maslach接到津巴多的邀请参与斯坦福监狱试验的研究项目时,心里为之一动。
刚刚获得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她另一重身份,是津巴多的女友。
但Christina已经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助理教授的职务,正准备动身,分身无暇的她只好拒绝了爱人的邀请。
但她还是答应了津巴多帮忙做一些访谈。
为了对访谈有所准备,她在试验进行了大约一周之后的周四晚上来到了斯坦福监狱。
一开始的印象是平静,与其中一名看守进行了交谈之后,她的感觉是这是一位礼貌、友好和让人愉快的好人。
而这晚负责轮班的是昵称为John Wayne的看守,斯坦福监狱最“臭名昭著”的狱警。
尽管耳闻John Wayne的作为,Christina见到了John Wayne之后却感到非常震惊(absolutely stunned):与传闻相反,John Wayne是一个绝对的好人。
但直到她开始试验观察时,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他戴着黑色的墨镜,手持警棍,身穿制服,放声嚎叫,痛骂犯人,让犯人报数时表现出一种粗暴的态度。
当时正当洗浴时间。
洗浴房在监狱外,看守把犯人用脚镣锁成一列,每个人都戴上头套,完全看不到环境的情况。
再把他们带到洗浴房。
津巴多通过观察窗看着发生在监狱的情形,兴奋地对他的女友说:“快来看,看一下现在要发生什么!
”“看到没有,这场景是太棒了!
”但Christina却把头转过去,不忍再看,心里充盈着一种冰凉而作呕的感觉:如此残暴的场景让她感觉到一种女性置身于男权世界所产生的无力感。
随后,离开了试验现场后,津巴多想要知道Christina对整个试验的评价。
但他得到的却是出乎意料的愤怒、恐惧与泪水:“你对这些孩子做的事情太糟糕了!
”辩论、争吵,Christina感到害怕,面前这个不再是她熟悉的爱人,那个以爱生如子闻名斯坦福的温柔而敏感的心理学家。
他们之间的立场从来没有如此巨大的对立和分歧,他们之间的争吵从来没有如此剧烈,如此漫长,留下如此巨大的创伤,她甚至无法想象以后会和这样的一个人相处。
这场争吵的结果是津巴多最终屈服了,从他监狱长的角色、从他对试验理性的准确和客观的追求中脱身而出,向他的爱人道歉,并且决定在第二天早上终止试验。
召集所有与试验相关的人一起,反省整个过程:一场模拟的试验是如何逐步演化成一个真正的监狱,一个如此严重的疯狂之地(madhouse)?
此刻,津巴多感到的不是失望,而是如释重负,如释重负的,还有他和Christina,当时他的女友,后来变成了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
但真正让Christina后怕的,是她作为系统挑战者、不服从者的角色:如果她一直参与试验,她能够有如此巨大的感情触动吗?
如果她参与了设计,每天目睹事情的发生而产生心理的适应性,眼前的这种疯人院会不会像所有其他参与试验项目的100多个人一样,变成一种正常? 她真的不能够做出肯定的回答。
就像莫罗的那句老话:“我们都是自身经历的囚徒(we are prisoner of our own experience)。
”
4 ) 为了制造冲突而制造冲突
首先,哪怕你的实验对象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一共就选了那么几个人,都能放进来两条漏网之鱼(一个谎报糖尿病,一个本来进过监狱),那连实验条件都不满足,能得到什么正确的结果?其次,刻意选择实验对象本身也是不合理的,让那些明显不做实验都能看出来心理有问题的人当狱警,让那些软蛋当囚徒,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这种经典美式大乱斗,只能说是吃爆米花吃傻了拍出这种无脑情节,一切的一切最终都会变成low iq大乱斗选的人这么少,又有很多明显有病的,就这种实验也想试探人性?先试探试探研究者的脑子吧再说各种冲突,就更可笑了一个老头随便传个球能给那黑人砸这么大血,哪怕是男主或者哪个年轻人传的可信度都比这大很明显,参加这个实验的,基本都是为了钱来的,虽然人物背景介绍寥寥无几,但能看出大眼小眼的老黑是为了拿钱治病,男主是为了去印度,混进来的真囚犯也是单纯为了钱,还有大部分人,从言谈中也能看出。
(除了那个胖子,胖子在这里就明显毫无动机了,你要真说为了画漫画得到灵感我还会有感触一下,结果胖子又说这是谎言,那真相又是什么呢?什么也没给,真就靠观众意淫呗)那么你们都是为了钱了为什么不好好遵守规则呐,又不是不给你饭,吃的食物也是豆子,并没有表现出多难吃,反而是囚徒在那无事生非。
咋滴都入狱了你还想吃什么山珍海味吗,简直可笑。
都知道是实验了又不是让你吃一辈子,实验前也警告的好好的咋就开始实验了就都成这样了呢?剩下的就没能认真看下去了,狱警的惩罚也是够离谱,第一个做俯卧撑还是正常人干的,后面的惩罚就纯脑子有病,咋滴才待一天就忘了这只是个实验了?真把自己当成狱警了?实验结束不怕被报复吗,全都是陌生人的实验真就敢这么肆无忌惮也真是够了。
“假狱警”这么对待“假囚徒”,囚徒也都是正常人,不造反就奇了怪了。
好好的正常人没犯罪就来做个实验受这对待谁受得了,狱警是没脑子还是真不想要钱了。
还有实验规则也够可笑,本以为会在规则这里做大文章,没想到规则本身就是个笑话。
发生这么多暴力事件没来人终止?监狱里的规则说一个被打破一个,是为了证明规则就是为了被打破的吗?死人了还不终止继续等着大乱斗才终止,难道研究员不知道已经失控了接下来会大乱斗吗。
各种毫无逻辑以及刻意的冲突让这部披着所谓社会心理学的低智片无时无刻显得很可笑,成功让我写了一篇影评来吐槽,上一部这么厉害的片还是《赌博默示录》,烂,真烂啊
5 ) “loser”的“反杀”:简析《死亡实验》中布瑞斯的角色特点
这是专业课的作业hhhhh很不容易地缩到一页纸了!
《死亡实验》是以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为原型创作的电影。
除了常见的从“狱警-囚犯”的对立关系入手来分析社会角色与认知失范、权力与服从、从众心理等心理学效应之外, “狱警领头人”布瑞斯这个角色也吸引了我的注意:一个最初与特拉维斯(后来的77号“囚犯”)交好的人,后来却慢慢成为伤害特拉维斯最深的人,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是一开始看起来最宽厚的布瑞斯最终成为了整个实验中最大的施害者?
这样的“反转”是由于实验赋予布瑞斯的“社会角色”,还是本就由布瑞斯自身的性格特征导致?
首先,在“世俗”意义上的评价体系中,布瑞斯是一个不太“成功”的人。
从散落在影片各处的细节中我们可以拼凑出布瑞斯的社会形象:42岁,未婚,和母亲居住在一起;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但母亲催促布瑞斯关窗时会重复喊他“chickenshit”,可见母亲并不是温柔宽厚的,布瑞斯在42岁的年纪里并没有获得温柔的母爱;在家庭之外,布瑞斯也经常受挫——他面试时会西装革履(可见他应当有多次求职和求职被拒的经历),也会积极主动地和面试场外的陌生人打招呼、介绍自己(说明他应当熟稔于“引荐自己”来结交人脉,以便获取更多的资源),这些行为恰恰说明他是一个在职场上不太成功;他的经济情况也不是太好,因为他除了参加实验没有更多的办法筹集母亲的医疗费用。
以上种种,共同塑造了布瑞斯的“低自尊人格”。
低自尊人格的人在抑郁、滥用毒品和各种形式的行为过失方面会面临更多的风险,也容易在遭遇挫折和打压(即遭遇“自尊威胁”)时以极端的方式来进行自我保护,甚至以打压别人或其他暴力的方式来应对自尊威胁,以报复行为来弥补受伤的自尊心。
所以影片中我们看到, “狱警”这个身份角色给布瑞斯带来了莫大的愉悦和快感,现实里长久失意的他在这个身份中前所未有地品尝到权力的滋味。
他深陷其中,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觉得“囚犯”们必须服从于自己。
而现实中长久以来的压抑又会让布瑞斯更加珍惜这个身份带来的权力和威势。
库利认为“自我概念”是一种“镜像自我”,人对自己的认知建立在别人的“反射性评价”上,即通过观察他人对待自己的反应来确证自己的社会身份;同时,“自我概念”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自我参照效应”——人们倾向于把自己看作世界的核心——也因为这样,当个体觉得自己被冒犯时,会产生强烈的应激反应,有时也会采取各种手段来维护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
所以,当以特拉维斯为首的囚犯们忤逆、反抗狱警们的“权威”时,布瑞斯在他们的反射性评价中感受到自己的身份尊严受到了冒犯。
因此,布瑞斯选择使用暴力行为来压制囚犯们(尤其是特拉维斯),希望重建自己的权威和自尊心。
当然,这一选择与他的低自尊型人格也是分不开的。
在这个角色扮演的实验中,布瑞斯第一次理直气壮地大声训话,第一次肆无忌惮地实行暴力,第一次感受到大权在握、高人一等的快感。
他对自己的认知也受到“近因效应”的影响。
在此前的生活里,布瑞斯是一个“loser”,但实验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重塑了他对自己的认知:他觉得自己就是囚犯们的控制者,就是拥有权力和威势的狱警;他一方面不想过从前被欺侮、被漠视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在贪恋着“狱警”这个身份带给他的快感。
也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最初看似内向、良善的他,最终成了陷落在“狱警”身份中最深的人。
布瑞斯这个角色也提醒着我们:现实中长久陷于困顿、失意的人,更有可能拥有反社会人格,社会底层的“受害者”也有可能成为新的“施暴者”。
6 ) 当监狱大门打开的一刹那,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这部电影是描述“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事实上我也是沿着这条线索才看的这部电影,然而我要讲的却是另外的一些思考。
红灯想起,监狱大门打开的那个场景,我感触很深刻。
前一秒大家都还在苦和暗的深渊里各自挣扎,两个阶级的矛盾彻底转化为暴力,然而刹那间,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刺眼的阳光照了进来,外面的世界好陌生,又好熟悉,我们不就是从那里来的吗?
噢,原来我们已经忘记了自己从哪里来,已经忘记了我们最原始的目的,已经忘记了这只是一个实验,我们陷得太深太深了。
明明只是为了报酬参加一个心理学实验,最后却把自己真正的当做了狱警或囚犯。
我在想,当有一天我们将要死去的时候,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突然觉得所有世间的一切、自己的行为、各种坑爹的人为制定的规则以及各种尊严和勾心斗角都是浮云了,都是在这个世界里陷得太深的结果。
那时我们会不会后悔这一切,像电影中的“典狱长”一样有所懊悔呢。
我们要始终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而且我们也终究要回到那里的,不要让世间的纷杂扰乱了自己纯净的内心。
这世间得到的一切,权力也好,利益也好,都不值得把我们变成一个魔鬼。
7 ) 导演借了斯坦福实验的壳,拍了个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
刚刚看完《死亡实验》这部电影,说实话跟我的心理预想(不是预期)差距还是蛮大的。
之前在社会心理学课程上老师曾经给我们详细的讲过这个赫赫有名的实验,并给我们看过当时录制的真实实验影像(上古AV画质),之后在网上也看过很多介绍文,所以在看电影之前对实验过程已经有些了解。
本身以为这是一部相当纪实的翻拍电影,然而当我看到糖尿病患者之类的设定(甚至最后他倒在血泊中),才发现这个版本的《死亡实验》加入了相当多的戏说成分。
与其说这部电影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还原版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不如说这部电影实际上将很多不同的心理学效应混搭、糅合到一起,成为一锅大乱炖。
不得不说这部电影相较于斯坦福实验,实际上倒是更像另一个跟斯坦福实验齐名的服从性研究——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
相信本身知道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人,或多或少也知道米尔格拉姆实验的内容。
实验由两人进行,一个是实施电击者,一个是被实施电击者;前者看不到后者,但能听到后者的声音。
在科学家以及实验规则的指示下,电击的电压不断加大,被电击者发出凄厉叫声并最终沉默。
尽管如此,由于科学家不断声明被电击者没有生命危险,并不断催促实施电击者继续实验,很多人因此将电压不断加大不断加大不断加大不断不断不断……加大。
以果壳网的描述概括一下就是:“许多人对权威的顺从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在科学家的指示下,许多参与者会对无辜的人施与一个足以致死(至少参与者是这么相信的)强烈电击”回想一下电影中面对那个糖尿病的“囚犯”,黑人狱警头头所说的话:“(大意是)监狱里的摄像头24小时都在不间断地监视着监狱里的情况,如果那个人真的有绳命危险,那些科学家会坐视不管吗?
既然他们没有给任何指示,那就说明没有问题。
”这段话其实是这部电影中的实验(而非斯坦福实验本身)的问题核心所在,而恰巧跟米尔格拉姆实验十分相似。
导演或者编剧实际上是套了一个斯坦福实验的外壳,拍了一个米尔格拉姆实验。
对比一下电影与米实验的相似点。
首先,两者中都有实验对象出现生命危险,电影中是糖尿病患者,而实验中是受电击的人。
其次,实验的参与对象都无法科学的判定危险的严重程度,而只能用常识来判断;例如电影中人们也不知道糖尿病患者不注射胰岛素能挺多久,甚至患者本身也抱着搏一搏的心态,但是根据常识判断情况十分危险;而米试验中实施电击的人尽管看着仪表上写着几十伏一百几十伏的电压,但是也不知道具体多少电压会威胁生命,但是根据被电击者的叫声他们有一个常识性判断。
其三,两者中都有一个绝对的权威者作为危险程度的衡量者,而且受到实验参与者相当大的信任,而且这个权威者都是科学家;电影中摄像头后面的科学家对于什么情况是过分的有绝对的决定权,而米实验中科学家对于什么样的电压是危险的,被电击者究竟有没有生命危险有绝对的权威。
而最后,这些相似点导致的结果也是一样的,那就是人们在权威之下不顾“受害者”可能面临的危险与痛苦,继续实施危险行动。
电影里权威的影子到处都有体现。
科学家们是最高的权威,黑人头头是狱警们的权威,狱警们是囚犯们的权威,这样的一个层级结构,而这个层级结构唯一的合法性(legitimacy)和持续性都来自于那个红灯——最核心的权威,权威的顶峰和本源。
权威是电影和米试验的核心所在,当权威不再被人们信任的时候,原本的体系就崩塌了。
在米试验中,当实施电击者的常识性判断超过了对科学家的信任后,便拒绝继续实施电击。
在电影中,体系崩塌的第一个多米诺骨牌就是那盏红灯的权威性不再被人们信任,原因是已经明显发生了违反社会基本原则以及流血事件,然而那盏红灯依旧不亮,“为什么你们还不停止这一切?
”;于是人们开始发现,不仅狱警们已经疯了,而且科学家们也疯了(实际上他们确实是疯了,哪有死了人还继续实验的科学家)。
由于黑人头头的权威是基于那盏红灯的狐假虎威的权威,因此随着红灯权威的消失,他自身的权威也轰然崩塌,紧接着是狱警们的权威崩塌,之后整个实验就陷入无政府主义了,这简直是生动地描绘了一个集权主义的政治体系是如何崩塌的。
那么这样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电影的设定是复制津巴多的监狱实验,为什么会演变成米格拉海姆实验呢?
究竟是哪里的不同使得原版和复制版实验的走向发生了不同?
我觉得一个关键的不同就是实验机制的区别。
在真实的监狱实验中,津巴多本人(科学家)尽管也是权威,但并不是躲在幕后的,而是作为“监狱长”以及整个实验的负责人,实时地参与到实验当中,当发生一些过分的,不合适的行为的时候,会出面予以提醒和制止。
相比之下,电影版有三个不同点:其一、科学家躲在幕后,让人们看不到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怎么衡量,怎么决策,但只能服从其安排,这很像集权主义的“神秘主义”特征,或者说像极了《1984》的老大哥;其二、狱警们没有犯错的机会,只要他们一次没有给予合适的应对,实验便要结束,他们就都拿不到薪酬,而津巴多则是多次干预了实验;其三、也是最核心的一点:这个实验中行动的评定上只分为两类——可以与不可以,只设置底线(bottom line),而不对“可以”但“过激”的行为做任何的纠正。
第三点产生的后果,需要联系到心理学的另一个效应,就是anchoring effect(锚点效应)。
人们在评估一个东西,不论是价格、表现还是身高体重,都很难凭空作出判断,而需要一个锚点。
比如说,如果你从来没买过洗面奶,最近因为长痘不得不买,进超市发现一罐60块钱的,也不知道贵不贵,合不合算;如果你以前买过一罐40的,或者有人告诉你一个普通、大家都用的牌子卖40,你就知道这一罐有点贵了。
在电影中,狱警和囚犯们面临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可以允许的,什么是超出允许范围的?
这决定了他们能不能拿到钱。
所以第一天演了那么多,实际上根本的内容就是找到这个锚点。
狱警们一开始也很茫然,知道黄毛找到第一个锚点线索——“相应的”(commensurate)。
于是囚犯们做了什么,预警们作出程度完全相同的应对,就是“可以的”、“合适的”。
这样做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权威的运行机制有问题,导致后面的走样。
原因即为红灯只设置底线(bottom line),因此预警们为了更好地树立自己的权威,以“可以的、合适的行动”为锚点,开始试探底线。
当成功之后,预警们的下一次评估,就不再以第一个锚点,而是以成功的底线试探为新锚点,来定义自己的行为是否是合适的,并探索新的底线。
如此的恶性螺旋只会导致预警们的举措越来越过激。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电影与真实实验相比,行动与体制的互动关系也不太相同的。
在电影中,是只设底线的体制逐渐塑造了人们的行动方式;而在津巴多的实验中,尽管狱警和囚犯的设定作为体制的一部分也塑造了人们的行动,但另一方面,随着实验的实施,预警囚犯甚至津巴多本人逐渐进入角色并按照角色定位行动,整个实验的机制也从优先考虑实验参与者的心理和生理承受力转变为优先考虑实验的进行与持续。
人们的行动改变了体制。
与底线原则的螺旋向下性相辅相成的,是权力欲望的无限扩张性。
尤其是在一个集权体制中。
我们都知道扩张性内在于资本主义,因为必须要有持续的扩张,资本才能保持延续性。
投资的盈利必须用于新的投资,否则无法保持现在的盈利。
汉娜阿伦特在《集权主义的起源》中描述了帝国主义中权力类似于资本的扩张属性。
在帝国主义体系中,权力必须不断的扩张才能保持自己的存在,权利的存在的唯一目标就是扩张,扩张才能保持权利存在;在此意义上,权力即是扩张,扩张即是权力。
因此,帝国主义必须通过通过不断侵略,来扩大权力的边疆,实现权力的扩张(这解释了列强的殖民扩张);如果殖民地瓜分干净,没有继续扩张的空间,那么帝国主义之间就会爆发战争,强行继续扩张(这解释了一战);如果甚至无法用战争来扩张,那么权利中枢便只能通过内部破坏,即摧毁国家内部现有的政治结构,来扩大自己的权利(部分解释了苏联的大清洗运动,以及苏联下一任领导人对上一任的政治清算)。
在电影中,黑人头头通过试探底线,不断地增强羞辱的强度,也不断地发明了更多惩罚方式,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权力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预警们的惩罚引发了囚犯们的反弹,因此只有对反弹实施更强大的镇压,也就是探索新的、更强力的羞辱和惩罚方式,同样也就是进一步的权力扩张,才能保持自己的权威,而不被囚犯们的造反推翻。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只有不断扩张权力,才能保住现有的权力;而狱警们手握权力,拿这个权力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扩张权力——强迫囚犯们做更多的事例如服务自己的性欲。
权力即是扩张,扩张即是权力。
底线原则为权力扩张提供了条件,权力扩张不断实践和探明底线原则。
以下省略一大段辩证法。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津巴多和电影导演意图的根本不同:前者想用一个实验论证屁股决定脑袋,人们的角色影响了人们怎样行动;后者则想展示给我们人是怎样屈从与权威、利用权威、抵抗权威,并描绘了一个不人道的集权体系是如何建立的以及怎样坍塌。
除此之外,电影中的实验未能还原的一个效应,还是造成了很大……不能说遗憾吧,只能说区别。
在津巴多的实验中,角色对行动的塑造效应,对狱警和囚犯都十分明显。
狱警逐渐变得残暴,囚犯逐渐变得顺从。
而在电影中,着重表现了前者,但对后者的描绘却乏善可陈。
影片的笔墨重点放在了囚犯们如何反抗,而不是囚犯们如何变得顺从上,这也与影片“反抗权威和集权主义”的基调相吻合。
在这部影片中,并没有任何一个扮演囚犯的人真的把自己当做一个囚犯。
他们的服从只是镇压的结果,而不能论证角色对于行动的塑造性。
17号囚犯虽然很服从,但那是因为他曾经当过囚犯,而且一开始便决心服从,所以也不能论证角色的塑造能力。
而在真实实验中,有部分扮演囚犯的人确实改变了对自己的定位:从角色的扮演者变为角色本身。
最后想说的影片中的一个心理学效应,是“社会情境效应”(social context effect)。
除了一开始科学家给予的角色外,整个模拟监狱内部的社会影响,也就是身边的人怎样行动,也对每个个人的行为产生巨大影响。
监狱里的社会情境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在一开始其实是没有被确定的。
监狱里可以是狱警和囚犯和平相处的,互相平等、配合、体谅的,可以一起打打闹闹的,就像实验刚开始白胡子黑老头期望的那样,也就是双赢win-win;也可以是狱警高高在上,囚犯绝对服从的,也就是零和zero-sum。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啥影片中的监狱社会情境最终变成了第二种,而不是更理想的第一种呢?
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尽管这个社会情境一开始并没有规定,或者说人们一开始照搬了现实的外部社会中人人平等尊重的社会情境到模拟监狱里,但是人们心中隐含着一个对于监狱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设定,这个设定来自于纪实片、电影与身边人的述说,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隐形的社会情境,它会逐渐引导狱警和囚犯的扮演者向着他们心中真实的狱警和囚犯靠近;第二是两类社会情境对于狱警和囚犯的扮演者各有利弊,双方因此产生利益之争,有特权的一方获胜。
双赢社会情境,表面上看是双赢,实际上是囚犯占便宜,这让他们过得舒服,但却让狱警们承担违背第五条规定的风险而胆战心惊;第二类社会情境让囚犯很痛苦,但是狱警很爽。
所以双方已开始便在争夺社会情境的“定义权”。
第一次针锋相对的争夺和冲突发生在囚犯们到底要不要把狗屎餐盘舔干净这件事上。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遵不遵守规定的争执,实际上是一场为谁才对监狱里应该怎么样说了算而引发的争夺战。
最终必然是手握特权的狱警获胜。
总结一下,除了几处明显不现实的情节,影片其实拍的不差。
不能单纯因为影片没有还原真实实验而说编剧水平差。
影片借了斯坦福实验的壳,诠释了别的主题,而且诠释得也不错,逻辑上也没有硬伤。
最后一场打戏很叶问,有冤冤相报的感觉,虽然看着很爽但是还是蛮微妙的。
8 )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2010美国剧情片《死亡实验》,翻拍自2001德国同名电影,定级R,豆瓣评分7.3,时光网评分6.9,IMDb评分6.2。
小说《黑盒子》取材于1971年斯坦福监狱实验,2001德国版根据小说《黑盒子》改编,本片则是翻拍德国版,一长串的链条。
美国版只有96分钟,德国原版114分钟。
较短的时长使得美国版的人性过渡不如德国版流畅和自然。
美国版砍掉了德国版中的男医生和女医生的戏份,男医生只在开头出现,没有女医生角色。
德国版中对剧情有推动作用的女友在美国版中打酱油,美国版中爱情戏份对剧情没有用,干扰主线剧情,应当剔除。
德国版中男主的狱友是卧底军人,美国版没有这个设定,男主狱友是有过服刑经历的黑帮。
美国版最大的变化是双男主设定,将狱警之一作为男主,通过狱警男主的黑化来体现权力改变人。
美国版的这个改编不错,因为真实实验主要的结论就是权利改变人。
美国版过渡强化了男主的个人英雄主义,将男主塑造成了坚强的囚犯领袖,其实应该像德国版那样将男主塑造成受压迫而反抗,男主不应当是坚强的英雄,这样的设计不符合真实实验。
男主被镇压,让我想到了几个词——杀一儆百,杀鸡儆猴,枪打出头鸟,擒贼先擒王。
在监狱管理中,狱警无论用什么手段都必须压住挑事的囚犯。
美国版突出了狱警的暴力镇压,折磨囚犯的剧情很少,这一点不如德国版更贴近真实实验,事实上折磨是最好的让囚犯顺从的方法(比如真实实验和德国版的拿走囚犯的床),暴力容易引发反抗,事实上美国版主要体现的就是双方针尖对麦芒的对抗,这不符合实验原型。
美国版结局做了改变,增加了实验者们木然地做大巴离开,增加了实验者拿到了酬劳。
影片有个槽点,狱警说囚犯人数是狱警的几倍,并且不止一次地这么说,可实际上上囚犯只有十多个人,难道编剧不会数数吗?
9 ) 转载:米尔格伦实验Milgram experiment
米尔格伦实验(Milgram experiment),又称(权力服从研究, 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针对社会心理学的科学实验。
实验的概念最先开始于1963年由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史坦利·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在《变态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里所发表的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一文,稍后也在他于1974年出版的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里所讨论。
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遭遇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
实验开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纳粹份子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被判死刑后的一年。
米尔格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
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
”(Milgram, 1974) 米尔格伦在他的文章“服从的危险” (Milgram, 1974)里写道: “在法律和哲学上有关服从的观点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但他们很少谈及人们在遇到实际情况时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我在耶鲁大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一个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辅助实验的科学家所下达的命令,而会愿意在另一个人身上加诸多少的痛苦。
当主导实验的权威者命令参与者伤害另一个人,更加上参与者所听到的痛苦尖叫声,即使参与者受到如此强烈的道德不安,多数情况下权威者仍然得以继续命令他。
实验显示了成年人对于权力者有多么大的服从意愿,去做出几乎任何尺度的行为,而我们必须尽快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和解释。
” 实验方法 实验小组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和寄出许多邮递广告信,招募参与者前来耶鲁大学协助实验。
实验地点选在大学的老旧校区中的一间地下室,地下室有两个以墙壁隔开的房间。
广告上说明实验将进行约一小时,报酬是$4.50美元(大约为2006年的$20美元)。
参与者年龄从20岁至50岁不等,包含各种教育背景,从小学毕业至博士学位都有。
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并被告知自身将扮演“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然而学生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
参与者将被告知,他被随机挑选为担任“老师”,并获得了一张“答案卷”。
实验小组并向他说明隔壁被挑选为“学生”的参与者也拿到了一张“题目卷”。
但事实上两张纸都是“答案卷”,而所有真正的参与者都是“老师”。
“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他们不能看到对方,但能隔著墙壁以声音互相沟通。
有一位参与者甚至被事先告知隔壁参与者患有心脏疾病。
“老师”被给予一具据称从45伏特起跳的电击控制器,控制器连结至一具发电机,并被告知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
“老师”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单字,而“老师”的任务便是教导隔壁的“学生”。
老师会逐一朗读这些单字配对给学生听,朗读完毕后老师会开始考试,每个单字配对会念出四个单字选项让学生作答,学生会按下按钮以指出正确答案。
如果学生答对了,老师会继续测验其他单字。
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会对学生施以电击,每逢作答错误,电击的瓦特数也会随之提升。
参与者将相信,学生每次作答错误会真的遭到电击,但事实上并没有电击产生。
在隔壁房间里,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学生打开录音机,录音机会搭配著发电机的动作而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随著电击伏特数提升也会有更为惊人的尖叫声。
当瓦特数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学生会开始敲打墙壁,而在敲打墙壁数次后则会开始抱怨他患有心脏疾病。
接下来当瓦特数继续提升一定程度后,学生将会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应。
电压 “学生”的反应 75 V 嘟囔 120 V 痛叫 150 V 说,他想退出试验 200 V 大叫:“血管里的血都冻住了。
” 300 V 拒绝回答问题 超过 330 V 静默 到这时许多参与者都表现出希望暂停实验以检查学生的状况。
许多参与者在到达135伏特时暂停,并质疑这次实验的目的。
一些人在获得了他们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保证后继续测验。
一些人则在听到学生尖叫声时有点紧张地笑了出来。
若是参与者表示想要停止实验时,实验人员会依以下顺序这样子回覆他: 请继续。
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请继续。
你继续进行是必要的。
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
如果经过四次回覆的怂恿后,参与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实验便会停止。
否则,实验将继续进行,直到参与者施加的惩罚电流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并持续三次后,实验才会停止。
结果 米尔格伦为整个实验过程和其结果录制了纪录片,纪录片名便是服从,纪录片的正版拷贝目前已经很难找到了。
他接著与Harry From制作了5部的一系列受到这次实验影响的社会心理学影片[1]。
这些影片都可以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媒体中心找到。
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伦曾对他的心理学家同事们做了预测实验结果的测验,他们全都认为只有少数几个人—10分之1甚至是只有1%,会狠下心来继续惩罚直到最大伏特数。
结果在米尔格伦的第一次实验中,百分之65(40人中超过27人)的参与者都达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惩罚—尽管他们都表现出不太舒服;每个人都在伏特数到达某种程度时暂停并质疑这项实验,一些人甚至说他们想退回实验的报酬。
没有参与者在到达300伏特之前坚持停止。
后来米尔格伦自己以及许多全世界的心理学家也做了类似或有所差异的实验,但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为了证实这项实验,也有许多更改了架构的实验产生。
马里兰巴尔的摩郡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的Thomas Blass博士(也是米尔格伦的传记—《电醒全世界的人》的作者)在重复进行了多次实验后得出了整合分析(Meta-analysis)的结果,他发现无论实验的时间和地点,每次实验都有一定比率的参与者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约在61%至66%之间。
对于实验结束时的情况所知不多,依据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回想,当时那些没有达到最高伏特数的参与者却也都没有坚持这项实验本身应该结束,也没有至隔壁房间探视“学生”,离开时也都没有询问实验人员的同意。
对实验的反应 实验本身受到了关于在科学实验上的伦理质疑,因为这项实验对参与者施加了极度强烈的情感压力(虽然这种压力可以说是由他们本身自由操作所造成的),尽管这项实验带来了对人类心理学研究的宝贵发现,许多现在的科学家会将这类实验视为是违反实验伦理的。
米尔格伦则辩护道,之后的调查发现当时的参与者中有84%称他们感觉“高兴”或“非常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15%参与者选择中立态度(有92%的参与者做了事后的调查),之中许多人事后还向米尔格伦表达谢意。
而且米尔格伦还不断接到这些前参与者想要再次协助他进行实验,甚至想加入他的研究团队。
六年后(也就是越战规模最大的时期),其中一个前参与者与米尔格伦联系,表示为何他们会感觉“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 “1964年当我在进行实验时,虽然我相信我是在伤害某个人,但我完全不晓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当人们根据他们自己所信仰的事物并顺从的服从权力者行动时,很少人会意识到这点...请允许我这样认为,我被权力机关征召入伍,而这将会让我做出一些连我自己都会害怕的坏事. ... 如果我拒绝服兵役的良心申请(Conscientious Objector)不被权力机关所批准,我已经准备因此而去坐牢,这对我的良心而言是唯一的选择。
我唯一的希望,是我那些同样被征召的伙伴们也能如此发挥他们的良心...” 不过,实验的经验并不是对每个参与者都有终身的改变。
许多参与者都没有依据现代的实验标准被告知细节,离去时的面谈也显示许多参与者看起来仍没有理解到这项实验的真实情况。
实验所引起最主要的评论不在于实验方法的伦理争议,而在于实验所代表的意义。
一位在1961年的耶鲁大学参与者在Jewish Currents杂志上写道,当他在担任“老师”的中途想要停止时,便是怀疑到“整个实验可能只是设计好,为了测试寻常美国民众会不会遵从命令违背道德良心—如同德国人在纳粹时期一样”而这便是实验的初衷之一。
米尔格伦在他《服从的危险》一书中便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便是,我们在实验室里所制造的使人服从权力的环境,与我们所痛责的纳粹时代之间有怎么样的关联。
”http://www.psychspace.com/psych/viewnews-619.html
10 ) 改编自斯坦福监狱实验——《路西法效应》
书名:路西法效应作者: [美]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 ISBN:978-7-108-03310-9出版日期:2010-03-15定价:¥48.001971年,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教授主导“斯坦福监狱实验”;该实验有如一发震撼弹,引爆全球心理学界重新审视以往对人性的天真看法。
三十年后,津巴多教授以《路西法效应》首度亲自撰述、并呼应从“斯坦福监狱实验”到“伊拉克监狱虐囚案”三十多年来观察到的社会现象,深度剖析复杂的人性,全盘且深入解释“情境力量”影响个人行为的概念。
在实验中以标准的生理与心理测验,挑选了自愿担任受试者、身心健康且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被随机分派到“守卫”和“犯人”两组,接着让他们身处模拟的监狱环境。
实验一开始,受试者便强烈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去扮演被指定的角色。
实验第六天,情况演变得过度逼真,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转变为残暴不仁的守卫或是情绪崩溃的犯人——一套制服、一个身分,就轻易让一个人性情大变——为期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宣告中止。
为什么握有权力的人,很轻易地为以控制他人为乐所诱惑?
而置身弱势角色的人,为什么却常以沉默来面对问题?
独具开创性的“斯坦福监狱实验”研究,津巴多教授将为读者解释“情境力量”和“团体动力”如何能使平凡男女变成残忍的魔鬼。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努力想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例如“男性-女性”、“上司-员工”、“父母-子女”、“老师-学生”、“医生-病人”等关系,在这些社会角色剧本的规范与束缚下,我们是否会像上帝最爱的天使路西法一样不知不觉而对他人做出难以置信的事?
本书提供认识地位和权力角色差异的原因;了解在环境中影响个人思考、情感及行动的形成及改变原因;帮助读者重新审视、了解自己,一旦面临陌生情境,自己会做什么及不会做什么,以及面对情境的强大压力,如何勇敢反抗“路西法效应”。
适合本书的读者,有犯罪学家、教育家、法官、临床心理师、电影小说工作者,以及父母和他们的子女;也适合嫉恶如仇者、欲拯救性灵的慈善家,以及准备手刃淫妇(夫)者,而尤其是,当你我在感叹人性堕落之际,这本书将启开我们对人性文明的新希望;认清黑暗,将更明白在何处点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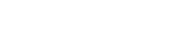






















不爱这版
和原版没办法比…
不给力啊,还是德国的原版给力
在特定条件下,人性是会自然扭曲的
表演好也无济于事,编剧低智商坏了一个好故事。
与《浪潮》放在一起看,真是黄金搭档。
剧情情节编写不足够同时也不够符合逻辑!
美国人拍的各种片都有一股美国味儿这种感觉就跟食堂的饭菜永远都有一股无法诉说的食堂味儿一样
看了觉得智商下降。。。。过程沉闷
原来这部是翻拍的……不过其实挺好看,尤其最后越狱那段,没有什么比压抑了一个多小时的情绪爆发的瞬间来得痛快,这就类似于军训若干天之后全校学生奋起暴揍教官,又或者(您所发表的言论涉及敏感话题,请不要发表)……咦?为什么我发表不了呢?
这是求知还是无知呢?永远别拿人性做实验 输不起!对于这复杂又脆弱的东西 可以反思 但不可轻易定义~ 老美翻拍的很有自己特色~那就是艺术理想至上与现实有些脱离 出发点高尚 形式上刻意 所以剧情上软肋不少 相较之下德国原版的就更有说服力 不过就电影题材的思考上来说 都值得找来看看
在特定环境下人性是会突变的
以暴制暴是自然法则,看完这部电影,觉得本我意识不强的人还是有信仰的好
金钱、权利、地位,那位豆友说得好:“权利是春药,谁吃谁发烧。”不过还是觉得该去看看德国原版。在《滑稽戏》里面就被Cam那个眼线男秒了,这部里面也同样,好帅气~~才知道原来一直网上热传的超级奶爸图里就是他~
表现得太假太没说服力,虽然人性本恶部分还是有表现出来。
7.3分
垃圾,白瞎了两个NB演员。
斯坦福监狱实验是个好实验,但是这部片子实在是部烂片子,用力过度的演技让人看了比导演勉强塑造的氛围更恶心
权力是春药、麻药、毒药、安眠药
用力过猛。多大事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