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之春》热门推荐
《小城之春》剧情介绍
本片为田壮壮向1948年费穆执导的同名电影的致敬之作,与费版相比,画面颜色变成彩色,空间延展许多,女主人公的独白被隐去,故事内容和讲述的手法也有一些不同,变得更为今天的观众所能接受。 影片伊始,便点题交代了年轻少妇周玉纹(胡靖帆)和丈夫戴礼言(吴军)之间貌不合神也离的关系,玉纹对礼言只是在尽传统道德伦理要求她尽的义务,同时,礼言的昔日好友、玉纹的旧时情人章志忱(辛柏青)正从上海赶往小城,虽然他的到访令玉纹在情与礼之间摇摆不定,有了走出小城的心思,但因独白不再,那更多是突兀而非满足心中长久以来的期待。而小妹戴秀(卢思思)因为身边原有一大帮和她一样充满朝气活力的朋友,志忱对她的触动以及她对志忱的爱,也打了些折扣。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行运扫把星联邦调查局:通缉要犯第一季外星也难民:2024年万圣节特别篇100八佰恋慕杨光的快乐生活4赛末点玄璃美人煞灿实也多福学警旋风犬部!第4防御区地平线警视厅特务部特殊凶恶犯对策室第七课乐高蝙蝠侠大电影:DC英雄集结杀手信徒第二季玲珑井夜幕低垂空战魔导士候补生的教官OVA寻爱咖啡馆背负春天刑警队长赘婿之吉兴高照文明伯尔尼的奇迹毛骗终结篇白月光下疾风使命风云天地
《小城之春》长篇影评
1 ) 兩代導演眼中的「小城之春」
在中國電影史上有兩部「小城之春」,它們分別於1948年及2002年誕生,分別由費穆與田壯壯導演執導。
一個是第二代導演,一個是第五代導演。
新版的出現可以說是田壯壯對中國最重要的導演費穆的一個致敬、臨摹與學習。
當時田壯壯已有十年沒有執導演筒,全因為拍了一部「藍風箏」,這是一部有關中國政治變遷的電影,以一個男生從出生開始的成長故事去呈現在反右到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之下生活的無奈、荒謬與影響。
戲中更對文化大革命這禁忌作出赤裸裸的處理。
因為這種處理令「藍風箏」被禁,不准公映不准他再執導演筒。
直至2001年才有機會再拍電影,受禁十年的他選擇去重拍四十年代的經典,全因為他知道這是最可行的選擇。
他在訪問中曾說過已十年沒拍電影,難以找到投資商支持他去拍太大的製作,而且在題材上亦要小心,不能再與政府正面交鋒,所以他選擇去拍一個不用費太多錢又不敏感的題材作為他再回影壇的首個作品。
田壯壯導演是非常尊敬費穆的,他認為費穆在所有前輩導演中,是受到生命最不公平對待的一個,他是一個用心去愛電影與話劇的人,其他東西都不會做,而且他不會以拍電影來賺錢,更不會為任何利益去向任何勢力妥協,就如當時日本軍來了,要求他拍電影,他寧願放棄工作離開電影廠也不拍,之後自己就跑去搞話劇,過自己覺得對的生活。
在當時「小城之春」這經典並得不到新中國的認同,他們認為是一部極之消極頹廢的電影,沒有配合新中國的新方向,反而在同情資本家與剝削者的個人情感問題,完全是一部與政府背道而馳的電影。
再加上與鼓吹的新現實主義有違背,完全是生不逢時,不合時宜。
結果「小城之春」一直被禁,直至八十年代初才得以重見光明。
所有看到此片的人都難以接受原來中國在1948年己有一部如此有藝術性有深度的電影,並從此奠定它在中國電影史上重要性。
其實田壯壯與費穆都一樣,拍了一部有自己立場,獨特藝術性的電影,但都因不能被政府接受而被禁,我想田壯壯一定很明白當時費穆的心情,這也許是他特別喜歡這部電影的原因,他說他每年都會看這一部電影,每次看都有新的發現,他就在2000新世紀來臨前的一年再次看這電影,並突然覺得想重拍這部電影。
本來他告訴過自己不會再去拍名著,因為他吃過老舍「鼓書藝人」的教訓,他在製作的時候得到的只有苦惱。
再加上「小城之春」已經是拍成了電影,還是一部被公認是經典中的經典,再重拍簡直是難上加難。
但最後他領悟到「我是在臨摹,我臨摹得再好也只是贗品。
我已經輸了,所以我反倒沒有負擔了。
」以故事來說,兩個版本幾乎一樣,角色劇情的設定都一樣,不同的只在於如何去說一遍這故事。
在新版中,找不到舊版經典的獨白,那獨白真的運用得很好,而且是出神入化,所有的獨白都是由女主角玉紋說的,但有時候她是以角色的主觀角度去說,有時就會以第三者的全知角度去說,既替自己的角色表達心情,又是導演的代言人,是在同期作品難以找到的。
當中有些獨白運用得很特別,例如當玉紋知道有個姓章的客人來了準備出去見他的片段,看到的是她停止了綉花,並她在房裡整理頭髮,走到走廊上看著,獨白就聽到「我心裡有點慌,我保持著鎮靜,我想不會是他,換了件衣服,整理一下頭髮,我想是個普通的客人。
站在廊子上,看了一看,看不清是誰。
」獨白跟畫面見到的是同步的,有別於其他的獨白,有人也許會覺得畫面已看到的事情,為何要說出來,豈不是重複了,像句廢話。
但假如沒有這幾句獨白,光看到他整理頭髮,是不能如此準確地明白到角色那時的緊張與複雜的情緒。
田壯壯選擇不用獨白,他選擇讓獨白的情感溶化在劇情之中。
但那些複雜的情感是難以讓觀眾去知道,換言之田壯壯的版本明顯隱瞞含蓄一點。
含蓄這一點在玉紋與志忱的身體接觸上亦能看到,記得在舊版中有一幕四人同到城牆上遊玩,志忱在禮言背後偷偷地拖著玉紋的手,直至禮言轉身。
又例如志忱第一次約了玉紋到城牆幽會,他們都有手挽著手走在小路上,往後的身體接觸當然難以逐一指出。
反觀新版,以上兩個片段都改成因城牆上的路不平坦而需要志忱扶著玉紋,走過了就放開手。
這樣的處理令到他們倆的關係更內歛更含蓄,把接觸變得合理化,又沒有獨白去表達,大家都會對玉紋的心態立場少了認識。
當然他也加了一點片段去表達玉紋的心態,例如當第一晚玉紋帶著被褥到書房時,她聽到禮言在咳嗽;又例如戴秀生日那晚,她打扮一下後欲到書房去找志忱,她先遇到禮言問她:「妳要出去?
」她沒回應並繼續向書房去。
這兩個變動都加強了她對禮言的心態,她不在乎他。
在對白上他亦作出了變動,如玉紋在城牆上做媒那段,她最後說:「我不想你走,我也不能跟你走。
」這清楚指出玉紋的受制於禮教的心態。
但另一點看到的是志忱的含蓄與不去表達,不像舊版那段,明顯志忱有表達過想帶玉紋坎,她才會說:「我有點矛盾,我不想跟你走」雖然沒有真切聽到他問,但那個溶鏡已做到這個效果。
公平一點去說,田壯壯應該希望他們的關係與舊版有點不同,特別是志忱,他明顯沒有舊版那麼敢於表達自己對玉紋的感情,而且在玉紋面前他有點怕作主導,並沒有舊版那個肯定。
就例如第一次提出到城牆上走走談談都有點沒信心去說。
這不知是否因為製作的年代不同,大家對偷情,對男女關係的睇法不同了。
以前的社會,男女是規規矩矩的,大家的感情表達都是含蓄的,不敢於表達自己的愛,那麼敢於表達自己的愛才是不平凡的行為,值得欣賞的,因為他們做到自己做不到的。
但現在的社會就不會這樣看,他們對愛情與男女關係開放了,敢於表達愛意,男女的身體接觸並不是新鮮的事,反而含蓄地默默地有距離地愛著對方才是現在缺乏的,珍貴的。
也許是這個原因令到有兩種不同的處理。
另外,在攝影剪接上都有不少的不同。
在新版,攝影機明顯與故事的角色們都有著距離,像在冷眼旁觀著故事發展,這與舊版有著明顯不同。
這做法其實很配合田導演較含蓄的處理,並沒有舊版那麼用特寫去加強去點出角色的心態。
以戴秀生日那場為例,新版是以一個鏡頭直落只以場面調度去描寫,並沒有用到不同鏡頭的組合,雖然欠缺了舊版那些特寫鏡頭如玉紋解扣、禮言看著二人手在划拳等等,但仍然以鏡頭的搖動看到的,只是要專心一點去細味。
又例如第一次相約到城牆上與划船,兩場同樣地以一個鏡頭拍攝,與舊版很不同。
原本特寫的二人鏡頭變成全景鏡頭,對於角色的表情變化,觀眾難以清楚準確地看到,看到的主要是動作,這仍保持著田導演的目的,冷靜觀察。
但在划船那幕,明顯少了舊版的複雜性,不只少了精彩的剪接,設定上亦由兩個開心兩個鬱鬱不歡變成四人都是開開心心地划船唱歌,只有一下玉紋的回頭,但沒看過舊版的一定看不到。
在整個長鏡頭當中看不到內裡的變化,明顯是一個差的鏡頭處理。
再這樣比下來,真對田壯壯很不公平,因為費穆的「小城之春」真的是一件天衣無縫的作品,像田壯壯所說,如何去拍都是不會贏過他,一開始已經是輸了。
但應該欣賞的是田壯壯那份虛心與用心,明顯看得到他下了不少苦工去嘗試才能拍出這新的「小城之春」,老實說他已經把原著的味道拍了出來,那份淡然的無奈的確能感受到。
不知道何時會再出現另一個「小城之春」呢?
期待那春天的來臨。
2 ) 不怎么样
没觉得哪好看了人少就五个人转来转去除了哪场舞戏挺好的小城嘛静悄悄的可是总觉得哪不对让人泛困也许是节奏的问题也许是自己心情的问题看花样年华就没这感觉只好一边锻炼一边看不太搭界不过没办法总觉得要发生点什么可是没有最后也没有倒是男女主角第一次见面比较有特点让人一眼就看出有故事可惜男配太木了不过也是因为是电影才觉得有事要放平常生活指不定就不觉得了男主角风格像黎明不过不是据说有人问田壮壮:你觉得观众会喜欢这风格吗答曰:爱看不看不错我喜欢风格有点像才片子可能是翻拍的原因故意这样的可是我不喜欢弄得和老胶片一样没意思女人有的时候实在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总不一样我遇上个这样的估计得挂掉还是开朗的好虽然一直在说晒太阳可是到最后才真正出现阳光也许在暗示日子有了转机可我不这么觉得有人为你自杀一次你就会爱上他她么顶多是可怜吧要不就是自责
3 ) 小城之春,1948,2002
2002年重拍《小城之春》时,田壮壮刚解禁不久,基本采用copy的路径,可能风险低吧。
美学上没有任何跨越,意味着些许倒退。
要演绎民国时期上海的富家知识分子没落做派,确实太为难年轻的演员了,能感到他们的效仿,拘谨和煎熬。
2002版的摄影指导是大名鼎鼎的台湾人李屏宾,当时正值近50岁创作巅峰期。
相比之下,1948年,30岁的广东人李生伟做《小城之春》的摄影指导就显得人微言轻多了,他之前只是摄影助理身份。
可见费穆先生不拘一格。
两个版本在镜头运用上有不少共同点,比如以跟踪人物为主的移动长镜和固定长镜。
缓慢移动前景模糊掩映的长镜转为固定长镜是李屏宾的本片标志性镜头,经常用于交代环境和人物关系和人物最终状态,2002版的宅院规模似乎要大不少,移动长镜替代了1948版的叠化转场。
戴礼言在废墟中独坐或春色掩映中彷徨,登场均没有露脸,全景。
两版镜头异曲同工:他处于厌世半隐居状态
1948年,戴秀的开窗亮相,焕发无比生命力,与其兄反差巨大,镜头魅力显现。
2002年,戴秀没有标志性登场,人物相对弱化。
借用此长窗廊是其嫂周玉纹标志性场景之一1948,借管家老黄之手,兰花被端进了章志忱暂住的书房,周玉纹自有深意,因为兰花代表了女主人的节操和爱情。
所以,费穆先生给了这盆兰花一个清雅的特写。
2002,故事完全重演,但是更加茁壮硕大的兰花已不再替女主人向志忱吐露心意。
虽然有兰花的镜头不少,而且不止一盆。
待续,,,,,,
4 ) 小蜜女主角
琼瑶阿姨又重拍《一帘幽梦》了,L看了片花,不胜感概,把一个好好的帅哥方中信给整成了白痴纯情男,把帅哥整砸了,人民群众心里能没气吗,据说,这位帅哥一看到例如优美建筑啥的,必做出陶醉状,说,好美好美啊……花絮说,方先生经常笑场,真同情哎。
宣传网站里还郑重其事写上,女主角用上了MSN……琼瑶阿姨大概正为与时俱进美得不行呢。
我等,我等,那天俺们俩足足笑了一刻钟。
为此致谢。
女主角,我们看了照片,刻薄一回,根本不像女主角吗,她说一小蜜,我看差不离。
可是翻拍这回事,大家都挺喜欢的。
我刚巧看了《小城之春》,也是一翻拍。
看完了,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好像是熟悉的家,进了陌生人,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就说那个女主角,表情倒是挺呆滞的,可是那举手投足,怎么看怎么像,同上,小蜜。
就给妹妹头上擦点桂花油吧,那手啊,就摇曳生姿、含情脉脉的一塌糊涂。
这手势,连我这女的,看了都心里咯噔一下,唉,修炼得还不够,可是想想人家玉纹,本是愁眉不展、看不到希望一人,有这个劲头在那儿玩手势吗。
大家闺秀,举止要合体,这般挑逗,哪儿跟哪儿啊。
还有,这个玉纹说话那叫一个娇,说不出的柔媚,哪有半点丈夫笠言口中玉纹的“冷”可言。
费版的玉纹是典型的大家闺秀,稳重大方,不动声色,极有分寸感,印象最深的就是和志忱深夜私会砸窗的那场戏,平时的克制与那一刻的爆发,对比鲜明,极富冲击力。
再看这里的这位,经常性地找机会接近志忱,动不动就往人身上靠,经常性距离只有0.01公分,还哪有那种潜流暗涌的情感发展啊。
当然,这女演员挺有魅力,也挺有女人味的,仪态也算万方,只可惜,她不是俺心中的玉纹,就跟琼瑶阿姨的那位女主角一样,忒像小蜜了。
不知道这女主角像小蜜,算不算是与时俱进勒。
费穆那时代正是大乱刚过,百废待兴,十足迷茫,再看今朝,本片全在赏玩,包括女性的柔美,庭院的清幽,根本不是一个心态嘛,时代剧变成了言情小品,而这个年头的人估计也提不起多大兴趣,觉得小儿科。
5 ) 史铁生评《小城之春》
在史铁生的《信与问》中读到他给田壮壮的回信,谈到自己对于新版《小城之春》删去女声独白的独到看法,另有对独白改编的大胆建议,对塑造礼言一角的想法,甚至假设礼言果真死了又将如何,“人性的一时压制,似不难解放,唯娜拉走后如何,还是永远的疑虑”。
谈及玉纹和礼言,好一个“独白的囚禁”,“无言的湮灭”和“未来的悬疑”,对于礼言死去的假设,好一个“死得无声无息,死成永久的沉默”,提到他钟爱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好一个“要我们从现实醒回到梦中去”。
就像信中说的,“小城”不会白白“之春”一场,但也可能就这么白白。
很好奇如果导演在完成拍摄之前得到这些反馈,或索性让史先生加入编剧团队,最终成品又将如何?
原文搬运如下。
给田壮壮壮壮:你好!
你送的三张碟,我认真地都看了。
有点想法想跟你说说,不管对不对。
最突出的一个想法是:玉纹的内心独白删得可惜了;在我看,不仅不要删,那反而(对于重拍)是大有可为之处。
因为,那独白,绝不只是为了视点,更不单单是要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在我理解,那特地是要划出一个孤独、封闭的玉纹的世界。
什么人会整天自己跟自己说话,而且尽是些多余的话?
一个囚徒,一个与世界隔离的人,一个面对巨大精神压迫而无以诉说者。
而那独白,举重若轻一下子就得到了这种效果——即于众人皆在的世界里(如画面和表演所呈现的),开辟出了玉纹所独在的世界(靠的恰恰是那缓慢且莫名的内心独白)。
这效果,在我想,是除此手段再用多少细节去营造都难达到的。
所以那独白才似无视常理,有时竟与画面重叠,仿佛拉洋片,解说似的多此一举。
作为通常的画外音,那无疑是多余,但对于一个无路可走的心魂当属恰如其分,是玉纹仍然活着的唯一证据。
这是费穆先生的本意?
还是我的误读,或附会?
我想应该是前者,否则按常理,他怎会看不出这独白的重叠与啰嗦?
但我斗胆设想,费先生的孤胆似还有些畏惧——这条独白的线索不可以一贯到底吗?
比如说——在志忱到来之前,那独白是一个封闭绝望的世界;志忱到来之后,那独白(譬如“我就来,我就来”),则是一个尚在囚禁但忽被惊动的心魂,以为不期然看到了一种希望时所有的兴奋、奔突、逡巡;而当玉纹与志忱心乱情迷似乎要破墙而出之际,那独白的世界即告悄然消散,不知不觉地就没了;再到最后,志忱走了,或从礼言赴死之际始,那独白就又渐渐浮出,即玉纹已隐隐感到那仍是她逃脱不了的命运。
另外我想,要论困苦,礼言不见得比玉纹的轻浅。
若玉纹是独白的锁定,礼言则几乎是无言的湮灭。
“他也不应该死呀”(大意),这样的台词太过直白。
尤其是,这样的人也许就死了,死得无声无息,死成永久的沉默;唯其如此,“他也不应该死呀”才喟叹得深重。
我胡想:设若礼言真就死了,会怎样?
志忱和玉纹就可解脱?
就可身魂俱爽去投小城之外的光明了?
——这些想法,于此片或属多余。
我只是想,当初的影片可能还是拘泥于人性解放,但人性的解放,曾经(或仍然)附带着多少人性的湮灭和对人性处境的逃避呀。
可否用无言、用枯坐、用背影,也为礼言划出一个沉默的世界?
费片中,有一场礼言发现志忱和玉纹告别的戏,我想,也许倒是志忱和玉纹不止一次地发现礼言悄然离去的背影要更好些。
那个沉默的世界几乎连痛苦的力气都没了,唯沉默和不断地沉没下去,沉没到似乎那躯壳中从不存在一个人的心魂。
在我想,礼言是绝不要哭的,哭是最轻浅的悲伤,礼言早应该哭完了;如今礼言觉察了志忱与玉纹的关系,对于这个无望又善良的人来说,只不过是久悬未决的一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我确凿是多余了。
他应该是静静地走。
哪有哭,然后自杀的?
设若礼言果真死了,后面想来更有戏做;那时志忱和玉纹的纠葛或可至一个新的境界。
结尾可以开放:如此局面下,志忱当然还是要走的,但逃离的是其形,永远不能解脱的是其心,他多半会给玉纹留下个话儿,留下个模棱的期冀。
玉纹呢?
心知未来仍是悬疑,因而独白再现;此时的独白,有多种意味——可能重归封闭,可能又是一个湮灭,也可能有另外的前途。
从而“小城”才不白白“之春”一场,但也可能就这么白白。
无言的湮灭,独白的囚禁,以及未来的悬疑——悲观如我者,看这几乎是人生根本的处境;而这才构成戏剧的张力,生活的立体吧。
你说拉开距离,似仅指今日与往昔的时间距离,观众与剧情的位置距离,但重要的是(剧中与剧外)心与心的距离,或心对心的封闭。
人性的一时压制,似不难解放(譬如礼言果真一命乌呼),唯娜拉走后如何,还是永远的疑虑。
在我想,小城的寓意,绝不止于一启恋人关系的布设与周旋,几年前从电视上看到此片,竟留下与《去年在马里昂巴》相近的印象,如今细看才知错记。
但何以错记呢?
绝不无缘无故;此片中若有若无地也飘荡着一缕气息,像《去年在马里昂巴》那样的一个消息:要我们从现实醒回到梦中去!
中国人轻梦想,重实际(有梦也多落在实处,比如发财,比如分房和得奖),这戏于是令我惊讶中国早有大师,只是又被埋没。
其他都好,不多说。
词不达意,见面再聊。
信,唯一的好处是可以斟酌,此外一无足取。
祝好,并问候令堂大人!
有一年知青晚会,她特意从主席台上下来跟我说话。
前些天在电视上见到她,老人家的真诚、坦荡、毫无修饰的言辞让我感动。
铁生2002/8/15
6 ) 新小城,旧春天
50多年之后,田壮壮重拍了费穆先生的《小城之春》。
新的小城里,花有了颜色,春天也有了它应有的模样。
不多不少的五个人聚集在戴家大院里,说的是新时代的话语,遵循的是旧时代的游戏规则,追忆的,是旧时代的春天。
田壮壮的《小城之春》整体基调仍是感伤的,人物仍是欲言又止的。
2002年电影里的这个春天如同1948年那个一样,孤立静止地呆在那里,人犹犹豫豫地从它面前晃过,终仍是没有打破平衡。
独白田壮壮隐去了费穆先生电影里玉纹独特感伤充满诗意的独白。
电影一开始,三个人物便一齐登场。
玉纹买菜抓药的时间里,礼言正在院落里对着春天对着满院落的残破喟叹,而志忱,则由火车从上海带回这个小城,正往礼言家奔。
不似1948年的《小城之春》的开头,玉纹用独白向我们交待她和丈夫礼言的日常平琐生活,告诉我们她并不知志忱会来,独白里念叨的正奔过来的志忱只是她因失落衍生的期盼。
没有看过或对费穆先生的《小城之春》一无所知的人直接观看田壮壮的重拍版或许在理解上会有一些难度。
田壮壮不仅隐去了独白,许多来龙去脉也一并隐去了。
田壮壮版本里玉纹与志忱十年后的初次见面,大概只有心敏感的人才能感觉出两人都有一丝不稳的情绪吧!
因为之前并没有任何伏笔交待玉纹与志忱是旧日恋人,观众只会当玉纹对丈夫礼言的朋友志忱的热情是种礼貌,是懂事贤淑的表现。
但是在费穆先生的电影里,我们看到玉纹内心的渴望竟成了真。
我们的情感随着玉纹的情感流动,她一遍遍念叨的昔日情人章志忱竟真的出现了,竟在这种场合作为她丈夫戴礼言的旧日好友出现了,她该做些什么?
她该怎样去做?
费穆先生的《小城之春》里,玉纹的渴望随着她的独白一次次成了真,志忱携带着她向往的生活一步步地朝她靠近。
只差那一霎那,她便可冲出小城走向新世界去过她梦想中的新生活。
在田壮壮的版本里,玉纹和志忱的进展虽也是与她的渴望亦步亦趋地前行着,然而少了内心的独白之后,其言起行不免有些生硬和苍白,情感传递到观众这里,引起的共鸣自然也少许多。
空间新版本的小城里出现了延伸向远方的铁路,有了商铺,学校里也出现了一大帮和戴秀一样充满了朝气的年轻人。
甚至站在城墙头向远方眺望时,还能看到绿色的田野。
想想1948年那个春天,除了几截断墙、几间旧房和一个旧城墙头外,别无其他。
虽在玉纹的独白里我们也知道这城里是有人家、商铺和学堂的,不然药和菜从何而来?
戴秀又去哪里念书?
然而影像里终没有呈现出学堂或商铺的模样,志忱乘坐何种交通工具来到这小城也没给予交待说明。
费穆先生电影里的小城是个完全封闭的小城。
玉纹和志忱复发的旧情,玉纹和志忱对道德伦理的顾忌,全在一个密不透风的空间内展开。
人物的言语、神态、动作都在一步步地制造紧张的气氛。
直到旧的平衡跌落,处在空间里的人才幡然醒悟,掩面而泣过之后,在跌落中尽快建立了新的平衡。
田壮壮版本里制造的空间虽大了,却也给人一种无意义延展空间的感觉。
人物间本该有的饱和张力涣散崩溃了,他们的言行多少显得造作刻意。
或许田壮壮是想将伤春的情怀仅留给一小部分人,毕竟这已不是1948年已是新时代,他不是让那些同戴秀差不多年纪的孩子们在志忱的劝引下丢掉了害羞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吗?
新旧两部《小城之春》是不能生硬地作对比的。
毕竟194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处在关口中的费穆先生难免会在影片中将自己对祖国对民族命运的思考放在影片中的几个人物身上,给处在私密空间内的他们赋予一定意义。
田壮壮重拍这部电影是想表达对中国电影先驱者的深深怀念和敬仰,同时在影片里放入自己对当下中国“新电影”的理解。
空间,在新的时代必须变大,要考虑的只是传统的一些东西是不是要丢弃。
田壮壮最后的笔触是和费穆先生一样温婉的。
玉纹面对自绝的丈夫留下悔恨的眼泪,志忱则离开小城又去了上海。
新的平衡还是在跌荡后被建立了。
田壮壮在多年压抑之后选择重拍这部经典旧片,除了让热爱中国电影的人感动的勇气之外,必寄托了某种情思。
不妨对比着两部电影的结尾来谈:1948年,费穆让玉纹再次踱上城墙头向远方眺望,随后礼言赶来,玉纹牵起他的手并指向远方初生的太阳给他看,或许这是预兆某种温和的希望,是费穆先生本人心中所想所憧憬的希望的光芒。
而2002年,田壮壮让礼言叹息着修剪花木,让玉纹坐在有阳光照射的阁楼里继续绣花,最后让摄像机在一段城墙前静止不动,这些是否田壮壮依旧迷茫无所皈依的心境写照?
纪念的电影是拍完了,对“新电影”的理解和态度也放进去了,心中却仍有一股烦闷的气不知如何宣泄——是对这个快速奔向前只讲速度的时代,也是对那一套无聊的电影审查体制。
7 ) 死气沉沉的小城,春心荡漾的人们——新旧版《小城之春》之比较
费穆是有经验而善感知的,黑白斑驳的老版有着散文般的结构和诗歌化的特质,而裹挟着静美情欲的玉纹、热切的志忱、温良的礼言以及青涩而富于活力的小妹在急管繁弦的淋漓时光里成为了刻在钩沉录、旧胶卷、故纸堆里的默然群像。
梦幻空华,五十三年——当胡子拉碴的田壮壮重拍《小城之春》的时候,不同人讲的同样故事已从艳冶凋零、沉缓阴谲的黑民谣转调重编为一支缱绻精致而颓废华丽的后摇曲。
“谨以此片献给中国电影的先驱们”——田壮壮在新版片头如是说,除去第五代导演对前辈的神交、瞻仰之意,不消说是为了避“挑战”之嫌:毕竟他翻拍的是“百年最好的电影”。
而田是有自己想法的,新版虽已不再有久远、潮湿的味道而变得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但也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一些艺术魄力。
“兀然无事做,春来草自青。
”——何其相似的断垣坏墙,春的到来没有唤醒城头的枯树似乎只暗示着人们的春心荡漾。
新旧两版最大的差异是在表达方式上,包括叙事角度以及镜头语言。
旧版开头,平拍,长镜,缓慢地跟摇,玉纹挎着菜篮子、晃着动人的腰肢揣着千愁万绪蹀躞在荒芜城墙。
而新版,仰拍,草草地给了玉纹一个镜头便切到戴家破落的门庭和繁盛的花树,再一下,章志忱就已经下了火车。
我在看新版《小城之春》时,第一个感觉便是志忱出来得太早,铺垫的不足使观众对新版的节奏产生不适,相形费版的游刃有余田版的镜头处理显然过于生硬。
老版《小城之春》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比如,玉纹第一次夜访一共用了十二个镜头,从对玉纹的脚的俯拍、上摇开始,到玉纹的第二次离去,能发现镜头之间是互相对称的。
人物的站位,镜头的时长……这些都是对称的,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建筑美,是对电影这种舶来品的成功本土化。
然而,“一天只拍一两个镜头”的认真做法并非一无可取,相比有着律诗韵味的费版,田壮壮的镜头语言则像参差的长短句,丰富秾丽而善于捕捉,最后构成一阕愁肠百结的婉约词。
老版最大的特色便是画外音,即玉纹的独白。
在百废待兴的一九四八,无名小城春意盎然而人心依然春寒料峭,玉纹化身为先知像口述一本回忆录一般面无表情地娓娓道来,声音同屏幕上闪烁的光点一样虚幻。
这里第一人称的自白实际上化为一种超现实的全知视角,给整部片子蒙上了一层凄楚而神秘的灰雾。
新版摒弃了老版的这种手法,在惨悴的灯光下,在精心的布景前,田壮壮的电影眼睛推拉慢摇、隔窗偷窥,打算用纷繁的镜头和其他角色的分摊试图讲清楚这个故事。
田壮壮在《南方周末》上如此解释:“画外音给人的感觉比较近,或者是一个比较主观的状态。
我觉得,已经过了五十年了,我希望这个距离远一些,现在的人去看,应有一个观赏距离的不同。
我还是希望远远地看这件事,应该是更客观一些了。
因为我觉得重拍的方式不一样了,叙述的心情也不一样了,和那个时代的距离也不一样了,可能是为了统一吧。
”因而在田壮壮那里,我们对周玉纹是没有同情甚而是无所知的,我们只有猜测她是心情压抑,她是欲求不满,她是静水流深……或即其他,不一而足。
可以这么说:旧版《小城之春》是中国影史上心理写实主义的开端;而新版只能算一部尴尬的故事片,而作为一部故事片,田壮壮的这部重拍作品仍缺乏一定的广度和深度。
无论是广袤的历史还是湍急的影史,五十年似乎都不是一个很大的度量单位。
田壮壮也算敢于扛鼎的勇士,其举不是有意的狎戏而更多探索的意味,其间也多有创新的段落和田导独特的风格。
布景、灯光、道具、配乐、人物塑造诸种也属广义上的表达方式。
新版中,阿城改得了剧本,做得了木匠,包括李屏宾的摄影和叶锦添的美术,在光影流转、空间变幻中揭露人心的远近明暗。
几树春花,旧时大家族的庭院,精致旗袍显出玲珑身材,花格木窗,洋蜡……是张爱玲的沉香屑、琉璃瓦,或是安妮宝贝的青天白日以及淡淡烟圈——“寂寞空庭春欲晚”,这是一部刻意追求颓废的电影。
五十三年的积淀未必有了颓废的资本,只是技术上的进步和新时期文化思潮的冲击却滋长出一种希望消受颓废的情绪,整部电影借由视觉糖果蔓延出一种无端的愁绪和落花般颓废的情感,填补了小资们和有闲阶级的审美渴望。
也许老版的《小城之春》没有那么“好看”:黑白片的质地,城墙颓圮,院中单调,即使春花热烈也在四散的砖块中显得妖异而狰狞。
家,真的是破落,同戴礼言衰弱的身体一样。
连年的战乱使得旧版的背景真实得发出一种阴黢黢的味道。
虽然囿于技术层面的原因,但老版依然不遗余力地造出小城之“春”:当玉纹喃喃说起“家,在一个小巷里……”的时候,画面中出现了纵面拍摄的小桥——小桥前面是灿然狂放的桃花,后面则是萦纡蜿蜒的小巷。
老版通过古典式的“烘云托月”手法间接地描摹出一个温煦的桃花源。
配乐上,老版的背景音乐基本上取自古典戏曲,韵味旷远而含义颇丰。
尤其是每个人的出场,配同一首曲子但用不同的节奏与音调:礼言的出场,音乐沉闷喑哑;小妹的出场音乐则富于节奏感,清新活泼……一向以为好的配乐能是电影锦上添花,不但引导着影片的节奏,也感染着观影者的情绪。
较之老版古旧平缓的民族音乐,田壮壮的情调是钢琴加胡琴,是舞曲,是洋歌,是脱胎于欧洲古典和中式怀旧的产物,新旧版在配乐上各有特点,平分秋色。
不免想诟病一下新版的人物塑造:吴军饰演的戴礼言面色红润,筋骨有力,完全不像是有痼疾顽症的人,而且从对白中知道他曾经还可以在吊环上做倒立动作……在田版里,礼言是警觉而脆弱的,他扶树啜泣;而在老版里,礼言是迟钝而温良的,他静默无言。
在老版里,费穆要求演员们学习戏曲,用戏曲化的细腻动作表达内心感受——身体动作、吐字发音,都用到了京韵的表演和念白,以至每个人的出场都遵循着京剧演员出台亮相的规矩。
新版所用演员多为话剧演员出身,话剧与电影是不同的艺术形式,因而我觉得新版的演员表演更加生硬(虽然一般认为老片子的演员演技要夸张些,而新旧版的《小城之春》是对这一惯例的悖反)。
费穆的蒙太奇不疾不徐,晃晃悠悠、一叠一掩地展开,恰似旧戏文里的咿咿呀呀——浅笑低吟间人情生灭,不着重彩而尽得风流,相形之下,新版略显夸张的表演、生涩的对白则难望旧版项背。
值得一提的是,《小城之春》是一部只有五名角色的电影。
古人讲究“意境”之说,老版中,小城是全然封闭、密不透风的,这种虚托性的背景处理不仅做到了写意传神,甚而带有现代性的意味;并且通过一种被简化、被提纯的人物关系展示了一种较为纯粹的可能性,提供了朦胧的象征意义和无尽的遐想空间。
而新版无疑打破了小城与人们的界限,为这种深刻的隐喻做出了体无完肤的解构:有碧绿的田野,有商铺,铁轨延向远方,学生翩然起舞……田壮壮这样的处理真的好吗?
新版要比老版多出三十分钟——这种戴家院子之外的场景延伸、主要角色与次要角色的互动,感觉就像在《十二怒汉》里插入闪回镜头或者纪实片里引入外星人的概念一样令人蹙眉不解。
好比四人春游时却用灰暗的影调,黛青色天空下的单薄歌声让人不寒而栗;而周玉纹在城墙上的瞭望则变得那样矫揉造作、无病呻吟;再有章志忱教学生跳舞的桥段,是为了展示章的别样魅力,还是渲染其与小妹的情愫呢?
再有,一身西装的章志忱为了玉纹三两下爬上树去取她挂在树梢上的手绢,这样刻意地雕琢旧爱,是不是显得粗浅而做作?
这种凌乱的再造与陈旧的话语于增加影片的含金量并无裨益。
重拍诚然是两难之举,既不能简单复制,更不能完全背道而驰,但新版给我的感觉仍然是热情有余而用心不足。
说完表达方式,更觉有必要讨论一下两版小城之春主题内容或者说是动机立意上的差异。
一九四八,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牵扯了过多的家国意味,抗战甫胜,南方小城,四方相望,孰无深意?
因而历来评家与观众爱以杜甫《春望》作电影的注脚——“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我无意以民族主义的视角解读《小城之春》,在我看来,电影故事简单而意向明确。
国破是不错,小城春临而草木幽深,时代烙印是躯壳而心脏仍如火里红莲般对人类的永恒命题进行不懈的试读与探索。
“蓝天白云星光虫鸣还有真理多余/别当真别乱问别乱猜/我没有答案。
”两千年风云激荡,人们揣着不同的信仰或者没有信仰走进新世纪,学习新的游戏带上新的面具遵守新的规矩。
田壮壮眼神狡黠而经历坎坷,《蓝风筝》的被禁早已让他心痒难耐,他说:“两千年,人人都觉得应该是理想实现的时候了,所以在那一年人们把表面文章都做得很漂亮,但是心都挺沉的,有一种没来由的惶恐。
”惶恐未已,迎难而上,蛰伏多年的田壮壮以更彻底的一种方式向费穆致敬,重拍了《小城之春》。
费穆的片子有一个经典的长镜头:小妹为志忱唱歌,志忱的眼神却流连着玉纹,玉纹则伺候着礼言吃药而不顾志忱灼人的目光,迟钝的礼言则只顾吃药。
田壮壮踌躇满志地翻拍了《小城之春》却不能安排一样的镜头,他是这么做的:在小妹的生日晚宴,志忱和玉纹带着撩人暧昧的划拳使不再迟钝而万分警觉的礼言走了出去抱树痛哭。
而志忱更是冲动地当着小妹的面给玉纹唱歌,还将玉纹抱了起来…… 老版隐忍而新版激情。
五十年,两部电影的差异中可瞥见国人思想之变迁。
但我是不大同意说费穆“发乎情止于礼”的传统解读的。
确实,当玉纹下定决心走进房间并兀自关掉灯站在志忱面前的时候,浓稠的黑暗里已经充满了腥热的赤裸裸的情欲。
当玉纹一改往日的沉闷孱弱形象而猛地击破玻璃的时候,这突然的一下同《一条安达鲁狗》割眼球的画面一样振聋发聩。
萨特讲,人有绝对的自由但必须为这自由负责。
玉纹被这种对自由的渴望占领征服了,膨胀的情欲同“止于礼”的传统思想彻底决裂,其歇斯底里的程度说是隐晦版的《感官世界》也不为过。
新版的深度与表现力则不及老版,情色电影与艺术电影有一线之隔,尽管影片里的桃色成分不过是深深庭院里的一声猝然裂帛,但为了偷情而偷情的行径并不足以作为一种成功的抒情方式。
在田壮壮的《小城之春》里,玉纹最后连送志忱都没有送,她低眉垂眼,顾自做着刺绣,窗外是矮檐细瓦,影片最后在青天衰墙的空镜中结束。
老版的结局是开放的,给出曙光而没给出答案。
当礼言拄着拐杖慢慢上坡和玉纹站在一起的时候,我不知道玉纹伸出手臂究竟在指点什么,横在两人之间的是天堑地坼,这个家庭已经是摔破的罐子了,旧日生活难以为继。
“我想他不是肺病,是神经病”,这句独白充斥着一种无意的恶毒;“我想他死”——玉纹是够善良而隐忍的,而人却不能欺瞒自己的潜意识:玉纹既然既已歇斯底里了一次,难道就不会继续臣服于强大的“自由”么?
这种结局实在是乍暖还寒,既是对封建思想不着一字的挖苦也是对人性的深入拷问——天平的一边是既为人妇便尽己责的传统道德心,另一边则是容易被贴上难听标签的追求爱情与幸福的权利——费穆把这个艰难的抉择交给了观众。
旧版的结局是封闭的。
在新版里,礼言是没有病的,甚至曾经是个健壮的男子,只是因为门庭的破落而忧心成疾。
而新版的玉纹小巧乏味,完全看不到裹在她旗袍里的蓬勃的情欲,灵与肉的挣扎显得轻飘无力,与志忱的偷情顶多只能看成是一出爱情游戏。
除此之外,导演还要让年方二八、单纯可爱得如同一颗青杏的小妹直面残忍的情感纠葛。
田壮壮本身的艺术气质是同《小城之春》不相投的,他对玉纹诸人轻描淡写而一心将礼言置于保护之下,女性的锥心之痛在光耀门庭的首要任务下必须忍辱负重。
只能说同样的故事穿越五十年已经由一部含义无限的银幕经典嬗变为有着俗世美学的伦理闹剧。
费穆对人性充满了尊重与哀伤,讲述的是期待与张望,而田壮壮只是换了一个视点讲述了一个男人获得救助的故事。
事到如今六十年,默然的群像在黑白画面上“放射出让人目眩心惊的光芒”,这部经典之作以惊人的艺术自觉、超前的叙事方式成为中国电影的代表作品,是一座难以逾越的艺术巅峰。
田壮壮的重拍或许是有话要说,且不管说得如何,我们依然应该感谢田壮壮做出的努力,让中国电影有了反思的习惯和前进的动力。
8 ) 于细节处见尺度——浅谈小城之春费版田版之异同
《小城之春》拍摄于1948年。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历史时间节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百废待兴之际《小城之春》上映了。
或许是抗战时期人们看乏了战争题材的电影罢。
电影《小城之春》确实以小见大的方式反映了当下时代的风貌。
而后田壮壮导演翻拍了费版的《小城之春》其改编之处接下来细细评论。
电影《小城之春》讲述的是一个四角恋的故事。
在小城里,女主(周玉纹)困守小城,嫁人无子,与丈夫貌合神离,有分无情。
一日接一日的消磨时光似乎是要将女主困死在小城。
没有希望的生活,没有情感的日子。
而男主(戴礼言)整日躲在破旧小花园里,怀念往昔的繁华,带有一点对妻子的愧疚,但我认为他更多的是在自怜。
而后女主(周玉纹)昔日情人的归来(章志忱)的归来让二者的情感与郁结彻底释放。
首先先谈谈费版,在镜头调度与处理上,可以看出来电影镜头的使用以及人物的调度左翼电影时期的电影镜头使用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例如开头处:戴礼言进入院子是人物先入画,再出画,再入画。
而镜头则是笔直的通过破旧的院墙进入。
在镜头的选择上,符号化,象征性的镜头运用的比较多。
例如:戴礼言的破旧的院墙象征着他残破的精神世界,城墙之外虽未出现,但是象征着美好和希望。
电影里频频出现的兰花象征着几人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
田版去掉了很多象征化的镜头。
从构图上,框架式的构图比较富有古典的韵味,环境的传统与章志忱的时髦的穿衣打扮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周玉纹以及戴礼言一人着旗袍,一人着长衫,小妹着学生装似乎也暗示着最后的剧情走向与归属。
而田版的构图更加自然,生活化的同时也丧失了古典的情调。
费版的小城之春与田版的小城之春区别最大之处也就在于对于周玉纹旁白部分的处理。
费版大量使用了周玉纹的旁白,周玉纹作为本次风波核心,以她为中心,大量展示她的内心活动有助于导演更准确的表达。
而田版则使用的是镜头画面来展现,视角更加客观,表达更加柔和。
去掉独白的小城明显缺少了女主内心独白赋予他的郁结的滤镜。
但是在情节上更加客观与生活化。
但相比而言我更喜欢费版的处理,由周玉纹起的那种郁结似乎有种别样的魅力赋予在此电影上。
在人物关系的表达上,费版的周玉纹对于章志忱的到来带着一些身不由己的主动,情感表达上也更加热烈。
那种压抑已久的情感爆发后的不能自控的情绪与神态表现得非常的彻底。
对于戴礼言的存在有点像《菊豆》里的那样,情绪过于集中在章身上,对于戴有点忙不过来的视而不见。
而在新版中,周玉纹更像是扮演着两个角色,一个是相敬如宾的人妻,另一个是谈恋爱的女孩。
最后谈谈戴礼言。
戴礼言在费版里虚弱无力,在玉纹那郁结埋怨无可奈何的独白里相得益彰。
而田版的戴礼言则有些过于中气十足,透露着僵硬与不自在。
特别是那让人无比尴尬的配音。
频频让我跳戏。
虚弱的像是刚割了声带。
最后总结一下,田壮壮导演对于《小城之春》的改编更像在原片上的扩大版,展现了更加细腻的镜头与更加完整的人物。
但经典不愧为之经典,费穆导演对于影片的掌控与细节处的拿捏确实精妙。
火候十足。
9 ) 咯么虾米叫含蓄呢
壮壮版《小城之春》。
这电影我真喜欢,看第一眼就喜欢,玉纹穿着宽宽的被风吹得到处乱飘的袍子,往城墙根上走过去。
多么得病态,多么得感伤。
--(玉纹托老黄送盆兰花到志忱睡觉的书房里去霉味)……我们有十年没见了。
老黄倒是预备洋蜡了,我们这里一到十二点就停电了。
用不着点蜡了,我就要睡了。
我不知道来的客人是你。
玉纹……这床上少点东西……不少,什么都不少。
短条毯子,我给你去拿。
不用。
……(玉纹一笑)不用了。
后半夜还是冷的。
我不怕。
我就来。
--(玉纹返场)……明天见。
哦,没什么,让他多晒太阳。
今天天气很好。
今天有太阳。
明天也应该是晴天。
应该是。
明天见。
明天见。
好象在拉警报啊。
就要停电了。
(玉纹把灯都拉亮)开灯干什么?
反正一会儿都要灭。
(玉纹点上了蜡烛)那,坐一会儿吧。
(志诚去找椅子)恩。
(玉纹坐到了床的左手边)(志诚迎上去,玉纹别过脸,志诚远远坐到了右边)你送来的兰花味道真好。
(灯闪了一闪,渐渐熄了,玉纹哭了,志诚欲关怀之,玉纹一手遮泪一手做拒绝姿势)明天见。
(玉纹退)(隔一日城墙上)我们去哪儿。
随便你。
你怎么老没意见。
你约我出来的,你让我上哪儿我就上哪儿喽。
战前我叫你跟我一起走你也说随便我,我不叫你跟我一起走你也说随便我。
要是我现在叫你跟我一起走,你也说随便吗?
真的吗?
(他们又走了一段)我没等你,没随便。
……(志诚扶住玉纹的肩)那是我的手绢。
(玉纹指指枯枝上挂着的手绢,前一天礼言说不知道谁的手绢)你的?
你来的那天中午,将风给吹上去的。
我睡着了,手绢被风吹走了。
很无聊吧,就是这样的,我可以在城墙上呆上一整天。
……(志诚跑过去爬上树把手绢摘下来朝玉纹挥舞)--(晚上,在玉纹房间)你原来也有对我挺不好的时候。
不过后来你对我的好,对我的不好,都让我觉得好。
我分不清了。
你来了我就想,这就是那个我分不清的人啊。
别说了。
你不让我说,我就没处说了。
(玉纹哭,志诚把玉纹的头靠在肩上)怎么办,怎么办啊?
除非。
走?
除非我走。
除非他死了。
(玉纹不知所措)(又一日晚上,在志诚书房)(玉纹关灯。
志诚起身开灯。
玉纹又去关台灯。
)答应我,以后别在瞒着礼言见我了。
……听到没有?
我有事,有话要问你。
今天你们玩什么啦?
弄得小妹一身汗。
去小妹的学校了。
好玩吗?
还可以。
看样子,你跟小妹已经很熟啦。
她是我看着长大的。
已经十年没看着了吧。
还是个孩子。
是个孩子就带着她到处跑?
你瞒我。
你什么意思?
我不懂。
她是礼言的妹妹,我是她的大嫂,我得管啊。
我以后会注意的。
好吧,我去告诉礼言说我来过这里,我不瞒着他。
明天见。
别生气,我跟你闹着玩呢。
---(雾蒙蒙天气,在城墙上)你得结婚了。
乱说。
你老是吓唬我。
都三十岁的人了,再不结婚叫人家笑话。
礼言让我给你说个媒。
说媒,还乱说。
跟谁啊。
你说我乱说,又要问我跟谁算什么,你还是心里有数。
你?
你跟小妹不挺好?
别闹了,到底怎么回事?
我说的是真的,礼言让我帮你跟小妹说个媒。
荒唐。
我也是受人之托。
话我已经跟你说了。
愿不愿意在你,回头你告诉我。
你还在闹。
我说的是正经的。
这是开玩笑,礼言也不想想,他小妹才多大。
今天是小妹十六岁的生日。
我走的那年你不也是十六吗?
就是没有人给我们说媒。
照你的意思,十六岁的姑娘是可以提亲的。
那你说你愿意么。
我不愿意,我告诉你我不愿意,满意了吧?
别再逼我,别再折磨我了。
我受够了。
真后悔当初我为什么不知道找个媒人呢。
为什么不,你为什么不知道?
莫非你也是不愿意当初。
我愿意,当初我愿意。
不是你母亲不答应吗?
我母亲现在已经死了。
可是现在你已经有丈夫了。
礼言要把妹妹嫁给你,不是也挺好。
我不想你走,我也,不能跟你走。
玉纹……---(小妹生日,志诚发完酒疯,呆在书房里)回去。
我要进去。
回去!
我要进去。
回去吧玉纹。
(玉纹头靠志诚肩上,志诚把玉纹抱起,放下,又抱起,复放下。
冲出书房把玉纹锁在了房里。
玉纹轻轻扣着玻璃,由轻到重,忽然把玻璃打碎,伸出手来开锁。
志诚摊坐在书房中,玉纹踩着一地碎玻璃回到自己房中。
)-2004.11.16
10 ) 且醉且饮且不醒
残垣断壁旧书庭萧萧疏影人依旧千转百回命无常她眉眼间化不去的冷淡轻愁 他欲言又止的内疚压抑她突然迸发出激烈热情的明亮双眸 少女般俏皮的微笑 却不为他他自欺自麻自醉自说自话 终是瞒不下去了 他想成全又不舍隐约中有些愤怒 她自觉对不起他 举手投足是怯意和勇气的挣扎他狠下心自我了断 阴差阳错活转过来 她似是忽然明白了生活明白了爱 结局是两人努力想要靠近对方 笨拙 冷淡 还有未知的未来当书里的文字从嘴中说出 我喜欢民国那个时代的文字 浓的化不开的古语 想要破茧而出的新说大家都是及轻缓的 说话走路 似是怕惊动了画面里掉光了叶子的漆黑树枝错过就是错过 不能再在一起的了戴礼言很狡诈 他明白不论死成与否 他都能永远赢得玉纹他把一切看得太透彻 志忱和玉纹的忠孝礼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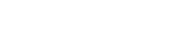























这种清冷幽寂压抑到窒息却又能嗅到一丝希望的诡异氛围让我欲罢不能
挺好的感觉,更有内心独白感,还是感觉这版更美,虽然意义有点变了。这个妹妹太疯癫了。这些人心里都在想啥针对这个版,与其理解为发乎情止乎礼,我更愿意理解为人和人之间其实还有一种微妙的感觉和感情在连着。
我试图去理解很多别人的人生,有些人的终归理解不来,这种就属。
不如老版细腻真切,现代人毕竟浮躁一些,世界变化得太快了……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屋子里幽暗冷清,透着一股年久的潮湿压抑气息。屋外是江南的春天,绿水青山,明亮自由,谁能不热爱啊。祖屋里挂着的吊环太经典了,因为我爷爷家也有。
本来就是向费老致敬的影片,所以怎敢超越他老人家呢,呵。但是,再看一遍发现,田壮壮版的这部在一些细节上把江南古镇的女人男人表现得挺到位的,比如老黄的苏沪口音,玉纹的一句“好的呀”“就来”,手势,把江南女子的那股温婉劲儿全表现出来了。小镇男子,如戴礼言,柔弱,含蓄,细腻,还读《花间词
一开口一通的京片子,太跳了,戏也尬
中国风的景,中国式的感情。隐喻很多,情感涌动也带动着观者的心情,大户人家的精致,礼义廉耻,细节都拿捏的很到位。胶片电影真好。
中国版廊桥怡梦
没看过费穆先生的原作,故无法进行比较。本片极具田壮壮风格,冷色调,压缩的对白,缓慢的节奏和压抑沉闷的情感。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片中被大量使用的隐喻:残破如鬼城般的小城、古老的城墙和白衣的女子、手绢、打破玻璃而受伤的手。其实片中的人物也都属于隐喻的一部分,在大宅院中,被严重压抑的冲动
人物实在不行,跟被人强奸似的
一直说随便,却不曾随便地私奔;一直说无碍,却不敢无碍地偷情。你就像春风一过,荡舟的歌,划拳的酒,枝杈上的手绢,残垣边的夕阳都春意盎然。我把房间的灯都拉开,反正生活总会将它们熄灭。其实,没有恨也会有战火,没有爱也能有婚姻,没有心跳也能叫活着,没有花开也可以叫春天。反正,也都没有你。
这编剧水平,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相比于费穆的版本,画面变成彩色,对比度更高,更显冷峻色调。用了很多远景,以及前景对于人物和空间的遮盖,有所掩饰和隐藏。女主的独白被隐去,转而用表情或动作等反应女主心境。对白和内容上,费穆的版本更像古典主义式舞台剧的展开手法,而田壮壮的版本更电影化,对于细节和故事内容更现实、生活化、实际(比如老黄加了口音),对于感情展示更隐晦、符合时代人物特点。个人认为这一版男女主年龄有点年轻,演员少了上一版的沧桑和沉重。
辛柏青最好,吴军次之,胡靖钒最次 抗战前后,城墙内外 经典的人物关系 希望之光 春天
把《小城之春》拍成了低配版的侯孝贤。。。。
估计观影过程若将全部精力集中在电影上会死掉
2012年看的第一部电影,没有看过费穆的原作,因而没有比较。总的来说,田壮壮的拍摄技巧和表现手法都非常到位。主角之间对话的台词,和细微的表情和动作非常值得细细玩味;而对于破落的小城,短暂的春天的描写和刻画,也自然让人联想到抗战胜利后,那个刚稍安息,即有重新陷入战乱的中国。
毫无意义的翻拍,演员的表现是灾难。
除了画面很美以外,故事情节和表演都拙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