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玛嘿玛》热门推荐
《嘿玛嘿玛》剧照
《嘿玛嘿玛》剧情介绍
每隔十二年,喜马拉雅山脚下的森林裡,挑选出来的人们戴上面具,隐藏性别,放下世俗身分,彷彿死去般的过著为期两週、与世隔绝的奇异戒律生活。在等待的日子裡,歌声无尽,舞不停歇,有人静心修炼,也有放不下尘俗的人打探彼此底细、无法抵抗原始的欲念。这是真实与虚假的界线,生与死的空隙 ,面具拿下即是毁灭。 不丹导演钦哲诺布,将修行求道转化为现代乡野奇谭,融合传说、禅语故事、舞台演出、梵唱琴颂等多重艺术形式,展开另一场悉达多的探索之旅。人性与神性的拉扯中,吟唱出千古不变的生命之歌。周迅、梁朝伟添画龙点睛的客串演出,更添意趣。 「有时,我们必须创造幻象,才能让世人看见真理」──钦哲诺布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真爱找麻烦!我的宠物恐龙主播胜负未决的战斗边城破晓动作女主:水果应援团伸冤人第二季武士马拉松2002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真实故事震撼鲜师大唐狄公案真心话大冒险大话红娘绅士乔瓦尼之岛网上卫士Hello锦衣卫行尸之惧:462航班第15条和平战士拉撒路计划第一季音乐永不停歇与凤飞再见的延续擅长捉弄的高木同学辣妹刺客3大宋提刑官浴血黑帮第五季美狄亚斯
《嘿玛嘿玛》长篇影评
1 ) 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电影?
作者:萨吾奇
拉康提出过这样的理论,小孩子在婴儿阶段,通过不断在镜子中观看自己的影子,通过自己能够控制的身体的动作和其在镜子中呈现的一一对应的反馈,确定了一个“自我”。
稍微大一点之后,这张镜子就变成了父母的表情,身边各色人物的语气和态度,老师手里的皮带,以后又变成被人类奉为真理的传统和各种训诫,你的工资和对家人的责任等等,这面镜子告诉你可以各种这样,不可以那样。
因此拉康认为这个“自我”是伪的,因为这是镜子或别人塑造/要求的“你”,是按别人的看法扭曲一个更真实的你自己的愿望而表现出来的“伪自我”,如相同一个人如果生在藏族,他不能喝马奶,如果生在蒙古就能喝,人还是一样的人,但是镜子对你的要求不一样,你按照从小培养的习惯表现出来的“你”也就是他者定义的“你”,不是真实的你自己,拉康还有一个专门的名称给这个“你”,叫他者。
“做真实的自己!
”这个口号意味着,你要服从自己最深处的想法,甚至是潜意识,拉康自己就认为把潜意识实现出来才是真的自己。
但是我们始终无法摆脱那个控制我们的镜子,即便在青春期的逆反时期,我们不过是用另一个镜子去对抗之前的镜子,当我们为了反抗父母这面镜子强加给我们的“自己”时,不过是去学“反面人物”开与之抗衡,认为这次我们做了真实的自己,但这个“反面”依然是另一个镜子。
嘿玛嘿玛中,男主角前往的密林就是这样提供展现“真实自己”的聚会地,象征地狱狱卒的人来迎接他,将他带入一个和以往世界不一样的地方,他的身份被隐藏,在这个密林之外,人的身份就像拉康说的那样是一个他者,隐藏这种身份才能真的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事,或许还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思考。
在聚会中,除了主线主角的状态以外,另一个副线是“主办方”表演的戏剧,这出戏剧围绕死亡和中阴展开。
佛教给出的中阴概念,中阴是死亡到重生的过程,按照佛教的解释,中阴期间你才会有一次机会展现真实的自己,那个阶段你将不受任何东西的控制,甚至因为阎罗要计算你的善恶德过,要判定即将去往哪里,你即便想不展现自己都是不可能的。
聚会中,每一个参与者真正表现了在另一个世界隐藏的自己。
在密林之外,他们不能窥探别人,不能随地交媾,也不能让别人喝尿,即便我们的生活中无时不刻都有窥探的欲望、性冲动和恶作剧的快感,但是这些都被整体社会的那面镜子给压抑了,不能随意的表现出来。
但在密林之中,你再也没有压抑自己的可能,就像戏剧中的死者没有隐藏任何自己善恶的可能一样,每个人完全的追随自己的内心的召唤,没有节制,没有他人的牵制。
当故事发展到高潮时,戏剧舞台的死者被投入象征痛苦的地狱铜锅里,为自己生前的所行受罪。
这暗示了主线即将步入恶业当中。
果然,主角的被面具所迷惑,误把前来和男二约会的同面具女二当成和自己暧昧的女一,在女二的反抗中他再也不能自已,犯下罪恶,又因为这个起因的蝴蝶效应而杀掉男二,男二的面具是代表善的静相白色神灵。
“做真实的自己!
”这个被西方推高到绝对真理位置的口号,却没有伦理和道德上的正义性,正如男主角的恶行是真实自己的结果一样,后现代以后的现代社会常常面临着这样的难题:我们精明于所有的知识,却同时撼动了善恶的根基,再也没有什么是善和恶,如果不是各种传统力量的缓冲,那个理性、科学、无教无神的新世界,是一个可怕的地狱,是一个没有人前来指引的中阴之道,每一个人将不得不在赤裸裸的自我的欲望下,遁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西方世界的一声“上帝已死”,让伦理成为利益的考量和暴力的规范,离开了利益,离开了诸如警察这样的暴力机器,再也没有道德的立足之地。
密林中,那个听见呼救就奋不顾身的白面神一死,道德还将如何拯救我们?
作为一个仁波切编导的作品,嘿玛嘿玛直指人性。
它让我们思考,不管在他人的规范当中还是自己的欲望当中,没有任何解脱的可能,只有无尽的轮回让我不断做出无论如何都不会正确的选择。
我们猛然发现,那个两千年前在菩提树下证得解脱之道的佛陀是那么的正确,无论你多么自由,如果离开正确的指引,那还有什么结果可得,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犯错。
二十四年后,男主角戴着双面面具再次回到密林,双面面具是一喜一悲,主面为悲,因为他还有心结未了,背面为喜,因为毕竟他在心结中似有所悟。
最后他愿意脱下自我的这张面具 ,而开始救赎的道路。
2 ) 人生无常,及时醒悟
宗萨仁波切.我的偶像。
整部片语言很少,靠的都是眼神传递和肢体动作表达情感。
这样的片子需要含金量很好才能出作品。
恕我愚昧,对佛教了解的太少,只看懂了皮毛。
1.一失足成千古恨--男主经不起诱惑,误奸了梁朝伟在剧中的女人,更是误杀梁,导致自己内心受折磨24年。
2.在森林里的舞台剧还是音乐剧?
额...随便啦.内容绝对真实靠谱,都是佛陀宣讲后,弟子以文字形式记录在佛经里的内容,真实性是某仙侠剧渡劫飞升所不能比的。
剧里所有的舞蹈动作都不是随便乱跳的,都有一定的密意,密意懂么?
不懂去恶补一下藏传佛教里的名词理解。
整场剧里,提到了无常、死亡、中阴身,包括人死时眼耳鼻舌身意的退化,以及出现的种种虚假之相--最执着的亲人呼喊你的名字等,经书里讲了,如果这个时候你不能提起正知正念,内心有一丝不舍亲人的念头,那就完了,下辈子还在六道轮回里头不得解脱。
所以啊.这部剧我还得多看多体会,温故而知新
3 ) 嘿玛嘿玛小感想
嘿玛嘿玛戴上面具,隐藏自己为了发现真我,经历生死间隙踏入那没有身份的空间没人知道你会做什么没人知道你会是谁匿名给予你勇气,躁动和力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只因一时执念,一时冲动,一时贪欲误奸人妻,失手杀夫惊愕之余,悔不当初二十四年,饱尝恶果回到原点,坦明善恶因缘和合,因果循环找到遗女,无可奈何只得给予金钱辅助,当做救赎人生无常,及时认清放弃对欲望的执着才能自若的开启证悟真理之路
4 ) 匿名之力,心之牢笼
我非佛教信徒,却从小在佛学熏陶之下长大。
首先整部影片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森林中那些类似舞台剧的画面。
给人已安宁,给人已力量。
匿名是一种力量,带上面具,你便再也不是你。
人性,欲望在面具之下,尽显无疑。
男欢女爱,这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
女人带上面具,脱下的是羞涩,洗澡可以被偷看,人群中,可以被抚摸,深林里,可以啪啪啪。
面具之下的释放,是真心,还是单纯的欲望?
影片的中间,我以为男主有真心吧,至少有那么一点点。
可是最后的最后,只是一场走肾不走心的追逐。
如果故事发展到这里,结束。
所有的人,都回到了现实生活,带上了社会的面具,身份,地位,名誉。
大部分人的结尾应该是这样的。
可是,男主却在丛林中,认错了人。
从这一刻开始,人生的列车,驶向了未知。
后面的剧情,发展紧凑。
死亡,一场无人追究法律责任的他杀案件。
结果又会是如何呢?
现实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人,在犯了事之后,试图逃脱法律制裁。
事实上,确实有很多人成功的逃脱了,其实我想问问他们,你们的内心,是否安宁,你们是否曾有过焦虑。
剧中的男主,不费吹灰之力,无人追究。
包括死亡人的妻子,也只能在葬礼最后,无助的哭泣。
可是24年的画地为牢,此生此世无法走出的牢笼,又比现实中的牢笼好了多少呢?
他的心,早已把自己困死在当年的喜马拉雅山之下,此生无法出走。
最后,男主找到了自己的女儿,希望的是救赎吗?
可是,人生很多时候,无法救赎。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为自己,种下的又是什么呢?
5 ) 起心动念即是修行
置身物欲横流的花花世界,我们戴着各种面具穿梭其中,努力表现面具应有的特质、行为、修养。
有的时间一长,潜移默化为自己的习惯,甚至面具揭都揭不下来。
而有些还是为表演行为,但还是会沉醉其中,乐此不疲。
一旦有机会,在陌生的环境,不需要面具,没有观看观众。
有多少人是本性出演?
是放纵自己的欲念,把贪嗔痴发挥的尽致淋漓,随欲所为,还是本着初心的模样,自律自省。
其实都在一念之间。
人的一生都在善恶两念间修行,行必果,自己积的善业行的恶业像天平的两端,那些起心动念、手起刀落自己怎会做不到心中有数,善业可能容易淡忘,但做的恶业会刻骨铭心,一直追随着你,折磨着你,直到有一天,你敢直面自己的过去,揭开尘封的秘密,也将自己释放。
这一刻,可能无比轻松自在。
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九九归一,初心都是教人向善,保留自身最大限度的善良。
ps. 梁朝伟自带一双辨识度很高的迷人眼,即使带面具只一下即可辨认。
他那一笑,就像宗教,深不可测。
面具很好看,音乐吟唱很好听。
6 ) 作为成年男性,带上面具想到的是性欲
如果是我头戴面具,我的第一反应,心底的本能欲望,就是尽量辨别哪个是女人!
然后就是:啪啪啪!
讲真,是内心第一反应。
看来还是本能性欲望驱使,而且脱离伦理道德法律,就像在梦中潜意识一样,知道这是梦会醒,所以肆无忌惮,欲望潜意识的体现吧。
(不知有人有同感吗)这才是真实的本我吧,回归到现实,谁又逃的过救赎忏悔的内心呢?
那么宗教性就出来了---修行。
同时我也很好奇,如果是你女性,戴上面具到那里的本能第一反应,面对周围这些面具,是什么呢???
7 ) 《嘿玛嘿玛》 匿名的力量
本片由不丹导演 宗萨钦哲仁波切 执导,参加了不久前落下帷幕的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周迅和梁朝伟无酬客串。
导演宗萨钦哲仁波切不仅是导演,《高山上的世界盃》斩获釜山国际电影节大奖,而且是不丹藏传佛教的喇嘛。
影片讲述的便是这个藏传佛教每12年举行一次的重要仪式:由长老亲自在各个地方追踪、寻找、锁定一个个人,让他们来到与世隔绝的不丹深山密林之中,戴上面具、隐匿身份和性别,在规定的界域内生活两周。
解读这样的哲理影片需要丰富的发散和极其敏感的感知力,目前的我还达不到这个水准,所以先谈一谈镜头语言,解读剧情重点放在后面来说。
这更像是一篇观后感。
本片的镜头语言十分简约,导演曾称他非常喜欢小津安二郎的作品。
经常会给一个主角在空虚与迷茫之中冥思的镜头,天空和丛林的空镜头,以及随情感一起绵长起来的慢镜头,长焦模糊视线产生的那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迷离感。
这种风格很能表现出一种肃穆、神秘的感觉,契合着密林深处的神秘活动特有的仪式感。
这种观感能引导观众把思绪投向深处。
影片的中心词是“匿名”,原片中所说的“匿名是一种力量”。
在仪式过程中,每个人都要隐姓埋名、戴上面具、穿上长裙,姓名、容貌、性别都被一一抹去,每个人都以“赤裸”的状态在生活。
这种状态是很容易让人陷入前所未有的迷茫之中的。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以名字相称,自己的名字就代表着自己的身份,“我是谁?
”这个问题似乎有了确切的答案。
但是实际上,名字不过是一个代号而已,将这个代号拿掉,“我是谁”可能就不得而知了。
正如原片中的长老所说,匿名之后我们便来到了“生与死的边缘”,生命的意义就藏在这名字之中,与过去的“我”诀别,真正的“我”在匿名的状态下才会慢慢展现,这是一个重生的过程。
匿名同时也表示着没有人知道你的身份,社会秩序和伦理失去了建立的基础,也就没有人会对你进行道德约束。
因此压抑已久的动物本能就会在匿名的状态下爆发出来。
由此可见“名字”这个发明本身,是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外化了每个人的“自我”,自愿将身份贡献出来,这是建立社会的重要条件。
在这个意义上,这部片子的现实隐喻意义非常强。
“名字”也就是身份,它束缚着你,一旦丢掉这层束缚,解脱之后,是任由本能为所欲为,还是克制隐忍潜心参悟,便是原始与文明的区别。
匿名之后,身份和容貌都不复存在,两性之间的吸引便是一种很纯粹的东西,要么是出于本能,要么是出于真心。
匿名有这样一种洗去偏见和心机的净化力量。
在原始丛林中,篝火光亮的的映衬之下,两只手十指相扣再缓缓抽离,两双处在面具之下的眼睛窥见了彼此的心。
但是匿名也会让人体验到人生的荒诞无常。
片中的主人公在追求爱人的时候,阴差阳错地爬到了另一个女人的身上,他慌忙起身,还杀死了前来追赶他的人,从此过上提心吊胆的生活。
他在24年后再度来到这里参加仪式,他纵火引开守卫,进到长老帐中质问他“你这辈子犯过错没有?
”匿名让他错失姻缘还背负了一辈子的道德负担。
影片最后他来到酒吧找寻自己的女儿。
四处好像依然是匿名的人们。
我们习惯了自己的名字,却早已忘记了没有名字才是生活的常态。
匿名的力量,在于透过面具,看清面具底下真正的东西。
8 ) 如果你是我的信仰
如果你真正拥有了自由和真正的自我,你会怎么做。
在喜马拉雅山下的密林里,有一个每十二年才会组织一次的活动,被选中来到这里的人,将会戴上面具,隐匿世俗身份度过两周循守清规戒律的与世隔绝的生活。
在这里,你不能打探别人身份,不能做违规的事,否则将被摘下面具公开身份失去此活动的资格并会被关押起来。
在这两周里主办方会在“原始”森林里举行各种带有地方性和宗教性的活动,诸如舞台剧,歌舞,吟唱等等。
参加者就在这些活动的观看与参与中修习自己,为了找到真正的自我。
这是有着深厚的藏传佛教背景的宗萨钦哲仁波切拍摄的电影,《嘿玛嘿玛》。
电影在叙述和画面上都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有着诸多的隐喻与禅意。
比如聚会每十二年才会举办一次,十二隐喻“十二因缘”,包括无明、行、识、名色、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
它们一环扣一环,意味着轮回不止。
这一活动以现实的眼光来看,犹如一个俱乐部,一个伊甸园,或一个乌托邦。
而电影的主线也选了一个很现实的切入方式,选了“面具”这一符号作为切入点。
面具的镜面效应导演说面具这一符号的由来,缘于网络聊天。
在网上人们躲在各种ID背后,可演化出各种身份及内在反应。
而“匿名是种力量”,因为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影片中的男主在加入聚会的前几天,一直小心翼翼的遵循着规戒,对别人的违规行为惊讶的捂起自己的眼警示自己,比如面对帐篷里的别人的欢爱,偷偷翻别人东西窥探别人身份的人,把瓶子里的酒喝掉又装入自己的尿液的人。
在“匿名”的盾牌下,人的本性恣意暴露。
如果他一直秉持自己,坚持到最后两周时间的结束,或许他能从中有所收获,就像活动举办的初衷一样。
而渐渐地,在目睹了身边一系列掩藏在面具之下的违规行为后,他的本能也蠢蠢欲动起来,最后在他追逐他的暧昧对象要去幽欢时,却意外的引发了一场强暴和杀人事件。
面具的隐藏作用没能让男主和前来参加聚会的人借助这一形式认识更深层次的自我,反而成为了人为所欲为盾牌。
面具的遮盖反而更显现了人的本性,是面具使人变得赤裸裸。
自由和自我,在此处成了把人引向地狱的缘由。
人性与自由的冲突显而易见。
而回到现实,人们在俗世生活中,迫于生活、工作的诸多身不由己,事实也在以各种面具在不同情形之中扮演着各种各样的人,这种无形面具之下的样子是人的真实状态,还是森林里真正的面具下袒露本性的是人的真实状态?
人究竟想要何种形式的真实的自我。
如果说现实种种不得已是对人的规范和枷锁,让人有身不由己的悲哀,和生出对自由和自我的向往。
那丛林里完全自我释放却也有着让人堕入罪恶的深渊的危险方式是否就是真的自由。
哪种形式能让人真正超脱呢。
面具也是一种无解的镜面。
无常与因果电影的名字《嘿玛嘿玛》,在不丹语中是“很久很久之前”的意思,字面就带有因果的意味。
影片中的副线,是由聚会的主持者,唯一不戴面具的叫“阿界”的人带领一些土著人所展示的各种歌舞表演。
在森林中明亮的篝火里,他们时而在载歌载舞,时而吟颂,或是表演某种舞台剧,其中比较醒目的是“尸陀林主之舞”,在表演的过程中,作为主持的阿界会吟颂出某些带有隐喻的字句,比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尸陀林,乃弃尸之处。
尸陀林主为掌管尸陀林之神,护持在尸林中修行的佛法者。
歌舞围绕死亡和中阴展开。
中阴指死亡和再生之间的中间状态,是真我醒觉、出离轮回的契机。
如果男主一直如最初那样谨言慎行的参加着各种仪式,并认真观看和聆听演出的教义,或许会是另一个结局。
然而连他自己都不会想到结局却是在那样的想象之远,他在一个女性学员的撩拔下终于本能的欲望暴发,追逐过程中错认了人,先是强暴人妻后又杀死人夫。
一时的动心起念,铸成弥天大错,致使他接下来二十四年中深陷罪责的深渊。
而那对夫妇,如果不是一开始公开在帐篷里欢爱,后又在森林里以改换面具增加性趣,也不会是伤与死的结果。
无常与因果在此体现的淋漓尽致。
你是你自己的主人影片中,主持者阿界在一种带有巫性的气氛里,一边舞动着一边念念吟颂,其中也有这样一句,“你是你自己的主人,你是自己的建筑师。
没什么命中注定,没什么自由意志。
”如果以无常来说,每一种无常都导致某种不确定的因果,那也就没什么命中注定,人也没有选择的自由意志。
那为什么还要说,“你是你自己的主人,你是自己的建筑师”?
自己的理解是(就电影来说),人通常都会借助神明的名义来达成某种仪式或效果,比如遇到灾难时,有莫大的誓愿时,仿佛通过某种仪式完成与神明的沟通,人的内心就实现了安宁或救赎。
而这种方式终究还是通过外在存在或虚设一个神明才能实现,是一种 “借助于外在”的方式。
而佛教是不相信有神明的存在的,佛教讲究的是个人的证悟,证悟的是某种真理。
个人证悟不是通过什么神明,而是通过修习经义使自己明通某些奥义。
是一种“借助于内在”的方式。
于是,无论你遇到什么事,在你的生活和修行中,你才是你自己的主人,你是自己的建筑师,你自己决定在某些时候你是一念执著,还是一念放下。
去走什么样的路。
证悟的工具佛法教人不要执著。
只有放下执著才能前行,执著会构成一个个障碍或魔鬼。
佛法也说,不要对欲望执著,并不代表不可以有欲望。
欲望有时能使人顺行,那就不要管它,如果欲望已经成为人的阻碍,那就放下对欲望的执著。
于是不禁要问,佛法教人放下对一切事物的执著,那为什么修习佛法的人还要对求得证悟和真理一直执著呢。
对于此,佛法又说了,“如果你手指里有根刺,你得需要另外一根刺,才能把这根刺取出来。
所以,为了摆脱所有其它的执着,你需要保留一个执着——对证悟的执着,作为暂时的工具和途径。
一旦你真的证悟,那么即使是对证悟的执着,都会消失。
佛教里有“乘”的概念,也分大乘小乘,“乘”就是“vehicle”(交通工具),一种工具和途径。
当你乘坐一辆车到达了目的地,你就不需要停留在车里了,你自然会下车。
”回到现实里,如果一切皆修行,那平凡庸常的生活里,什么才是我们的“乘”。
如果你是我的信仰以上种种只是基于电影中的情节有所针对性的阐释,并非自己就坚信如此。
比如,当人们通过与神明沟通来完成自我救赎之时,我觉得这其实是种能量交换,不管神明是否真的存在,也只是一种途径。
这也不是什么有神论,只是一种哲学。
比如,佛法让人放下一切执著保留对证悟的执著以求得真正的证悟,在佛法里或许这是途径。
但对于不信佛法的人,我反而觉得佛法让人放下的执著恰恰是人成功和自我救赎的途径,甚至欲望也是。
以前的时候,问师长,如果不信宗教,也不执信任何一门哲学,哪我们信什么,师长说,自然。
遵从自然,找到其规律并在某种平衡里学习与成长。
后来觉得,这不就是道家吗。
道德经,道者,不就是自然和宇宙的规律吗,而德者,不就是掌握这些规律的能力和遵从这些规律的程度吗。
而经者,不就是以上两点的总结吗。
(哈,我浅薄的认识。
)但事实,生活里,人依旧是那惶恐和荒乱的猴子。
什么都无着我心。
于是,不禁呼之,“如果你是我的信仰”。
耶稣基督,释加穆尼,穆罕默德,圣经金刚经古兰经,超然道法,庄雅儒家,共产主义社会义辩证唯物主义……,究竟该信哪个。
故事里说,如果你信了,从此你便有了保护。
如果你不信,你就永远痛苦。
看完电影时,“如果你是我的信仰”跑到嘴边,转念又想,如果就把一个人当作信仰也是好的。
而这种信仰或许就叫爱吧。
而收回来说,许多在某些领域深入并有所作为的人,最后似乎还是选择了皈依,比如许多学者,明星等。
不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大约是为了内心有所依靠吧,只取宗教最本质和浅简的作用,而无关什么哲学和奥义。
而再回到自身信什么的问题,除了依旧信仰自然,我觉得还可以信仰艺术。
艺术在这里指的是美和审美。
无论是纯粹的艺术还是关乎了宗教或政治的艺术。
现在觉得,艺术都是建立在某种哲学和审美之上的,如果没有背后这种哲学和审美,这种艺术也就不存在了。
而艺术里的逻辑就是循着这种哲学来流动的,许多艺术之所以让人看不出美,看不出它的逻辑,并不是它不存在逻辑,而是这种逻辑在艺术里过度压缩了。
需要审美来把它们释放出来。
而自然的美,是不是就是毫无道和逻辑的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们依循在某些时序的规律里。
电影的创新性与审美再回到《嘿玛嘿玛》这部电影本身。
影片是由宗萨钦哲仁波切拍摄,他是佛教界的一个传奇人物。
是藏传佛教的导师,是多部著作的作者,也是世界著名导演。
在宗萨钦仁波切看来,电影是一个沟通的工具,但对比其他工具,电影叙事的方式更加微妙:“有时候我们必须制造幻象,才能让世人看见真理。
”导演如是说。
这部电影以“面具”这一符号从现实层面切入,以面具作为形式,既带有某种神秘感,又使得电影的叙述行进中散发着艺术的张力。
由于导演的佛教背景,也使得思想的表达有着宽敞的路径,如在片中有主副两条线,一条是男主的体验主线,一条是带有地域和宗教特色的诸多仪式的展示。
这使得影片无论是在类型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带有别具一格的审美。
有着某种艺术性和实验性。
比如森林里犹如来自原古的歌舞,各式各样的面具,简少的台词。
看的过程,让人觉得那一张张特写于眼前的面具有着某种美感。
还让人想到了流行于盛唐的昆仑奴面具。
电影走到现在,创新已经成为电影最有价值的部分,无论是剧本摄影剪辑等等哪种形式的创新。
而在创新的基础上,和电影所展示的美即电影创作层面的审美,是电影最终是否会成为好电影的重要因素。
这部《嘿玛嘿玛》因其自身背景的独特性而有着与众不同的创新性。
但作为爱好文艺片的人,这部电影至多打七分。
因为基于个人偏见,我觉得文艺片首先得美,其次才是它表达的主题。
而这部电影除了占了先天独特性,并不具有打动人心的美。
再是掩盖在晦涩表述之下的主题并不晦涩,相反是显而易见的。
而在表达“匿名是种力量。
没人知道你是谁,这就是你的力量”这一面具下人本性的荡漾摇曳之时,导演还是迎合世俗选择了最浅显的性欲望来展示。
恰当又直白。
而在叙述上有灵气的一笔是,在电影的开头,当周迅盯着镜子中的自己一直看时,她似乎由着直觉发现了什么,然后镜头就切换到二十四年前男主初入森林中的场景。
而她所莫名发现的正是自己的身世。
这个跳转正是从此开启她身世的由来。
永恒的轮回与宗教飘零首先电影在形式上实现了首尾呼应的环形结构。
从开始在舞厅里面对镜面凝视的周迅开始,到父女最后相见于舞厅。
在形式上和剧情上以及人生上圆满展示了因缘和合。
而作为主题剧情的镜面具面,无论你是在现实的规范之中,还是森林里自我的欲望之中,没有任何解脱的可能,只有无尽的轮回,轮回在“无论如何选择都不会正确”的无常里。
影片的最后,当男主二十四年后又回到森林找寻自己的罪恶之源时,依旧每十二年举行一次的聚会还在,只是形式早已被现实的风溶解,曾经的庄重仪式变成了轻松的表演,梵唱琴颂变成电子音乐,手搭的布帐篷变成了露营帐篷。
如此的对比大约也有导演对宗教飘零的感慨和无奈吧。
佛颂依然,良人何踪。
而电影的英文名字叫,“Sing Me a Song While I Wait”,翻译过来是,在我等待之时请为我唱首歌。
这大约也是一种“心之忧矣,歌且谣之”的情怀吧。
花果既已飘零,灵根如何自植?
科技时代,全球化时代,宗教与时代、与世俗的碰撞之难免,因因如是。
9 ) 作者不一定懂拉康,就是扯一下
拉康提出过这样的理论,小孩子在婴儿阶段,通过不断在镜子中观看自己的影子,通过自己能够控制的身体的动作和其在镜子中呈现的一一对应的反馈,确定了一个“自我”。
稍微大一点之后,这张镜子就变成了父母的表情,身边各色人物的语气和态度,老师手里的皮带,以后又变成被人类奉为真理的传统和各种训诫,你的工资和对家人的责任等等,这面镜子告诉你可以各种这样,不可以那样。
因此拉康认为这个“自我”是伪的,因为这是镜子或别人塑造/要求的“你”,是按别人的看法扭曲一个更真实的你自己的愿望而表现出来的“伪自我”,如相同一个人如果生在藏族,他不能喝马奶,如果生在蒙古就能喝,人还是一样的人,但是镜子对你的要求不一样,你按照从小培养的习惯表现出来的“你”也就是他者定义的“你”,不是真实的你自己,拉康还有一个专门的名称给这个“你”,叫他者。
“做真实的自己!
”这个口号意味着,你要服从自己最深处的想法,甚至是潜意识,拉康自己就认为把潜意识实现出来才是真的自己。
但是我们始终无法摆脱那个控制我们的镜子,即便在青春期的逆反时期,我们不过是用另一个镜子去对抗之前的镜子,当我们为了反抗父母这面镜子强加给我们的“自己”时,不过是去学“反面人物”并与之抗衡,认为这次我们做了真实的自己,但这个“反面”依然是另一个镜子。
嘿玛嘿玛中,男主角前往的密林就是这样提供展现“真实自己”的聚会地,象征地狱狱卒的人来迎接他,将他带入一个和以往世界不一样的地方,他的身份被隐藏,在这个密林之外,人的身份就像拉康说的那样是一个他者,隐藏这种身份才能真的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事,或许还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思考。
在聚会中,除了主线主角的状态以外,另一个副线是“主办方”表演的戏剧,这出戏剧围绕死亡和中阴展开。
佛教给出的中阴概念,中阴是死亡到重生的过程,按照佛教的解释,中阴期间你才会有一次机会展现真实的自己,那个阶段你将不受任何东西的控制,甚至因为阎罗要计算你的善恶德过,要判定即将去往哪里,你即便想不展现自己都是不可能的。
聚会中,每一个参与者真正表现了在另一个世界隐藏的自己。
在密林之外,他们不能窥探别人,不能随地交媾,也不能让别人喝尿,即便我们的生活中无时不刻都有窥探的欲望、性冲动和恶作剧的快感,但是这些都被整体社会的那面镜子给压抑了,不能随意的表现出来。
但在密林之中,你再也没有压抑自己的可能,就像戏剧中的死者没有隐藏任何自己善恶的可能一样,每个人完全的追随自己的内心的召唤,没有节制,没有他人的牵制。
当故事发展到高潮时,戏剧舞台的死者被投入象征痛苦的地狱铜锅里,为自己生前的所行受罪。
这暗示了主线即将步入恶业当中。
果然,主角的被面具所迷惑,误把前来和男二约会的同面具女二当成和自己暧昧的女一,在女二的反抗中他再也不能自已,犯下罪恶,又因为这个起因的蝴蝶效应而杀掉男二,男二的面具是代表善的静相白色神灵。
“做真实的自己!
”这个被西方推高到绝对真理位置的口号,却没有伦理和道德上的正义性,正如男主角的恶行是真实自己的结果一样,后现代以后的现代社会常常面临着这样的难题:我们精明于所有的知识,却同时撼动了善恶的根基,再也没有什么是善和恶,如果不是各种传统力量的缓冲,那个理性、科学、无教无神的新世界,是一个可怕的地狱,是一个没有人前来指引的中阴之道,每一个人将不得不在赤裸裸的自我的欲望下,遁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西方世界的一声“上帝已死”,让伦理成为利益的考量和暴力的规范,离开了利益,离开了诸如警察这样的暴力机器,再也没有道德的立足之地。
密林中,那个听见呼救就奋不顾身的白面神一死,道德还将如何拯救我们?
作为一个仁波切编导的作品嘿玛嘿玛直指人性。
它让我们思考,不管在他人的规范当中还是自己的欲望当中,没有任何解脱的可能,只有无尽的轮回让我不断做出无论如何都不会正确的选择。
我们猛然发现,那个两千年前在菩提树下证得解脱之道的佛陀是那么的正确,无论你多么自由,如果离开正确的指引,那还有什么结果可得,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犯错。
二十四年后,男主角戴着双面面具再次回到密林,双面面具是一喜一悲,主面为悲,因为他还有心结未了,背面为喜,因为毕竟他在心结中似有所悟。
最后他愿意脱下自我的这张面具而开始救赎的道路。
/结语/“宗萨仁波切将电影视为现代的唐卡,万般都寓佛法于其中。
他以电影的虚拟实境,巧妙的比喻我们身处的幻想世界;而证悟的过程就仿佛脱去妄念所带来的层层蔽障,了解因缘的善变与无常;因而放下我执,迈向觉醒之路。
”
10 ) 或许该将它沉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Hema, Hema.......很久很久以前这部电影迄今为止我忍不住抓住在台湾的机会,看了两遍。
从来没有一部电影将我带到这样深的层次去看待我当下的人生。
从主人公一出场,部落首领就一直在强调,“匿名是一种力量”。
当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人认出我们,回到最初的干干净净。
我们会做些什么呢?
会想做些什么呢?
匿名是一种力量,就像网络评论,像我们每一个独处的时刻。
我们也许会为所欲为,以为这一切都不用承担,都可以逃脱。
主人公逃了,但是二十四年之后,内疚却成为一种折磨,相比这种痛苦,暴露自己的面容,其实又算的了什么?
我一直不住的想,当主人公在完全干干净净的时刻,为了逃离尘世的所有纠缠,他想去体验干干净净的人生。
可是在这片完全的空白世界里,他还是忍不住再一次陷入纠缠。
有人和他一样忍不住单调,忍不了寂寞。
于是欲望就这样荒谬地发生,甚至都不知道对方的面容,不在乎对方真的是谁,仅仅是几个动作,几个声音,被引发的伤害就这样不可收拾了。
看到影片的中间,我曾以为那是爱情。
然而当一切揭开真实的面孔,我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失望。
也许每个人有不同的解读。
这篇电影,只能说对我来说信息量太大了,感觉那就是活生生的自己。
我的现在,我的此刻。
然而有一个人,真的展示给我们,一遍又一遍的,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是怎样发生的。
导演在片中,展示了一个生与死的交界。
也许生死听起来像一场戏剧,一个演出,但却真实的发生着,发生在任何一个出乎意料的时刻,发生在甚至我们满怀希望,带着微笑和期待去迎接新的改变的时刻。
就如片中的梁朝伟所扮演的角色。
到死亡的那一天,正是他满怀希望,换了一副微笑面容的时刻,如此讽刺,又如此地出人意料。
而对于有佛教背景的人们,这部影片就更是演示了我们的当下,它即是生与死的交界,即是中阴。
所有的一切都如同面具。
那些名声,身份,相貌,行为,欲望,愤怒,这所有可以更换的一切,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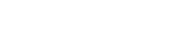



如果说生活的本质是无数因为活着而衍生出来的补充物,那么戴面具这个意象正意味着抹灭掉活着以外的所有属性,体验既无外物又存自我的灵魂本真。所谓本真便是卸下,卸下的是外物,卸下的也是人格面具,也是人类为各类社交行为而准备的心理建设。自此愧疚如同利刃直击魂魄。哎,一戴一卸之间便是禅机。
什么暖蛋玩意,天天他妈拿着宗教当宝了,一群原始未开化的人。
女主那个妹子太美了啊!戴面具都超美!
很可爱
如果不是周迅和梁朝伟有多少人会去看?立意不错,高度很高,电影…真的没有张力
噱头居多,但是幻象犹存。
很有意思的设定,但总觉得结尾应该有更好的处理,而不是简单的“24年后”
電影最有趣的部分,最能彰顯自然主義之美的部分,正是那些沒有台詞的部分,對失語和無面的符號結構,可以有千萬種方式,然而一旦出現了台詞,薛定諤的可能性消失了,創作者的高傲向觀眾低了頭,或許也正如此,電影最終的落於以入世出世。無論是從人類學的角度,探索人的特性湮沒於共性時社會化的可行性,還是從佛學的角度,思辨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說的越多,思考的枷鎖便越重,未知的樂趣便越少,都已經做了那麼多減法了,到頭來卻終究缺了如拈花一笑的節制。周迅的幾場客串,仿佛重遇了孫納,又似瞥見了東東,而梁朝偉的幾場客串,則恍惚間回溯幾十年,又遇見《阿飛正傳》的無名賭徒。
为了迅哥儿看的,没看下去。。
故事和意思其实蛮好理解,就是一堆人带着面具我看着就呼吸困难特难受。开始我以为在看《大开眼界》,然后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被杀瞬间跳到了狼人杀,24年后一言不合开始普通disco尬舞了也是吓了我一跳。梁朝伟和周迅还不如不露脸。反正片子不和我口味,我还是喜欢人间的东西,仙界就算了吧。
每隔十二年,喜马拉雅山脚下的森林裡,挑选出来的人们戴上面具,隐藏性别,隐藏身份,与世隔绝一起生活两周。导演展示的是,这些被挑选出来的,想要过隐世生活,想要认识自己的人们,在这里,做的事依然是杀戮,小团体,性欲的渴望——戴着面具不知道长相可能让他们觉得更刺激?里面的领导说,匿名是一种力量,能有什么力量呢,现在的网络不就是可以匿名吗,善良的依旧善良,而罪恶则放大了滋生。
真的挺难形容。符号与象征溢出了电影本体。也许,对藏族文化和秘教有更多了解,会好些吧。
no id no moral,but inside is mine、contorl it and let it free
什么鬼
影片真是简练、形象到爆,只有跳脱出电影陈规的真正的艺术家能奉献如此般影片
原始奇幻风 从剧情角度来说算不上强暴吧 只是误上了 两个女的刚好换了一样的面具 也要怪这两夫妻搞什么Cosplay
看不懂系列只知道明明是大好壮丽风景导演却拍成深山老林的感觉
对男人来说,皈依佛教不如皈依一个女人,女人是男人最好的修行。英文名挺好的,sing me a song while i wait
佛教和夜店这么另类的拼合,可能在于二者拥有共同的主题:虚无。
时代更替的桥段还是很震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