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剧情介绍
在得奖首作《索尔之子》以破格观点呈现纳粹集中营的人间地狱后,拉斯洛·奈迈施将深焦镜头再推前,凝视一战的世道崩塌。神秘孤女爱丽丝来到布达佩斯,欲在亡父创立的帽子名店求职竟被拒门外,由此开展一趟追寻兄长恶魔幽灵之旅,重回过去,揭开家族的隐藏真相。延续前作风格,长镜紧随爱 丽丝穿梭暗黑时空,聚焦局限观点、狭窄视角,如梦魇般朦胧影像的压迫感袭人而来;以家族老店残留的微光,斜照文明的殒落。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王者归来黄飞鸿独自去逃欢24小时营业名门劫被遗弃的死者厄普肖一家第三季预定婚期30枚银币第二季自白UFO计划绿色婚礼唐顿庄园第六季戴安娜:音乐剧九幽寻宝录蓝色骨头燕山派与百花门大爱撑天我和我的传奇奶奶密令1949百慕大三角:多彩田园曲赵世炎触火之恋丧尸出笼:血脉半之半假凤虚凰第三季梦比优斯奥特曼外传亡灵复活樱姬幸福与分数无关小飞侠彼得潘炒作之家
《日暮》长篇影评
1 ) 啊!!!!!活生生被导演激怒了!!!!!
先剧透一下。
我觉得这是一部必须被剧透了之后观众才能耐着性子看下去的影片,否则真的要被导演搞的很烦。
影片讲的是一个有一脸不招人喜欢的神情的中年女孩来到布达佩斯一家帽子店门前,这家店是她父母的,后来被意外烧毁了,两岁的她被送去孤儿院。
现在成人的她回来了,想在这家店里做一名帽子女工。
新任老板先是拒绝后又接受了她。
她又冥冥中得知自己有个哥哥。
但所有人都对她哥哥这个人讳莫如深。
于是她拼命想找到哥哥。
后来也没遇到什么困难她就找到他了。
他哥是个暴力帮派的头头,本来她哥想撵她走,她死活粘着不想走,她眼睁睁看着她哥杀人放火。
这下她又想走了,她哥又不想让她走了。
纠缠了一会,她走她哥追,后来她用船桨把他哥打死在湖里了。
她回去找帽子店老板,生活继续。
帽子店要接待国王皇后,店里上上下下的忙。
女孩又冥冥中觉得不对劲,结果她发现帽子店的女孩们要被选中一个送进皇宫,她得知之前有一个帽子店女工就被选中送进皇宫,她特别想知道这些女孩会咋样,于是她趁被选中的女孩还没有上马车的时候就自己跳上马车被送进皇宫,皇帝和几个男的看到并不是被选中的女孩被送来了,也没说什么,就让她试戴了几个帽子然后让她喝水。
女孩觉得那个水不能喝,就歇斯底里的推开皇帝跑。
皇帝也没有为难她,就放她走了,她出门的时候看到那个真正被选中的女孩走向了皇帝的房间。
她特别幻灭,她也终于理解了她哥,原来她哥早就发现自己的父母把帽子店当作秘密妓院给皇帝送女人,她哥就把自家店和父母一把火给烧了,现在轮到这个妹妹了,她鬼使神差般地她穿上她哥的衣服回到她哥的老巢,结果聚集在那里的人们高喊着她的家族姓氏开启了一场新的暴动,暴徒冲去帽子店烧掉了店铺杀死了老板。
影片的结尾是那个女孩像鬼魂一样怒目圆睁出现在一战的黑色战壕里。
影片结束。
故事就是上面讲的那些。
现在来讲为什么导演彻底激怒了我:首先,导演罔顾内容需要而强行选定了形式,主要就是为了秀他的拿手绝活:第一视角跟拍。
这个技术在他的第一部影片《索尔之子》里取得了成功,令人愤怒的是年纪不算老的导演就像学不会新把戏的老狗一样在他的第二部长片里故技重施,结果就是这部影片被他的第一视角跟拍彻底的搞死了。
《日暮》是一部彻底的失败之作。
形式极大限制了内容的需要!
相信没有被剧透的观众看了十分钟之后就能感觉到一些不舒服。
这个总是一脸愠怒的女人到底是谁?
要干嘛?
观众看不到她的全身,而是永远象半尊胸像一样的特写镜头,永远一张令人不安的脸。
永远象鬼一样飘来荡去。
这尊胸像按照导演的意图,在抹去了所有必要情境,省略了所有细节承接,忽视了所有人物内在自主性之后,她自由的仿若上帝,想去哪就出现在哪。
公爵城堡,暴徒老巢,布达佩斯任她四处闯荡,帽子店任她进进出出,皇宫也无法设防。
第一视角镜头成功印证了人物内心?
第一视角真实还原了布达佩斯的风貌?
no!
帽子店门前方圆一里地的面貌都看不到,女演员像傀儡一样被导演扯着线伸手抬脚,导演野心勃勃的将女演员作为摄影机而呈现的视域范围还不如一只复眼苍蝇,纯粹的卖弄肤浅的技巧,毫无意义的制造困惑与焦虑!
我一直都在说“女演员”而不是“女主角”。
这个长着一张令人厌烦的脸的可移动半身女子胸像是女主角吗?
谁能说出她的动机,她的行动,她的情感,她的性格?
能对这位女演员在剧中扮演的人物进行任何描述只能在看完影片之后才能做出(前提还是你能看明白导演到底讲了个啥)。
整个观影期间,任何观众都无法对这个半身女子胸像有任何理解和认同。
这部影片没有主角,那位女演员只是导演用来制造自己风格的工具,是导演悬挂在镜头前面的木偶,顶着第一视角真实的羊头卖着导演自己故弄玄虚的狗肉!
这个女演员只有在影片开头和影片结尾的两个短暂瞬间为自己赢取了一点作为演员的尊严。
影片开头,摄影机正对着她的脸,揭开面纱,试戴帽子。
影片结尾,她身着护士服站在战壕里,摄影机正对着她的脸。
对于演员来说,这两个瞬间才让她短暂取得了自己作为一名演员的合法性,但同样是这两个瞬间让导演的失败更加明显:除了开头和结尾,这个法西斯一样的导演篡夺了演员所有的权利,将自己的恶意操纵贯穿始终,他居然可以如此傲慢的实施自己的暴政,还颇为为得意的想要获得电影节的赞誉?
所以戛纳拒绝了他。
只有威尼斯,这个法西斯一手创办的,现在只能经年吃着戛纳的残羹冷炙的电影节接待了他!
(好吧,威尼斯这个是纯粹为骂而骂。。。
)最后再扯点宏观,这部电影到底要表达什么?
《索尔之子》本来就是一个政治正确到无法受到任何质疑和嘘声的主题,在那种极端环境下,唯一的视角,摒弃一切杂物的情境,人物情感和行动的无选择性可以被观众迅速理解和接受。
所以导演的第一视角跟拍这个“花活儿”让他获得了成功和赞誉。
而《日暮》不是一个发生在极端环境下的故事,导演在开篇和末尾增添的也许不必要的注脚(开篇文字和末尾一战)很明显的表明他要讲述的是一段历史。
历史是复杂多义的,历史的大忌是挑拣出一个碎片以偏带全对过去作出解释,在历史叙事中任何交代不明或者事实混淆都会令观众拒绝接受和进入影片中的故事和人物。
《日暮》的导演做的更过分,他不是回避复杂,他是挖掉了所有历史的细节,他别别扭扭的讲述了一段旧事,要表达的居然是他俗气的不能再俗气的狭隘的民族情绪和爱国主义观。
影片开端的一屏文字交代了故事背景:多民族多语言环境下的奥匈帝国,繁荣兴旺的布达佩斯。
这个开篇的注脚要么多余要么导致了影片的歧义。
影片中任何时刻观众看到多民族了吗?
如果不是了解奥匈帝国历史的人,看着影片里说同一种语言的人谁分得出来个民族?
影片是在称赞(或者反讽)奥地利皇帝治下繁荣兴旺的布达佩斯吗?
完全没有,影片只表现出单维度的阶级矛盾(暴民洗劫公爵府可能是因为繁荣掩映下的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
作为一个匈牙利人,原则上怀揣着对母国的热爱与骄傲,在影片中对奥匈帝国皇帝进行了无情的谴责(尽管在电影中能看到这位皇帝唯一的罪恶就是在民间挑选美女供自己和其他贵族享乐)。
多民族,繁荣昌盛,一切的矛盾,国仇家恨,在影片中似乎都缩减到影片中的帽子店了,在影片中新店主就将其称为文明的巅峰。
新店主利用昔日店主的姓氏装裱品牌以接待皇室,一个被贵族认可的帽子品牌。
这家文明巅峰的帽子店是一种隐喻吗,奥地利吞并匈牙利就像这个新店主一样是无耻的鸠占鹊巢?
好吧,导演挚爱的母国就浓缩为一个帽子店,而实际上这家店一直是奥地利皇帝的秘密妓院。
(不重要的八卦:茜茜公主不幸福的婚姻大家现在都知道了,不知道的是深爱茜茜公主的弗兰茨皇帝也在这家帽子店里买过春?
至少导演是这么暗示的。
)影片末尾,导演让故事结束于如地狱般黑暗的战壕。
这个结尾对于前面整个铺陈展开的故事来说突兀而牵强。
如果不是在片尾将一战与影片故事强行绑定,在影片进行中的任何一个时刻,有什么东西能让观众预测到影片讲述的故事和影片里的人物就是将要不可避免的卷入战争?
战争压根不是那家帽子店和女演员的逻辑结局,这个结尾来的真是莫名其妙毫无意义。
唯一的解释就是导演刻意要给影片增加的宏大面向,《索尔之子》讲述二战,《日暮》讲述一战,为什么不呢?
我就是这么一个有历史责任心的导演啊,又这么有才华,我用我独特的艺术风格为观众呈现了两次大战的眼睛,我可太牛逼了。。。。
这世界就怕野心勃勃的知识分子在那胡说八道!
不像二战,参与一战的所有欧洲国家没有一个是无辜,没有一个可以代表正义,女主角站在战壕里能说明什么呢?
她是被迫参军的吗?
匈牙利的纯洁只能在于证明她是被动卷入奥地利人发动的不义之战。
可是看上去她也不是被迫啊,那么她就是一个为了正义而战的女英雄?
别扯了,她是刽子手团队的一员,她是暴力和邪恶的化身,一个起初将他的哥哥视为恶人而最终走向她哥哥同样道路的女革命家。
她的家族姓氏在布达佩斯领导了暴乱,她还将暴乱的种子洒向世界!
也许唯一能将她的暴力罪恶视为相对合理的战争应该是为了争取匈牙利独立而对抗奥地利皇帝的战争,肯定不应该是成为奥匈帝国军队中的一员对抗法国英国和俄国!
导演混乱的历史观和民族国家观让这部影片更加糟糕的一塌糊涂!
导演丝毫不肯挖掘细节,深入探讨东欧民族情绪和国家观念的复杂本质,而是投机取巧,移花接木,用他的“花活儿”讲述了一家妓院和拉皮条的人的故事,然后跑到世界舞台上以受害者的姿态甩出各种大词滋哇乱叫,是虚伪,滑头,爱慕虚荣且爱偷懒的左派的一贯做法。
2 ) 日暮
在得獎首作《天堂無門》(2015)以破格觀點呈現納粹集中營的人間地獄後,尼美斯將深焦鏡頭再推前,凝視一戰的世道崩塌。
神秘孤女愛麗絲來到布達佩斯,欲在亡父創立的帽子名店求職竟被拒門外,由此開展一趟追尋兄長惡魔幽靈之旅,重回過去,揭開家族的隱藏真相。
延續前作風格,長鏡緊隨愛麗絲穿梭闇黑時空,聚焦局限觀點、狹窄視角,如夢魘般矇矓影像的壓迫感襲人而來;以家族老店殘留的微光,斜照文明的殞落。
3 ) 一场不知所终的猜谜游戏
众神的黄昏,欧洲究竟是在哪一刻堕落?
这是瓦格纳音乐,尼采哲学,维斯康蒂电影。
如果说《索尔之子》创制了一种美学,一种沉浸式历史微观叙事视角,但谁能想象拉斯洛的第二部就会如此野心勃勃通过一个身世不明的神秘女子在欧洲大陆最深处来经验欧洲日暮时分一整个旧世界崩塌。
我们甚至能更强烈感到这种微观视角本身无序混乱荒诞,一种个体化历史视角的不可能,前作所有缺点几乎都在新片上得以进一步放大,文本自身不稳定仿佛随时都能和电影中世界一起瓦解。
但又没有办法不为之震颤这种回到历史本身巨大冲击。
1913年布达佩斯,黄金时代最后一年,奥匈帝国末世当前。
不再是禁闭高压下的集中营,而是完全敞开的大街小巷、帽饰店等公众场所,导演试图用同样的摄影手法来制造沉浸感难免有炫技的嫌疑。
其次,剧中女主角一意孤行寻找亲生兄弟的设计也跟《索尔之子》里父亲一心想为儿子体面安葬如出一辙。
然而,在这个故事里,女主角的出发点是令人生疑的,由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给出明确的答案,只是依靠模棱两可的人物对白以及人物关系来推动情节及制造悬念,令观众逐渐坠入一场不知所终的猜谜游戏。
由此可见,导演一心想延续的独特美学风格,在这个叙事文本上是难以站得住脚的。
从深层隐喻来看,女主角好比是一种无孔不入的思想或执念,这种植根于昔日辉煌的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心态,在面临权力/荣耀日薄西山之时,难免会像女主角一样深陷焦虑,四处碰壁而无法找到出路方向。
影片高潮部分,女主角进入被侵占的珠宝店,却始终无法见到自己的兄弟,而当她靠近窗户俯视楼下群情汹涌的暴动民众,听到呼喊的不是别的,而是她的姓氏。
到了这一幕,导演似乎才向观众揭示这位神秘女主角的真正含义,她是一种抽空了现实意义的象征符号,连同最后一个镜头也再次明确了这种隐喻。
4 ) 小年夜的“精神按摩”
寻找兄长到成为兄长,是选择对可控牺牲的默认?
还是投身摔进下一次失控的轮回漩涡中?
…对抉择的思索终为一纸空言,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现实之间存有差距,有时它就像一根受潮的火柴,在阴冷的大背景下,失去了光与热的效用。
而有时,它如同一颗渺小星火,微风拂过,即可燎原。
时机差异造就了结局的不同,在没有合理的解释下,人们称其为命运。
5 ) 为啥评论人那么少
该片讲述了黑暗还未侵入文明的一战之前,神秘女子爱瑞丝在被拒绝加入已故父母的店铺后,开始寻求自己失去的过去的故事该片讲述了黑暗还未侵入文明的一战之前,神秘女子爱瑞丝在被拒绝加入已故父母的店铺后,开始寻求自己失去的过去的故事该片讲述了黑暗还未侵入文明的一战之前,神秘女子爱瑞丝在被拒绝加入已故父母的店铺后,开始寻求自己失去的过去的故事 电影《日暮》完美塑造出一个暴风雨前看似风平浪静,但远方躁动的乌云却早已不断逼近的氛围,华丽梦幻却也充满着罪恶与黑暗。
6 ) 日暮
同学一句评论最触动我:“《日暮》这部片具体xxxx讲了啥?
——情节对应什么不重要,重要的不是逻辑,而是这种视角受限的感觉。
”可是我不懂,我想要知道所有的信息啊?
——难道你平常生活中能知道所有的信息吗?
” 一时间我语塞,我突然又一次地发现,我以为自己已经理解了周遭的世界,然而我却连自己的生活也不懂。
我盲目乐观而过于自信,即便现在不懂,也相信只要沿着目前路径之指引必定能抵达最终的胜利。
可是随着世界进一步显露,揭示出的却是无序与混乱的原风景。
我无法掌控自己全部的生活,甚至无法知晓自己的身体,又何况整个社会,哪怕另一个别人!
+电影↑ +镜头:晃动的表达;特写、近景、远景,既有代入感,又有疏离感(第三人称)。
第一人称视角, +历史背景:法国“美好时代”,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奥匈帝国最后的辉煌。
日暮!
- 并非爆米花大片,也不是最激进的拍摄形式,可能我试图用好莱坞逻辑套文艺片,用哲学要求电影(
7 ) “线条”与“节奏”的失能
对于很多观众而言,追求沉浸感体验与感知影像所传递的微观情绪似乎是相悖的。
其实早在《索尔之子》披荆斩棘戛纳之时,观众就对奈迈施的创作形式持以怀疑态度。
时隔三年,奈迈施再次启用《索尔之子》中那套熟悉的视听系统,引发的不满有增无减,同样的嘘声从观众席上传来。
为何?
面对《日暮》以叙事谜团填充的冗赘文本、充满机械感与幽魂感的人物动作、碎片化的主观视角,观众体察到的却是银幕背后强硬的预设与导演操纵的双手,而非代入角色后真实情感的涌现。
——这样的批评并不轻率,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奈迈施前后二作创作体系上的变化,对《日暮》为何遭受贬低的原由进行解惑。
1.线条毋庸置疑的是,《日暮》与《索尔之子》的根本驱动力都来自于奈迈施追求观看体验感的创作程式。
这种创作程式分为两步:一是以视线与画框的局限完成环境建构,并借此形式匹配人物偏执的动机;二是人物的偏执动机带来其运动轨迹的既定,主角之外的人物被断然“抛弃”,只在需要调动时呼之即来。
《日暮》中,我们可以轻易地跟随Irisz的目光,“扫荡”余晖之下的布达佩斯;《索尔之子》中,人物的囚犯身份使之不得已在有限空间中活动,朦胧晦暗的色调将背景环境进一步地压缩。
在此程式基础上,主体人物的“眼睛”或“背影”自然而然地凝聚观众的注意力,我们不禁地关注起主体人物所关注的物体与事件,因为它们都由具有边界的画框给出。
Irisz在帽子店对精美饰品的凝视,在马车上对周遭事物若有所思的观察,在伯爵夫人宅邸透过门帘的偷窥,逐渐将浅焦镜头下虚化的景物抽象为倒映在观众视网膜上的“线条”。
对这种“线条”的感受,是肯定或否定影片创作程式的根本所在。
《索尔之子》将摄影机对准集中营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下的空间,当Saul的处境被交代,观众可以充分理解人物的处境,很快地站在了他的身旁。
我们能够信任人物是在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人物与建构的环境充分融洽。
此时摄影机所勾勒的“线条”,是有机的、生动的。
反观《日暮》,主体人物的处境自开场就被隐藏,导演试图不断生产情节的谜面,作为营造神秘感的来源。
但这却导致了主体人物与构建环境的不可信任:观众无法洞察谜境中的人物状态,巨大的帽子总是遮挡着人物的脸。
《日暮》通过精细的色彩渲染达到的典雅质感实为电影工业化的产物,它的“线条”是空洞的。
摄影之所以与绘画不同,就在于影像的独特性是对原型物体本质客观性的揭示[1]。
电影摄影无法摆脱对原型物体的机械复制,因此,现实的真实性仍然需要毫不避讳地透过影像被观众看到。
当我们凝望着Irisz脸上柔和的光线,便很快发现这种依赖于色调打光的古典主义建构是如此的不切实际。
它太过精致了,就像文艺复兴时期严格遵循透视法则的画作,笔触致密却缺少了灵动。
《索尔之子》的置景纵然亦有精致化的倾向,但它始终让位于行动迅疾的人物,人物的动作才是被强调与被捕捉的,影像所展示的情景相对客观地保留下了真实的动作瞬间。
值得一提的是,Irisz的目光似乎被导演设计为是“失明状”的。
那么,从她的视角出发,如何确认她所看、所感的一切是真实的呢?
《日暮》仿佛被泛滥的视线引导所淹没。
奈迈施是否忘记了《索尔之子》中Saul坚定、深邃、却柔和的双眼?
2.节奏“线条”是对奈迈施作品谱系中被摄内容的抽象,而对于拍摄方式以及摄影机运动带来的视觉流动感,我们可以抽象化为“节奏”。
电影只要一开始播放就无法停止,因此电影拍摄的主体常常被注入动力以完成系列动作,它关乎动作如何开始、如何终止、如何转换。
在奈迈施的作品中,动力似乎就存储在摄影机身上。
摄影机紧紧跟随人物,人物又从运动的摄影机中汲取补给。
影片中时间流逝的过程,也就是摄影机动力不断损耗的过程,《索尔之子》与《日暮》都呈现了这一损耗,区别仅在于主体人物的行为动因不同。
《索尔之子》中,主体人物行动迅疾,动因是逼仄空间对其进行的施压:集中营不见天日的生活迫使Saul在清理尸体时找到了寄托,被视为“Son”的男孩尸体象征着Saul仅存的信念,信念始终支撑着他的偏执,做出一系列费解、毫无意义的事。
《日暮》中,Irisz的行为动因却十分羸弱:一开始是继承家业的愿望,而后是调查兄长与家族的真相,再后又投入到对王室阴谋与革命的探索。
文本设计上,导演的野心昭然若揭,但如此再三转折,视觉动力却陷入消耗殆尽的境地。
Irisz对一战前夕布达佩斯城的观察,不可挽回地沦为一种场景堆砌:太过戏剧化地去设定场景,实际效果更像是镜头刻意地要与戏剧保持一致;表面情节组织充满了紧随剧本的僵硬感,可人物却没有产生相应的姿态。
或许可以将《日暮》的场景堆砌解释为一种依靠人物视角呈出时景剖切面的手法,但它必定需要抛弃掉一些来自情节上的变奏点。
为了配合文本所需的情节转折,主体人物以外的配角都成为了功能化的“工具人”,他们仿佛集体患上了失语症,对Irisz的问题三缄其口。
与此同时,Irisz对外界的认知全盘来自他者口述语言的信息传递,而非自身通过观察感受得到。
这是一种笨拙的剧本设定,也是一种重文本轻视听、退而求其次的设定,使得人物间充斥着的揣测与质疑,无一不透露出浓烈的预设感。
回到“节奏”的问题上,由于文本周折对动力的损耗,观众很快对《日暮》的镜头感到疲乏,无法像《索尔之子》一般,因为对人物投入了充沛的关心,而使意识能够跟随并保持在高速运动中。
二者动力观的差异也印证了纯视觉情境与感知-运动有着本质区别,观众并非盲目地面对视听画面,而是可以从角色身上看到自己[2]。
《日暮》的人物在后半部分逐渐步入失控与迷失中,结尾衔接进入战时状态的长镜头,或是为了点题,或是为了让Irisz逃离家族的迷局,从而转移观众的注意力。
相较之下,同样在结局给人物正面特写的《索尔之子》显然更有力量:疲惫的Saul看见不知从何处来的金发男孩,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这是终止时刻“节奏”上应有的舒缓。
尽管,《索尔之子》的拍摄是奏效的,但总体而言,奈迈施的创作程式并不足以让人怀有乐观态度。
这种依赖于摄影机动力追求体验感的能量十分有限,一旦缺少情感真实的触动(《索尔之子》中尚有面对尸体时人物发出喘息的场景),便很容易进入设计情境的游戏视角。
反对主张“游戏式体验”的影像作品,因为“游戏”的视角让我们失去对真实情境中人物如何作出反应的感知,转而跟随提线木偶般的人物,被既定的情节牵引着,步入远离现实、拥抱虚幻的危险之境。
参考文献:[1] 安德烈·巴赞. 电影是什么?
[M]. 崔君衍,译.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2] 吉尔·德勒兹. 时间-影像[M]. 王文融,译.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
8 ) 电影节产品还是模拟游戏?
借由《索尔之子》名声大噪的导演拉斯洛·奈迈施在第一次执导电影时,就捧回了戛纳评审团大奖的桂冠,又在颁奖季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收入囊中。
可当三年以后,这位被戛纳捧红的新人带着自己趁热打铁,野心蓬勃的新作,试图重回棕榈海滩的时候,法国人却犹豫了。
争议四起,流言纷纷,奈迈施最终和已被媒体谨慎期待的《日暮》亮相威尼斯。
丽都岛的观众们发现,这部降临在1913年布达佩斯的电影,从剧作结构、浅焦摄影、主观视角、沉浸式美学、历史叙事上都几乎和前作的方法论一脉相承:好像将摄影机置身于二战的惨绝人寰已经不够,奈迈施要在时间中继续回溯,直到世道崩塌的一战前夕。
可是这一次,电影差强人意的口碑却证明一切似乎都不再奏效。
《日暮》对准一个身世神秘的少女,她远道异国而来,出现在由亡父创立的帽商店应聘遭拒,却意外得知了家族数十年前的灭门惨案,不由卷入一场由腐朽贪婪的贵族,疯癫的车夫,衣衫褴褛的伯爵夫人,狂热的反叛分子共同画就的“黄昏”卷轴。
这座她阔别已久的城市,如今被过去的阴影和现世的疯癫所纠缠,正在为不久以后的战火纷飞举行“最后的晚餐”。
然而,笔者的质疑恰恰要从这里开始:这乍一听上去为了重现历史而生的黄金设定,真的将我们置身于历史当中了吗?
它怀着多大的好奇心和诉说欲进入这段往事?
除了一个盛大的布景和诗意的噱头,观众还在原尺寸复刻的城市模型中看到了什么?
事实是,我们什么也没有看到。
如果说焦距是导演为观众裁定视点,以便划清什么是“可观看的”,什么是“观看的禁地”的话,奈迈施的浅焦摄影则是导演独裁的极致:除了主角的运动我们什么也看不清,也不被要求去理解,我们像集中营的囚犯,被摄影机拖在地上前行,等着被导演实施火化或枪决——在这里面,导演并不屑于给观众思考的时间,更无从谈起在其中呼吸和沉浸。
奈迈施的狡黠就在于他“制造”了一个主角作为观看的起点,但我们并不完全共享她的视线,多数时候她的运动霸占了画框,似乎这样我们的观看便有了意义,而日暮中的欧洲却模糊在焦距之外,它们是幻影,是奇观,是玩偶公仔,是操纵情绪的昆虫嗡鸣声,却唯独不是事件,不是人物,更不是历史。
为数不多的深焦镜头,却是角色在景框中消失的瞬间,在这些时刻,我们终于被返还了眼睛,看清了身体在其间穿行的空间和情景,在观看权再次被剥夺的倒计时里贪婪地呼吸,同时感到错愕:跟随主角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不是去体验和留下印象,而是正好相反,被她屏蔽观看的权力?
于是我们仅剩的目的便是等待导演向我们滚出下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你有一个哥哥”“被送往奥地利的姑娘们凶多吉少”“他们要来洗劫帽子店”),下一个不知所云的人物,下一个“禁止入内”的地方:这正是奈迈施十四年前执导的短片《耐心》中所做的——我们漫无目的地跟随一个忙活着的女人,接着“咔”的一声被扼住喉咙(或者只是导演这样认为),这是一名集中营里的女秘书。
这便是电影的“作者性”,它被减少到了一个冲击值(shock value),好像我们跟随一个长镜头就是为了挨它这一巴掌...在集中营电影《索尔之子》中导演狡猾地给浅焦长镜提供了堂而皇之的借口:“我们最好不要抬眼观察和驻足凝视,也不要试图理清楚不幸为什么会发生,因为谁有权力说自己猎奇的目光不是在消费这场浩劫呢?
如果对其理性推演就意味着野蛮和伪善的话,我们不如直接将观众丢进泥泞之中。
” 是的,确实如此,可是奈迈施的处理不啻于脱下一件伪善的外衣,又穿上了另一件。
索尔埋葬儿子的执念在集中营无情的秩序中本就稍欠说服力,而在牵涉到越来越多的牺牲者,付上越来越高昂的代价后,这种坚持已然演变为一场近乎不可理喻的行为艺术。
索尔对犹太同胞的无视,对逃出集中营的漠然,对难民的利用,又和缺乏人性的纳粹军官有何区别呢?
这时我们终于恍然,导演为了把长镜头的坚持得淋漓尽致,为了继续“让观众置身于历史中”,不惜破坏他同胞们用心良苦的计划,以便空洞的承诺足以无限延宕下去。
如果无节制的观看是用目光剥削了受难者的话,这样对人物的漠然和冷酷,只是从外表规避了良心的谴责,而背地里用一套电影的诡辩术又一次消费了这场浩劫。
而这样的借口离开集中营便不复存在了,奈迈施空洞的表达欲露出了马脚,《日暮》只剩下一个诡计去除伪装之后单薄的骨架。
这个故事之所以被语焉不详的人充斥,只因为长镜头要继续下去,奈迈施要继续霸占我们的时间。
莱特小姐有充分的理由去观看,但她却只是神秘莫测地降临在一个场所,被含糊其辞的人搭讪,激起偏执至无稽的好奇心,被一架正好为她而来的马车接走。
她被全城知晓秘密的人愚弄,正像观众被导演愚弄,华丽的服装和摄影掩盖不住导演的“偷懒”和影像的无能:他没有让电影的时长“名副其实”,尤莉·贾卡比僵尸般的表演也没有向我们透露她的内心,而是让电影彻底变成一场由虚假的美,和臆想的错乱堆积而成的游戏,镜头看似跟角色亦步亦趋,却和现实始终保有一步之遥。
一旦跟随这个虚拟主角(Non-Player Character)进入叙事之后,观众便失去了“体验”的选择,而沦为“体验”的猎物,任由她把一个又一个关卡丢向我们,之间只有编排,无需调度。
谁会对一款伪装成艺术的奥斯维辛体验游戏说不呢?
从欧洲到美国,评委会们对它夹道欢迎,于是制作公司满怀热忱地推出了第二款,这一次一棒打醒了所有人。
我们确实该思考近年来越发自我标榜的 “历史沉浸感”究竟是什么,它通常和长镜头直接对应。
《日暮》中的微观叙事只是一个人造的舞台,在奈迈施的一声令下一个预设的终点凭空出现,他在其间设置的障碍令终点不断延迟,而人物在封闭的圆环中障碍赛跑时看见的风景,被他叫做“历史”。
与其说它描摹旧欧洲的日暮时分,不如它无意中捕捉到了失魂导演的黄昏:灵感像一轮残阳一样奄奄一息,从他本就贫瘠的弹药库里落下去了。
与之相反的则是贝拉塔尔的电影。
同样是匈牙利人的长镜头,同样讲述一个逐渐衰落逝去的时代(《撒旦探戈》),观众没有被直接暴露在混乱之中,而是先被安置到了一片牛棚,一间黑暗的房间,一个雨夜,一条垃圾和落叶横飞的街道上——“混乱”在真实的时空中逐渐打开了自己,因为历史作为坚实的客体已经先设地、不容置疑地身在其中,而人物只需要用他们的动作去经历它。
和奈迈施相反,塔尔给我们时间,他的长镜头中每秒钟都是真实的,为人所体验的,是人的身体同社会机器碰撞的过程。
正是这样个体化的时间,而不是长镜头本身,具有“沉浸感”的魔法。
而奈迈施的电影里充斥着时间的折叠,人物从帽商店走到街道上的路程经过了排演和计算,成了一场抽象的走秀,历史也只是外部的装置艺术。
观众在时间的错乱中感到眩晕,因为这里面没有情感,只有量子化的信息洪流。
《日暮》只能是为不愿动脑的观众们准备的,踩上它,便像《天方夜谭》的飞毯,不再需要质疑和思考。
这样善于瞒天过海的诡计走向了什么呢?
电影的结束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满目疮痍,滂沱大雨,一镜到底的摄影机穿过一战的战壕,最终来到了主角的面前。
她眼神空洞,面容僵硬,微微的喘息试图说服观众她处在前所未有,实则纯属虚构的危险之中。
是的,无需劳烦介绍,正是《1917》。
9 ) 一个国家的日暮
《日暮》 我发现每年冬天都会上映一部优秀的剧情片,去年是《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今年是《日暮》。
不得不承认,它很沉闷、冗长,台词前言不搭后语,以至于我的好友在我旁边昏睡过去无数次。
但是它也有很多优点,比如摆脱了上帝视角,通过一个匈牙利女人的视角来看待一战前夕的奥匈帝国,还有独特的摄影技巧等等。
虽然它不“有趣”,虽然它很“沉闷”,虽然它有着观众理解不了的台词,但是这并不影响它成为一部很好的剧情片。
因为有些优秀的电影不是为了娱乐观众而产生的。
10 ) 谁说《索尔之子》导演的新片砸了?
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已然进行到后半程,终于如愿以偿得见了匈牙利导演拉斯洛·奈迈施的新作《日暮》。
这部从戛纳前夕就被很多人传言“失手”的作品,真的如坊间所言拍砸了吗?
我看并不尽然。
电影《日暮》剧组亮相威尼斯电影节顶着贝拉·塔尔弟子的光环,拉斯洛·奈迈施导演注定备受瞩目,其诞生于三年前的长片处女作《索尔之子》也绝对没有让任何人失望。
处女作《索尔之子》曾横扫颁奖季全片手持浅焦跟拍镜头,阴沉昏暗的色调,提炼普里莫·莱维笔下复杂的道德观,让笔者当时在影院第一排观看的时候差点冲出去大吐特吐,也让拉斯洛·奈迈施从戛纳一直拿奖拿到奥斯卡,可谓一时风光无量。
拉斯洛·奈迈施导演今年上半年,当所有人都期待拉斯洛·奈迈施的新作在戛纳的表现时,却意外传出了因质量问题被拒,随后转战威尼斯。
事后,奈迈施和戛纳双方都没有正面回应,打了太极便“哈哈”过去了(见下文采访部分)。
但也因为这个原因,引起更多人的好奇,真的有差到要被拒绝么?
也许只是导演出于其他考虑所做的调整。
无论背后纠葛如何,拉斯洛·奈迈施的这部新作《日暮》已经足以说明逐渐形成的大师气象,即便贝拉·塔尔退休,匈牙利电影也还是后继有人。
这一次,奈迈施的目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毕竟祖国奥匈帝国曾经是一战的主角。
对于导演而言,探讨起战争、集体和个人命运也更加得心应手。
从《索尔之子》开始,奈迈斯就显示出掌控宏大主题的能力,从历史镜头前走出来的人物,用生命来讲述时代;而这一次的《日暮》依然没有让我失望。
影片《日暮》始于这样一个故事。
20岁的艾瑞斯阔别家乡多年后,因为父母双亡,第一次回到布达佩斯,等待她回来的只有父母留下的女帽设计作坊,和哥哥刺杀了伯爵后逃逸的谣传。
然而,八月炮火前的一战硝烟即将一触即发,艾瑞斯在寻找哥哥的过程中,面对宏伟帝国摇摇欲坠的坍塌,眼前只有迷失和不安。
和《索尔之子》相似的是,《日暮》的叙事连贯性同样是不重要的。
镜头一直跟随着艾瑞斯深邃的视角,小心翼翼的重遇这个“阔别已久”的城市。
被肢解的伯爵,穿着丧服的夫人,神经质的车夫,光脚的王子,无政府主义者的聚会,堕落的贵族…..全片几乎没有完整连贯的台词让人摸清叙事线索,所有对话都是在低沉的耳语中进行,好像每个说话者都掌握着一个秘密。
在短短几天内,奈迈施以其标志性的长镜头,像在梦游中穿过城市。
褪色的布达佩斯街景,用人物视角的机位打造出一种焦虑不安的主观拟像,充斥折大量的面部镜头特写,而跟拍镜头一直固定在人物头部位置,以水平视角悄然代入艾瑞斯的内心。
影片中,艾瑞斯就像一个时代的游魂,徘徊在日暮下布达佩斯的迷雾中。
这种身临其境的紧张感和虚幻感,似乎让人抓住了已逝时光折射回来的一瞥消亡,看似真实存在却又如此触不可及。
三十五毫米摄影机让影片中的每一帧画面,都充满着油画质地般的美感。
奈迈施将布达佩斯战争前夜的恐怖,隐藏在这些无限美丽的画面背后。
想必,导演的目的在于营造一种不安的氛围。
颓废的贵族阶层沉溺于阴谋,城市平民充斥着不满和暴力;而这些笼中困兽式的冲突,在世界大战面前都显得那么可笑。
影片所植入的宏观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印证着拉斯洛·奈迈施的无奈。
到底是什么将我们带到这场时代的硝烟中,直至一切化为灰烬。
影片结尾处,战争的硝烟在模糊中弥漫开来。
所有对战争的恐惧,对旧秩序坍塌的预言,都透过日暮中的烟雾和镜面,折射到布达佩斯那家优雅的帽子商店里。
拉 斯 洛 · 奈 迈 施 导 演 专 访来源于Screen InternationalQ:在《索尔之子》获得戛纳评委会大奖之后,创作《日暮》有什么样的新挑战吗?
A:对于我来说,下一部作品永远都会是挑战。
拍完《索尔之子》之后,认识的制作人都催我赶紧开始下一部作品拍摄,千万别拖,趁着热度。
因为第一部电影在全球都挺成功的,所以相对来说,也是有特别大的一个压力。
而且我自己真的一直都很想拍一部关于20世纪初的电影。
这个执念一直在引领我继续创作,所以在制作过程中,因为过于投入反而忘了压力。
Q:《索尔之子》的成功和匈牙利电影基金会的努力,让我们看到匈牙利电影似乎正在经历一次小小的复兴。
你如何看待这个事情?
对安迪·瓦伊纳(基金掌门人)看法如何?
A:我总是把他比作工作室的头儿,20世纪50年代盛行这样具有强执行力的人物,比如像路易斯·梅耶。
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吧,但现在基金会的引导下,至少还是有创作自由和拍摄动力。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工作室和工作室负责人制。
《索尔之子》Q:“帽子”这个元素在《日暮》中非常突出,主角是一位女帽设计师。
为什么设置这个重要元素?
A: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帽子,无论富穷。
这些非常个人化的私人物品有时候会传递出精细微妙的生活信息,包括它们主人的品味、地位、财富、文化等等。
这个由代码和符号组成的分层世界,非常有趣。
Q:《日暮》在威尼斯首映,《索尔之子》是在戛纳。
哪个电影节对你影响更大?
A:几十年来,很多电影人都会从一个电影节转到另一个电影节,没有谁会觉得有多大问题。
能来到威尼斯其实挺高兴的,我曾经在这里拍了第一部短片。
事实证明,这部电影在威尼斯上映是特别合适的;威尼斯这个地方,可以在人们心中唤起世纪之交的年代感。
Q:《日暮》这部电影是不是受了约瑟夫·罗特的小说,或者F·W·茂瑙的影响?
A:约瑟夫·罗特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确实对我影响特别大。
卡夫卡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影响,还有就是阿图尔·施尼茨勒。
这是一个非常梦幻的时期,文学和电影,旧风格的打破,新世界的形成。
茂瑙的《日出》就像一个时代的重音。
我很喜欢这部电影,对我影响也特别大,即使到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还是很有时代意义,充满创意。
茂瑙《日出》Q:《索尔之子》对于年轻观众来说,提供了一个了解二战和集中营的侧面,《日暮》会不会有类似的效果?
A: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布达佩斯,现在看来似乎是另一个世界。
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这些都非常遥远的,但同时它又存在于每个人的记忆中。
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让观众沉浸在一个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的世界里。
在《日暮》这部电影中,一直存在一个“在特定的社会中,如何选择自身命运“的疑问。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社会,在不知不觉中也处在某种文明的十字路口。
Q:《浩劫》的导演克洛德·朗兹曼最近去世了,《索尔之子》拍完之后你跟他联系过吗?
A:有,我和他经常联系。
他的生命这么长,一定有很多特别的经历。
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不仅是电影,而且同是电影人,我们有一种更本质的方式相互理解。
我甚至有一种感觉,应该继承他开创的传统。
对我来说,他能看我的电影、并欣赏我的电影,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
电影《浩劫》导演克洛德·朗兹曼已于今年7月5日去世Q: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拍摄计划?
A:还不确定,但下一个项目是一部英语电影。
作者| 小飞侠;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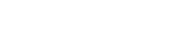













































大年夜at朵云轩4厅,和4年前在协信看《索尔之子》一样,近乎包场,近乎包裹的视听体验,没有什么比这种close-up的焦距和声场,更能激活在“历史现场”中的具身认知,仪式与暴力,呼喊与细语,屠杀中仍能听到丝丝缕缕的小提琴,晦暗的室内仍能见到幽魂般的脸庞,身为女人,被抛入男人的手中,如被抛入本能的狂涛中,连喘息都是侵犯,感受这种无助,感受这“藏在美丽背后的恐怖”,然后才是“莱特之子”的故事,是帝国迟暮的暗流涌动:一份昨日的记忆在游荡,寻找着未来的鲜血,用不断绵延的、焦点调度的当下。在一场大火吞噬的黑暗里(同一场大火也曾吞噬身世),昨日世界崩塌于余晖的庆典,一个名字成为一声呼唤,过去成为了将来,她成为了他。
「世間的恐怖,都隱藏在絕美事物的背後。」導演的前作《索爾之子》是集中營一日遊,這部有多可怕看完有多難受不必多說。 《日暮》好一點,至少全片大概三分之二是以這個視角穿梭布達佩斯,看到的是美人美景賞心悅目,只是這次更像玩解謎遊戲,裡面出現一堆角色說話語焉不詳,女主角就是永遠不會死被綁定好的主角,亂衝亂撞亂問話都不會有事,玩RPG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其實佈景、服裝、鏡頭和聲音設計還是非常厲害,但導演可能已放棄和一般觀眾對話。
☆:3-试图用摄影机把观众困在一个“不谙世事”的视角,然而看起来作者本人对于所谓的“历史”也没有足够坚定的认知,与其说是见证历史或文明的日暮,不如说是见证(只针对这个作品而言)创作想象力的衰竭。
由于中心主角的缺失(无论是角色行为还是演技),社会环境的构建只能是松散与模糊的,过多的涉指可能性也消解了情绪的漫延。不过片子倒挺适合做摄影教程的,室内暗光怎么拍、室内散光怎么拍、夜景街道怎么拍、白日风沙怎么拍、日暮河流怎么拍...
在《索尔之子》的基础上进一步抛却身份与情节,完全将镜头语言凌驾于故事之上,油画级校色、层次丰富的环境音,把1931年的布达佩斯还原为最大的秀场,借女主视角在历史中神游,美则美矣,实则空洞无物。打着家族恩怨的幌子,所有人物与剧情走向都在无脑般刻意服务着这次神游太虚,仿佛瞥到了日暮西垂的帝国衰王,可走马观花得来之物又有几分真情呢?一切都美得如此虚无。战壕中的回眸,又似狗尾续貂般一定要给帝国一个所终。
一个目的明确的匈牙利女子在幽幽的《日暮》中寻找着欧洲人共同的身份,然而紧贴历史的摄影机实际上是在拒绝观众再次进入他们的历史。任何以历史主义之名的考据考证于此都是荒唐而又无效的过度解读,戴着唯物史“冠” 的奈迈施最终将民族历史拍成了一个美得令人窒息的迷。我们随着漩涡一样的剧情越陷越深,直至跟着女主角一同来到记忆的尽头抑或初始:她用自身的道统、美学和眼界设计了一顶包罗万象宛如时光机的帽子,带领我们穿越了一个又一个精致、华丽、昏黄色的梦。
我在影院看了这么久的电影,这是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如坐针毡的两小时是什么心情😒
奥匈帝国日暮之时,奢华精品帽店背后的龌龊光脚之宴;二世祖失踪大哥漂浮多瑙河上,焚烧的家族之名变成了革命口号,只允许男性进入的阴谋密室必导向无差别暴力屠戮;直到庞大腐朽的体制彻底崩坏,全程瞎溜达的历史看客才在一场必败的战争中当上了小医护兵……就像《鲸鱼马戏团》的通俗化翻拍,当然比贝拉塔尔的功力要差几个段位;结尾过于直白刻意的问题也跟导演前作《索尔之子》类似
奥匈帝国在影片里的形象始终都是失焦的。好像只有结尾一战的战壕里,能清晰的看清周围的一张张脸。这个表达是打动到我的点。虽然很难评价这种,用技巧而不是用情节来进行叙述,是不是好的方式。适合对情节体验要求不高的观众。
拉斯洛·奈迈施的调度+运镜大师班,但是故事和力度不及《索尔之子》
艺术性很好,故事性很一般;女主真的像屈臣氏…
视听非常满意,黄昏的光线没的挑的,但是人物和故事还是看的很迷惑,女主角为什么总是执着又目的不明的到处转悠(为啥哪儿都让她进,甚至穿越枪林弹雨也不在话下?)服化道方面其实我没看够帽子(想看到女主做帽子的才华和热情结果并没有)对哥哥的情感对帮助其他女性的态度也过于模棱两可,虽然作为游魂和历史游客的象征寓意也能接受,但这样的人物也太工具化了,有种看《我的二十世纪》的同款上当受骗感
《日暮》(不是日暮里)《索尔之子》导演新作。赶在春节前两天2.9号上映,偏要迎难而上。跟一贯的风格一样,长镜头。这一部一直跟着女主角贴脸拍,沉闷。剧情起伏几乎没有,基本靠配乐才有起伏。
二刷。8-->8.5两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新世界也开始日落红尘了~
觉得画面很美,观影于宜宾。
看完只有??对于我这样的普通观众,觉得实在有些莫名其妙,并且觉得不单是我进入不了导演想讲的历史或是什么,电影主角本身也完全游离,毫无同情心的主观视角,空洞的旁观。(前排的人睡得鼾声大起,后排结伴的两个人在出字幕时同时发出了“嗯?讲了个什么?”的疑惑)
胶片放映的画质让电影很精美,但恕我直言,内容真的太晦涩了
虽然看不懂背后的历史隐喻,不过道具服化还有第三人称视角的沉浸式拍摄方式还是很不错的,(感觉这个 沉浸式手法可以廉价实现?
2.5
如果我不是那么讨厌没有人物主观色彩的局限pov的话可能会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