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野派》剧情介绍
《粗野派》长篇影评
1 ) 粗犷派建筑师,建造废墟
行驶中公路、铁路,除此以外还有信件:建筑与书信、念白与建造、个体与历史。
交叉剪辑,带出粗犷的宏伟叙事,背后的内容。
观感很“古典”的摄影、光造,如果说主角的仰拍很好融入、广角镜头的特写很美——那隐藏的还有冲突的手持摄影,车内的辩驳抖动的拍摄。
电筒的演示中断,比照片更美的实物是什么?
日光射落,大理石上的光影,胶片的显影,凝聚简明的话但说不出的份量。
开给亲人五百元支票的新资本家,算计一分钱擦鞋匠建筑师的报酬……而后半段,集中营逢生的犹太(犹太教)建筑师,怎为宾州新贵美国人的教堂社区满注心血?
恢弘的这段音乐开始就是一层诡计……前半段的经典梦核叙事,其实很工整了,后半段的拆解力所不逮但全然不顾地推进。
尽管女主角、台词、结尾、语言,有些地方差强人意,但将表达融入一栋久未完成建筑的方寸表里——这个故事,几段结构,拍摄程度,依然是荡气回肠。
四星半
2 ) 倒置的自由女神像,令人崩溃的《粗野派》
微信公众号 | 添糖陌影(欢迎关注 )前几日科贝特在电台节目中透露自己“濒临破产”,引发了不少人对于作者导演处境的关注,而《粗野派》以不到1000万美元的成本博得近4000万美元的票房,同时收获如此口碑和赞誉,想来也应当会为科贝特的导演生涯带来更promising的未来。
看过电影后,不得不说,科贝特以不到1000万美元实现了《粗野派》在制作规格上如此高的完成度,的确值得赞叹。
作为一部相当严肃的传记电影,尽管故事本身是虚构的,《粗野派》对于犹太移民题材的呈现有其视角,可能不同于部分人粗鲁判断的“为犹太人唱赞歌”这一立场,电影更多聚焦在移民到美国之后的犹太家庭所面临的处境——一方面是被资本强奸后的“美国梦”破碎,另一方面则是缺失母国影响下的归属感灭丧。
当然,这本身对我而言并没有太多的吸引力,《粗野派》的故事与其讨论的议题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未免颇有些距离,而导演科贝特在叙事上也采取了一种相对复古且克制的风格,令我难以真正被电影吸引。
不过,《粗野派》在技术层面是无可挑剔的,画面细节的考究,场面调度的精巧,均充分提示着观影者导演始终保持在场。
电影序幕,一段极具风格化的跟拍长镜头带我们跟随着男主角拉斯洛穿越骚乱不安的集中营,耳畔是妻子的来信,交待故事背景与人物的同时,点出电影牵涉的核心议题(歌德说,“没有人比那些自以为自由的人更无药可救”)。
可逃亡中的拉斯洛似乎无暇倾听妻子的声音,我们在他的脸上看见的是匆忙、惶恐、破碎。
我们跟随着他掀开舱门,伴随着一段昂扬的音乐响起,刺眼的光线令人眩晕,随即看见,倒置的自由女神像。
这段镜头的设计感与完成度堪称大师手笔,而倒置的自由女神像这一意象更是极为巧妙贴切的表达符号,为整部电影奠定了基调。
在临近结尾处,当女主角痛斥盖·皮尔斯饰演的资本家之后,众人去寻找不见踪迹的老板,镜头跟着人们在一个个幽暗的甬道中搜寻,最终推进聚焦在拉斯洛为其设计并建造的教堂中央的十字架光斑之上,镜头上摇,仰望穹顶,随即电影进入尾声。
我不想也无需对这一组镜头再作解读,相信看过它后,大家应该都能感受到其表现力与隐喻性。
最后尾声,几乎一直在沉默的侄女佐菲亚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讲,为拉斯洛的人生态度和艺术成就予以作结。
多年后的佐菲亚改由此前饰演男主妻子的菲丽希缇·琼斯扮演,此前饰演佐菲亚的拉菲·卡西迪则改为扮演佐菲亚年轻的女儿。
镜头在年迈的拉斯洛、演讲中的佐菲亚、年轻的佐菲亚女儿,以及拉斯洛的教堂杰作间切换,我们见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人生,更是一群人的命运;我们听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态度,更是某种民族性的、代际间的传承。
“目的地才是关键,而不是旅程。
”对于我而言,《粗野派》最大的观影障碍依然是其接近三个半小时的时长。
即使会被导演技法所吸引,我的耐心依然在冗繁的故事中被消磨殆尽。
这部电影再次证明了一条真理——cinema是属于cinema的艺术——在个人空间内寻求沉浸极度困难,煎熬的体验也终让观影变作了加班。
“未能沉浸”,既是《粗野派》的遗憾,也是我的遗憾。
3 ) 粗野派观后感
漫无目的的流水账,每个镜头都在疯狂暗示导演的野心:闪开,我要装X。
可惜没那个实力。
所以能把这个导演选为奥斯卡最佳导演的,说明美利坚在装X这块还是一块很有市场的沃土。
学术界发论文都需要投稿-审稿-修改的漫长流程,就是为了避免一些人把自我高潮的垃圾喂给读者们看。
电影界就不一样了,你只要有自信你就可以拍,拍完就可以把垃圾扔给观众们看,然后有些及其自恋的导演,可以把垃圾拍三个小时,他浪费观众的时间看这些痛苦的玩意,毫不内疚,好没有公德心的。
4 ) 乙巳年四月初四 劳动节
太长了,210分钟的时长陆陆续续看了四五天,整部电影就是一个类似“似水年华”的拱形对照结构,不断地互文与对应,几乎用一个虚构的人物史诗再一次的反美国梦的叙事(太多这类的叙事了,不同的则是艺术家牺牲了一切终究完成了自我的艺术成果),这种缓慢、破碎的复古质感,开头就是一个倒着的自由女神像,如果仅仅是电影本身的美学是非常值得欣赏的。
但后续补充了建筑方面的内容后,又是一种粗暴的文化符号的堆砌与滥用。
内与外的巨大割裂,作为建筑学家完全为自己的想法设计建筑合理与否?
对于粗野主义的理解偏颇与混用,人物本身作为虚构放到真实历史的不合理设定(不仅仅是作为包豪斯学生却找不到工作?
)拙劣地化用安藤忠雄的光之教堂(安藤忠雄本身就是粗野主义的反面),与电影本身的野心与美学奇观完全不匹配地是对于作为核心的建筑本身的粗暴处理(片中的建筑物我是一点没看出来美在哪里,粗野主义又在哪里),粗野派如果指反派资本家,那本身内涵的左翼理念毫不提及,仅仅是导演阐释为犹太大屠杀的惨痛历史的纪念,导演和影片本身也是刻薄的“粗野派”啊。
5 ) 粗野派的背后:艺术家、资本与破碎的美国梦
在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中,一部片长215分钟、采用70毫米胶片放映的电影《野兽派》挑起了人们的巨大好奇心,这对身经百战的记者和影评人们来说并不常见。
这部由布拉迪·科贝特执导的伪传记片,讲述了一位匈牙利裔犹太建筑师拉斯洛·托特从二战后的集中营逃离后,远渡重洋来到美国,试图在这片充满机遇的土地上扎根的生命旅程。
然而,他所期待的“美国梦”不过是一场幻灭。
战争创伤、移民困境与艺术家命运的微妙交织,再现对资本主义压迫的思辨。
影片第一部分“The Enigma of Arrival(抵达之谜), 1947-52”讲述拉斯洛在美国讨生活的种种艰难境遇,他为富商哈里森设计的家庭图书馆意外获得了赏识后,情况逐渐好转;第二部分“The Hardcore of Beauty(美之核心), 1955-60”则主要围绕拉斯洛为哈里森建造一座社区教堂的过程,以及他的妻子埃尔塞贝特和他重逢后的家庭生活。
叙事基调由前半部分充满美式乐观主义的“奋斗即成功”,逐渐转向战后心理的创伤难愈以及移民生活的苦涩,气氛更加悲观阴郁。
两部分之间,导演留出了15分钟的中场休息,他还特意选取拉斯洛的全家福作为画面背景,并设置了时钟提醒观众剩余的时间。
除此之外,《粗野派》还是自马龙·白兰度1961年的《独眼龙》以来,第一部完全采用VistaVision拍摄的电影。
这种宽银幕电影格式由派拉蒙影业于上世纪50年代开发以对抗当时兴起的电视业。
它以其极高的画面分辨率和细腻的光影表现著称,曾在《迷魂记》《西北偏北》和《十诫》等经典影片中被广泛使用。
VistaVision的镜头转制为70毫米格式后,不仅带来震撼的视觉冲击力,更凭借其鲜明的复古特性,与影片设定的背景20世纪50年代形成深刻的呼应。
这一时期,粗野派建筑崭露头角,成为现代主义建筑的独特分支;与此同时,逃离战争与迫害的犹太移民大量涌入美国,寻求新生活的希望与融入社会的困难相伴而生。
那也是一个美国试图通过经济繁荣与技术优势确立全球文化权威的年代,繁荣的表象之下,深层的不平等与政治紧张早已暗潮汹涌,恢弘且细腻的视觉表现成功将这种社会氛围融入叙事背景。
在威尼斯世界首映时,制片方将26卷总重约300磅的70毫米胶片空运至水城。
据导演形容,在片场拍摄时,摄影机“就像一台缝纫机一样”嗡嗡声不断,演员们也对这一设备感到好奇。
不过,它可谓恰到好处地展现了片中粗野派建筑在光影下的独特魅力。
例如,拉斯洛为哈里森设计的图书馆仅有一个穹顶天窗,随着一天中光照角度和强度的变化,射入室内的光线展现出极为细腻的光影层次,令图书馆时而庄严、时而静谧;而开场一路跟拍拉斯洛从幽暗的火车车厢走出的手持镜头,则令观众仿佛置身于潮湿阴暗的车厢中,拥挤与窒息扑面而来;当拉斯洛迈出车厢时,突然涌入的开阔视野和通透光线带来强烈的解放感,确实是普通的高清摄影机难以实现的效果。
拉斯洛逃离了法西斯主义的魔爪,却在美国遭遇了社会边缘化与阶级滑落,这几乎是一种宿命。
“美国梦”的背后,是身份被时刻拿捏、成为被资本家吸血的傀儡。
富商哈里森的出现表面上为他带来了转机:不仅提供薪水,还通过政治关系帮助拉斯洛的妻子和侄女与他团聚,然而,这份援助并非无条件的慷慨,而是资本家“施舍”背后的隐性掌控。
拉斯洛虽然领命建造社区教堂,但完全被哈里森层出不穷的奇想所压制,这座粗野派建筑更像是哈里森膨胀自我的外化。
而教堂越接近完工,拉斯洛对哈里森的价值就越微不足道,就又摇动了他在美国扎根的前景;凡此种种,让他本身暴躁的脾气、对屠杀的恐惧、酗酒与吸毒的恶习变本加厉;工作中对完美主义的严苛贯彻,又令他的妻子和周围的工作伙伴痛苦不堪,项目也严重超支,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令拉斯洛陷入精神死角。
或许当他刚踏上美国时,看到的倒置的自由女神像就暗示了一切——拉斯洛逃离了家乡的集中营,却在异乡用自己的双手,用大理石为自己建造了新的“精神监狱”。
《粗野派》对移民问题的讨论,跳脱了种族歧视或社会接纳程度的常见语境,而是以资本主义剥削为落脚点。
尽管本片以拉斯洛作为第一视角,但盖·皮尔斯饰演的哈里森才是推动叙事不断前进的动力。
他多金、直率、品味高雅,能够欣赏拉斯洛的天赋,但最终显露出狂妄与刚愎自用的性格本色,不仅通过雇佣关系在经济上对拉斯洛施加压迫,还通过心理操控与性侵,把拉斯洛当作自己的玩物,击溃了他的心理防线。
哈里森的个人成功发迹和对移民的盛气凌人,简直就是“美国梦”的一体两面。
科贝特通过拉斯洛的双重囚禁——从法西斯主义到资本主义——展现了“移民”和“艺术家”二重身份被现实挤压的生存困境。
从暴力当中看似解脱的灵魂,又被崭新的现实蹂躏和击碎,正是他电影中一贯的母题。
但剧本却浅尝辄止,只能用最浅显的方式交代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
编导用伪传记片的形式钻了空子,将无数个拉斯洛捏合成阿德里安·布劳迪那张瘦削忧郁的脸庞,也将移民困境的根源过度简化为哈里森单一资本家的压迫。
但这并非是个体化的悲剧,而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进程中的结构性矛盾。
这种模糊性虽然增强了叙事的普适性,但也削弱了其批判资本主义剥削的深度,令影片在叙事和影像上的野心显得大而空。
再来看影片的标题The Brutalist。
它不仅可以指建筑师,也可以指粗野主义这一建筑流派,它还是对战后移民在美梦前跌落、艺术家与资本力量博弈的粗粝现实的指涉。
建筑与权力之间始终存在复杂且富有启发性的关系,粗野派建筑本身追求结构与功能的直接表达,摆脱过度装饰,而拉斯洛在美国的经历却反映了这种“赤裸”与“被挤压”的状态。
他试图在他乡建造属于自己的根基,但终究只能粉饰别人的梦。
阿德里安·布劳迪是演绎拉斯洛的不二人选,除了层次丰富的表演,他的母亲正是一位当年从匈牙利移民到纽约的摄影师,特殊的家庭背景也让这份演出更加沉重。
而做建筑和拍电影又有多少本质区别呢?
两者同样需要多方协作,艺术家必须知道该如何与资本力量共存,这种关系中往往暗藏不平等的剥削。
正如拉斯洛的建筑被投资人修改和限制,电影创作也面临着来自资金、市场和体制的种种制约。
在威尼斯的记者会上,科贝特谈到:“好莱坞有太多不能拍的故事了。
”他的上一部与娜塔莉·波特曼合作的、探讨美国流行歌手产业和恐怖主义的《光之声》毁誉参半,艺术野心在与美国文化体系的务实与市场化逻辑碰撞后,最终受挫。
作为典型的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知识分子,科贝特这种情绪和自我投射也若有若无地贯穿于《粗野派》的叙事中。
科贝特和自己的妻子花费了六七年的时间撰写《粗野派》的剧本、筹集资金,期间又遭遇俄乌战争、疫情、罢工等挑战,影片的拍摄和后制一直辗转腾挪于欧洲各地。
难以想象的是,本片的成本才不过一千万美元,可谓真真正正把每一分钱花在刀刃上,但代价就是“自己长达六七年没有什么收入”。
作为独立电影人,他同样得在创作自由与生存压力之间权衡。
影片控诉了资本对移民群体的压迫和艺术家的求而不得,仿佛也在隐晦表达电影制作的辛酸。
最终,威尼斯影展给予他最佳导演银狮奖,也可以算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6 ) 知识分子移民的困境,野心过载也值得一看
听朋友推荐,下午去看威尼斯最佳导演影片,总长3h35min,有10min幕间休息。
最初期待值随人物发展和剧情推进而飙升,休息时和影院小哥点了份披萨闲聊,连说非常喜爱很有共鸣。
后续却令我遗憾,收尾力有不逮,果然是野心过载。
晚上回过头来,觉得还是很值得观看和讨论的影片。
第一部份移民建筑师的心绪写实而精彩,在新土地适应新规则建立新身份,与机会过招时命运大起大伏。
外语表述多少会有些降智,过往的社会积累也几乎清零,日常的思辨被赤裸裸的生存焦虑所取代。
有时候得依赖本能存活,而过于严酷的环境会让人陷入唾手可得的瘾。
第二部份出资人与艺术家的狗血剧情,我觉得压过细腻的人物发展。
粗野主义建筑沦为动作片背景板,略有失望。
导演想呈现美国梦的反面,拯救者有时也是毁灭者,骄傲的知识分子到底是本地资本家的玩物,所谓睿智的发言是晚餐桌子上的调味品,而屈辱会麻木灵魂或者化为愤怒,离间自己的爱人。
而我感到导演意图过于显露,很有些禁毒科教片的意味。
第三部份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场景重述历史,试图庄重地把现实与过去联系在一起。
曾经失语的侄女讲述轮椅上建筑师叔叔的经历,把复杂的过往整理成一种英雄叙事,压缩了其他阐释空间。
正如导演把粗野主义建筑归纳为战后难民的心理创伤与不朽的纪念碑,这种策展总结语般的收尾,弱化了前两部份多义的冲击力。
我读了电影的媒体包,了解到影片在布达佩斯小成本拍摄,还固执地选用了昂贵的大理石,精妙地使用了70mm胶片。
我喜欢影片中各类交通工具(无尽延展的公路是新移民不知未来如何的茫然,树林间穿梭的自行车承载轻快的希望,火车站人群里的瞭望加重了久别重逢的忐忑),也喜欢从容又不拖沓的镜头剪辑,还有潜入各种情绪的精准配乐。
意大利克拉拉采石场的纹理,妻子这个角色的骄傲坚韧与信赖,以及布洛迪呈现的破碎感,都给我非常多的回味。
特别惊喜发现,虽然主角是虚构的,但是原型曾在英国小住。
他是匈牙利裔现代建筑师布劳耶,设计过瓦西里椅子(以好友瓦西里·康定斯基的名字命名)。
在前往美国设计惠特曼美术馆之前,曾与包豪斯创始人格罗皮乌斯都住在伦敦Hampstead的Isokon Building,这里也曾住过其他建筑师以及阿加莎等人,准备未来去这座公寓探险!
观影于Curzon Camden25.9.16
7 ) 原文轉載:《粗野派》的空洞的野心
The Empty Ambition of “The Brutalist”Brady Corbet’s epic takes on weighty themes, but fails to infuse its characters with the stuff of life.By Richard Brody, January 3, 2025,The New Yorker websiteMost filmmakers, like most people, have interesting things to say about what they’ve experienced and observed. But the definition of an epic is a subject that the author doesn’t know firsthand: it’s, in effect, a fantasy about reality, an inflation of the material world into the stuff of myth. As a result, it’s a severe test of an artist, demanding a rich foreground of imagination as well as a deep background of history and ideas. Brady Corbet’s “The Brutalist” is such a film—one that proclaims its ambition by the events and themes that it takes on, boldly and thunderously, from the start. It begins in 1947, with the efforts of three members of a Hungarian Jewish family, who’ve survived the Holocaust, to reunite in America and restart their lives. Corbet displays a sharp sense of the framework required for a monumental narrative: “The Brutalist,” which runs three hours and thirty-five minutes, is itself an imposing structure that fills the entire span allotted to it. Yet even with its exceptional length and its ample time frame (reaching from 1947 to 1960 and leaping ahead to 1980), it seems not unfinished but incomplete. With its clean lines and precise assembly, it’s nearly devoid of fundamental practicalities, and, so, remains an idea for a movie about ideas, an outline for a drama that’s still in search of its characters.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film’s unusual conceits, I’ll be less chary than usual of spoilers.)The movie’s protagonist, László Tóth (Adrien Brody), a survivor of Buchenwald, first arr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Upon reaching a cousin, Attila (Alessandro Nivola), who had immigrated to Philadelphia years earlier, László learns that his wife, Erzsébet (Felicity Jones), is also alive, and is the de-facto guardian of his orphaned adolescent niece Zsófia (Raffey Cassidy). But the women, who endured Dachau, are stuck in a displaced-persons camp in Hungary, under Soviet dominion, and the bureaucratic obstacles to a family reunion are formidable. Before the war, László was a renowned architect; Attila, who has a small interior-design and furniture firm, puts him up and hires him. A commission from the son of a wealthy businessman to transform a musty study into a stately library gives László—who’d studied in the Bauhaus—a chance to display his modernist virtuosity. The businessman himself, Harrison Lee Van Buren (Guy Pearce), soon adopts László as something of an intellectual pet, housing him at the estate and commissioning from him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a massive project—combination library, theatre, meeting hall, and chapel—that László calls his “second chance.” Meanwhile, Harrison’s lawyer, Michael Hoffman (Peter Polycarpou), who is Jewish, lends a hand with the efforts to get Erzsébet and Zsófia into the country.That bare description covers only the first half of the film, which is divided by a fifteen-minute, built-in intermission. What’s clear from the start is that “The Brutalist” is made solely of the cinematic equivalent of luxury components—elements of high historical value and social import—starting with the Holocaust, American xenophobia, and the trials of creative genius. Corbet and Mona Fastvold, his partner and co-writer, quickly add some other materials of similar weight. The movie features drug addiction (László is dependent on heroin to treat the pain of an injury that he suffered when escaping from captivity), physical disability (Erzsébet uses a wheelchair because of famine-induced osteoporosis), and postwar trauma (Zsófia has been rendered mute by her sufferings). The arrogance of wealth is personified by Harrison, who lures and abandons László capriciously and cruelly—and worse, commits an act of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László that wraps up in one attack the rich man’s antisemitism, moralism about drugs, resentment of the artist’s independence, and desire to assert power with impunity. Harrison’s assault, accompanied by choice words to László about “your people,” is consistent with a broader climate of hostility: long before the rape, the architect had experienced bursts of antisemitic animosity from Harrison’s boorish son and Attila’s Catholic wife. Indeed, the capper among “The Brutalist”’s hot-button subjects is Zionism, the lure of Israel as a homeland for the Tóth family, when, as Jews, they come to feel unwelcome in America.These themes don’t emerge in step with the action; rather, they seem to be set up backward. “The Brutalist” is a domino movie in which the last tile is placed first and everything that precedes it is arranged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it comes out right. In a way, it does, with an intense dénouement and an epilogue that’s as moving as it is vague—and as philosophically engaging as it is practically narrow and contrived.The result is a work of memorably dispensed invective and keenly targeted provocations. What Corbet films vigorously is conflict, and there’s some lively dialogue to match. The writing is at its best for Erzsébet, a character who demands greater attention than the movie gives her (and whom Jones brings to life with exceptional nuance). Erzsébet converted to Judaism, studied at Oxford, and worked as a journalist cover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she also loves László with a radical devotion, sympathizes deeply with his art, and puts herself at great physical and emotional risk to confront Harrison on his behalf. She’s a scholar and a wit, and László has a philosophical bent, yet Corbet avoids any dialogue between the married couple on subjects of regular personal or intellectual interest. For starters, she doesn’t talk politics and he doesn’t talk architecture, even if both subjects would be prominent in their lives and in the times. Major developments in their native Hungary—say, the country’s 1956 uprising—and civic life in America, from the Cold War and McCarthyism to Jim Crow and the civil-rights movement, go unremarked upon. So, too, do the buildings they see (either in Philadelphia or in their next stop, New York), and, for that matter, the books that they read, the movies they watch, the music they listen to, even the people they meet. Erzsébet and László are presented as brilliant and eloquent, and their brilliance emerges in plot-driving flashes, but they’re largely reduced to silence about the kinds of things that make people who they are. Survival of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too, is an ordeal affixed to the pair like an identifying sticker, devoid of any subjectivity and specificity, never to be discussed by them. Corbet’s characters have traits rather than minds, functions rather than lives; they’re assembled rather than perceived.The film’s impersonality reflects its arm’s-length conception. Its rigid thematic frame—an arid realm of thinly evoked abstractions—carries over into its composition. Though it’s ballyhooed that “The Brutalist” is shot on 35-mm. film, in the classic, cumbersome, and now largely obsolete VistaVision widescreen format, the matériel is detrimental to its aesthetic. There’s very little sense of texture, of presence, of touch: the only images of any vitality are wide shots of landscapes and large groups of people. As for the individuals, they’re defined, not embodied. “The Brutalist” is a screenplay movie, in which stick figures held by marionette strings go through the motions of the situations and spout the lines that Corbet assigns to them—and are given a moment-to-moment simulacrum of human substance by a formidable cast of actors.To sustain that illusion, Corbet also sticks with a conventional, unquestioned naturalism, a straightforward narrative continuity that proceeds as if on tracks and allows for none of the seeming digressions and spontaneity that would make its characters feel real. (In contrast, in “Nickel Boys,” RaMell Ross’s drama of Black teens in a brutal, segregated reform school in the nineteen-sixties, the main characters talk and think freely, whether about books or politics or their immediate experiences; Ross’s script shows his curiosity about their inner lives, and their own curiosity about the world around them.) Corbet’s awkward forcing of his characters into his conceptual framework leads to absurdities and vulgarities—not least in the depiction of László’s first and only Black acquaintance, a laborer named Gordon (Isaach De Bankolé), as a heroin addict. (Their trip to a jazz club, with frenzied visual distortions and parodically discordant music, suggests an utter indifference to the art and its cultural milieu.)Because of the backward construction of “The Brutalist,” what’s of greatest interest is its very ending, which involves an account of László’s eventually reinvigorated career. Ther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film links his stark, sharp-lined architecture to the coldly industrialized cruelty of the Holocaust. Even as this revelation casts a retrospective light on many of the movie’s plot points (such as László’s obsession with the details of his design for Harrison’s grand project), it merely gets tossed out, even tossed off. The ambiguities that result are fascinating and provocative, though Corbet never quite thinks them through: If László is creating, in effect, architectural poetry after Auschwitz, does this poetry redeem the cruelty and brutality of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or reproduce it? Are his designs intended to be commemorative or sardonic, redemptive or oppressive? Is he likening his domineering, plutocratic patrons to his Nazi oppressors? Is “The Brutalist,” with its impersonality and its will to monumentality, meant to be of a piece with László’s architecture? If so, why is the film’s aesthetic so conventional? And if the artist’s ideas are the point, why does Corbet skim so lightly over them?♦
8 ) 粗野派|阿德里安布罗迪二封影帝
阿德里安凭借《粗野派》再封影帝,实至名归。
但是,《粗野派》应该不是简单的讲了个“土木工程”的事儿,《粗野派》野心不小,估计奥斯卡“应该有的”全有了。
故事开始,就警告了哪些“沦为奴隶却错误认为他们还自由的人”,这句话,貌似在为阿德里安的一生做“总结”,但总是感觉有点阴阳怪气的,特别是咱这种牛马听了以后,特别不舒服。
电影时长相当考验“肾功能”,所以,当阿德里安死里逃生到了漂亮国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展示了一下“肾功能”,别说,这一幕,相当的“粗野”。
影帝都这么大岁数了,“肾功能”还在线,观众可别掉链子哦。
昔日的“土木工程”,绝对的天之骄子,但如今,“土木工程”已经沦落到要改专业名称才能“骗”到学生的地步了。
阿德里安到了漂亮国,也只能找老表,当年的画图技术,多少还有点用。
寄人篱下的滋味,不好受啊。
特别是对于阿德里安这种当年的“知识分子”而言。
在等待妻子的这段时间,阿德里安只能苟着。
苟着苟着,就习惯了。
平时,阿德里安也积极练习贯口,技多不压身嘛,说不定哪天就进了“德云社”呢。
折腰至苦。
转机来了。
老表的家具店迎来了大单。
富二代想着拍老爸的马屁(当然,背后的目的也相当清晰),希望家具店能在老爸不在的这段时间,改造一下老爸的书房。
请注意,此时富二代在提需求的时候,提到了要一个“带轮子的梯子”,哈利波特在图书馆用的那种。
老表的心理报价也就700-800,阿德里安直接给侃到了2k,这下,赚翻了。
专业就是专业。
改造吧,人家富二代也不差这俩钱,只要能讨得老爸欢心,将来继承权有望,一切都值。
后来的样板房,大概是这样。
个人感觉,这种一道门开所有门都开的设计,不太符合日常需求,而且,就这结构,带轮子的梯子也没法放了吧,不知道如何解决“上层书架”的问题。
反正,绝对没达到甲方的需求。
甲方的需求先放一边吧。
富豪回来了。
书房还没完工,惊喜变成了惊吓,别说工程款了,没让赔偿就算不错了。
人老外就是直接,老表怎么了,遇到问题,老表也不好使。
当晚,老表就“委婉”的表示,咱这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再说了,你还调戏大嫂,这实在说不过去。
好吧,来说说“调戏大嫂”这事儿,故事里头,当时谈下大单,可是老表生拉硬扯,让阿德里安和大嫂共舞的,就这点事儿,竟然被“秋后算账”了?
当然了,“事实”哪有这么简单,无非是老表一家人都是新教徒,而阿德里安是个犹太人。
被扫地出门的阿德里安,只能到工地搬砖。
这段痛苦的时光,让阿德里安染上的毒瘾。
很多故事告诉我们,这玩意儿沾上了,就戒不掉。
但貌似阿德里安只有在“极度痛苦”的时候才需要,这点还是相当厉害。
峰回路转。
虽然当初富豪对儿子准备的惊喜相当不以为然。
但后来发现,这书房还真好使,关键问题,是“深得上流社会”喜欢。
于是,找上门来了。
有意思的是,富豪其实找不到阿德里安,只能找到老表。
这种事儿,搁在咱这边,完全没有阿德里安什么事儿了,家具店可以“包揽”一切功劳。
不过,人老表虽然“恶劣”,但绝对不会干这种“抢功”的事儿。
不合逻辑,不合逻辑,专利法都规定了,在职期间研发的和工作相关的成果都归公司所有,这老表的脑袋,也不太好使。
眼看着,就错过了泼天的富贵。
阿德里安受邀参加了富豪的聚会。
工地搬砖的阿德里安,甚至连礼服都是富豪借的。
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接踵而至。
当场就有高层表示,愿意对阿德里安的妻子侄女开通绿色通道。
当晚的聚会,主要就是参观富豪的私人书房,让富豪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
其他人还在“社交”时,富豪和阿德里安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
这次不是“面试”,但绝对是“面试”。
富豪讲了一个关于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这个故事已经很明确的表达了自己“做人做事”的规则,接下来,就看阿德里安能“阅读理解”到什么程度了。
阿德里安虽然当下只能在工地搬砖,但,毕竟也曾经是个知识分子呢。
这段“应试”,不卑不亢,绵里藏针,绝对可以入选面试教科书。
当然,阿德里安之所以能够如此,也“得益于”富豪某种程度上的“宽容”。
故事里头,阿德里安的老表和富豪,都不能算是什么“好人”,但即便是这样的“恶人”,还是遵从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放到咱这边,完全可以是“圣人”。
由于阿德里安“卓越”的表现,富豪当晚就宣布,要以母亲的名义在当地建立一座地标,工程总工,就是阿德里安。
这个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
富二代其实还是有点“不高兴”的。
如果,富二代到咱这边进修这么两三个月,完全有一万种方法让阿德里安死得莫名其妙。
但是,富二代毕竟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啊,有什么不满或者有什么“需求”,都是选择当面谈。
而阿德里安也不客气,对方虽然是太子,但该刚的时候就刚,刚到富二代夹着尾巴逃跑。
说实在的,这俩人,放到咱这边,也别考验什么“肾功能”了,一集短剧就完事儿。
从此,阿德里安就安心搞工程了。
也没看到阿德里安给当时宴会上的高层送什么礼,人家就把阿德里安的妻子和侄女给救回来了。
这……在咱这边,明明举手之劳的事情都会表示“很难办”的呢,怎么到了人家那边,真的很难办的事情怎么就没送礼就办成了?
完全不明白。
就别重逢,按道理应该干点什么。
但是,阿德里安的妻子,也是高级知识分子。
这么多年,阿德里安干了什么,她完全用不着证据,就知道。
知道,就会痛苦。
但……这一切都是生活的错啊,两个被生活颠沛的人,还有什么力气指责彼此。
第一次见面,阿德里安妻子“谈笑有鸿儒”的气质,也是迅速吸引了富豪的注意力。
不得不说,看到这里,小编还是相当“阴暗”的认为,这富豪绝对是色迷心窍了。
但,人家富豪虽然不是什么“好人”,却从来都是真诚的“举手之劳”。
要知道,大人物的“举手之劳”,可能就是小老百姓的“破天富贵”。
妻子也找到了工作,阿德里安也大搞土木。
日子逐渐滋润,始终横亘在夫妻之间的那道屏障,也是时候移开了吧。
只是,好景不长。
这段“幸福”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他们夫妻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空洞,再多的“幸福”好像都不能填满。
那心灵深处的痛苦,只是被表面的“越来越好”小心掩盖罢了。
工程出问题了,阿德里安当年承诺把自己工资搭进去的工程,还是没办法继续。
一切都结束了。
刚刚看到“美好”,一下子断了“活路”。
不过,这么多年,阿德里安也算是“小有积蓄”,不用到工地搬砖了,估计是在什么设计院找了份绘图的工作。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吧,直到妻子的侄女提出要回以色列。
这里,始终是“别人的地方”,侄女觉得,只有回到以色列,才是叶落归根。
这个观念,和阿德里安完全不同。
出家就要剃头,就要吃斋。
但是,济公说酒肉穿肠过,佛祖依然可以心头坐。
没有谁对谁错。
工程问题解决了,再次重启。
阿德里安坚持工程中用的石头必须是来自意大利。
富豪虽然霸气,但还是跟着阿德里安去了意大利,虽然富豪平时的谈吐中经常表露出自己“高人一等”的架势,但,个人感觉,一个老板,手下竟然不听他的,还跟着手下瞎掺和,已经相当了不起。
咱这边,不都是外行指导内行么。
这个工程,成了阿德里安心中的一个魔怔。
他,太想工程顺利完工了。
妻子,虽然是知识分子,但也仅限于理解,这是不是阿德里安在“专业”上的追求。
其实不然。
在一次回家的路上,阿德里安压抑在心底的痛苦,得到了一次“大爆发”。
妻子“做爱”的愿望,最后得以实现,竟然神奇的“治好”了半身不遂。
然后,妻子冲进了富豪的朋友圈。
按照法律来说,这确实是一次“莫须有”的指控,一切,都没有证据。
但是,有意思的是,富豪面对阿德里安妻子的指控,一言不发。
即便是富二代依然在“以法律为准绳”。
这段指控,究竟是“实指”还是“虚指”,其实也不太分辨得清楚,故事本身就表达得相当隐晦,相较于阿德里安的两次“肾功能”,绝对的隐晦。
故事的最后,也是上了一顿饺子。
阿德里安的一生,都认为时间能过去,建筑恒久远。
他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
这个观点,遇到强大的“宝姐姐的钗迁队”,一无是处。
9 ) 创伤叙事
这类将艺术与战争创伤相结合的电影立刻让我想到了之前看的《无主之作》。
在我心里是绝对的神作。
的《粗野派》》处理其实与之其实差别很大,但是都给人一种相似的气质。
三个小时以上超长体量,没有直述创伤,最终用艺术达到一种震慑心灵的感觉对粗野派的理解容易产生偏差,查了一下才发现原来粗野派也可以指代粗野主义建筑。
一种东欧战后流行的建筑风格,钢筋混凝土,工业风、极简,战时多为了满足资源短缺时的建筑需求,规模庞大有压迫感,带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冰冷的灰黑色质感投射下战争的阴影,引起对反乌托邦的思考,反而成为一种独特风格。
而片名以-ist结尾词缀似乎更多指代影片中的人。
谁是真的粗野派?
美国人眼里狂放不羁、失去尊严了的欧洲民族?
还是那表面现代化、衣冠楚楚,实则是强暴者的资本家?
他们似乎都是对方眼中的粗野派,或是那个时代本就是个混乱的躁动的暗流涌动的粗狂时代。
在爵士乐的尖利刺耳的咿呀中伴着颓然的夕阳,癫狂着,在酒水毒品性爱中压抑着挥之不去的战争创伤“it's too much”没人知道他们真的经历过什么。
一切控诉和纪述在真正经历过的看来都显得苍白和做作。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咱有部片子可以与类《粗野派》》比,那就是高《青春派》考咋就不是一种创伤呢?
那真是太够创伤了!
简直可以说是集体创伤,或多或少都会给人一点PTSD吧?
但像这种高考题材的电影一般都评级不好,原因就一个字“假”,你对仍和一个经历过高考的人直述高考,很难做到真实,很难还原出那种体制性的残酷,和它对人的思想潜移默化的产生的重大作用。
所以可见这种题材真是少之又少。
但战争题材嘛可能在座的普通观众大部分没有亲历过战争,所以将战争和创伤座位一种奇观来展现在电影漫长的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可以延续到现在,都是管用的。
但可能这种过于强烈惨痛的战争题材真的太多了,观众已然要被相似的叙事榨干了眼泪和共情力,而且甚至加上疫情对人们的思想产生的重大影响,观众越加卸下了潜在的道德对影片评价的影响,战争类型悲惨叙事怎么看都不太高明。
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比较反感表现过于强烈的电影,而本片的战后创伤叙事更有一种深邃感最深的伤痛是无法用影像展现出来的,只能在无言缄默之中引导观众去想象去感受。
关于建筑师的电影真还没见过。
而将战争的创伤融入到建筑中的展现方式更是让人觉得神妙。
建筑本身就是可以视作一种抽象的符号式的存在。
这样也达到了一种符号象征和影片叙事的融合。
“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上层建筑”建筑这次本身就被赋予了一种政治性的、组织架构的宏大意义。
战后建设一个将体育、文化、宗教功能合为一体的四合一建筑,象征着战后对于社群社会的重建。
资本家主动引领着这项工作 ,“建筑风格”上向着现代性,采用来自欧洲意大利曾用来击打国家共和军大理岩,构筑起了现代的美国梦。
而来自欧洲的犹太建筑家本以为可以被邀请参与到这项构建过程中,在这个宏大的建筑中嵌入自己的理想,但至始至终都被视作一个外来者、被施予恩惠的乞丐,被排斥在外。
失语的索菲亚,无法行走但最后仍靠自己站起来面对那些新世界的掌权者发出控诉的埃利兹。
他们如渺小的个体在异国他乡四散流离,延续着他们先祖流亡的命运。
那种被无依之感、那些创伤被印刻在记忆深处,呼应着民族的坎坷命运。
所以他们最终选择回到那片土地与同胞团聚。
可能民族性归属感这种东西必须得处于一个极端的条件下才得以共情看电影时我在想要是取名为“建筑师”不会更合适?
但看完后还是觉得这个名字肯定不行。
象征意味太强。
建筑师太给人参与到社会体系构筑中的感觉,而拉兹洛不是那个建筑师,他最后还是被排斥在外,美国梦对于他而言像许多人的那样,破碎了。
但是他给建筑本身注入了某种永恒不灭的东西,仿佛给这建筑开了光一样赋予了它灵魂他想要赋予他的建筑永恒的意义,超过意识形态简单而纯粹,静默地俯视着时代起起伏伏。
看到结尾才意识到原来他以自己和妻子待过的集中营为原型设计了这个建筑,并用地下联通设计将两个空间连接,象征他们之间永恒的联结。
而狭小天窗的设计则有在苦难中憧憬个体性、自由的意味。
那种个体的真实的记忆与情感赋予了建筑具有超越了时代与空间的坚实核心。
“我可以预见人类愤怒恐惧的众生相,这可笑的洪流也许会不断起伏翻涌,但我的建筑会在动荡中屹立不倒,抵御多瑙河畔的侵蚀”
10 ) 《粗野派》短评
论影像质量和美学价值,《粗野派》绝对远远胜过《阿诺拉》,然而,从影片的内容来看,这部时长超过三个半小时的电影实在是有点冗长乏味,导演费了这么大劲儿拍出了这部漫长的电影,观众却看得很疲倦,与此同时,导演在本片中想要表达的东西太多,却没有一个核心的主题,全片除了宣传了粗野派建筑艺术之外,还涉及了战争、种族、宗教、移民、资本、婚姻、家庭、强奸等议题,但是本片对这些议题都是点到为止,并没有深入探讨,这些议题就像乱炖的大杂烩一样被强行塞进了男主角拉斯洛·托斯的支离破碎的人生,在这样的大杂烩之下,粗野派建筑似乎变成了一种仅仅用于增加本片的艺术内涵的装饰品,不过,正是因为如此,本片才会不涉及任何与粗野派建筑有关的专业知识,观众即使不了解粗野派建筑,也可以顺畅地看懂这部电影。
(本片并不是一部历史人物传记片,本片的男主角拉斯洛·托斯其实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甚至可能连人物原型都没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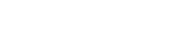
















































当野心只有野没有心 整个电影分崩离析的速度和其本身长度严重失衡导演说电影不应该有长度限制因为小说没有 可是电影向观众要求的是连贯的、实时流动的时间 导演对长度的必要性应怀有责任心 对时间的把控要求乐感和讲故事的功底 眼里没别人的电影 时长越久人物越多也就越难看 这是一部不论故事还是画面都非常平庸 没有人会真的觉得好看 但很适合一部分崇拜小伎俩的人赞不绝口的那种电影@ Camerimage 32
虎头蛇尾了,立意很高很远,但是越走离目标越远。3.5星。
倒置的自由女神,被排挤的美国梦。电影视觉和配乐时而严谨肃穆,时而跳脱不羁,如同设计的建筑风格一样,确实很粗野,也很A24。不了解犹太人漂泊寄生并存的历史,只感觉这个虚构传记太高开低走了,模仿《奥本海默》比较失败,好在先锋的视觉语言足以支持我看完这部几乎三个半小时的冗长电影。在巴以冲突导致犹太口碑下降之际,不得不感叹,犹太人群体真的很擅长宣传自己的民族苦难,时不时来个文娱产品,总是能拔高成普世价值,受到世人同情。然而正如那位鸡奸男主的资本家所说的——看到你们民族对待自身的方式真是可悲,如果痛恨遭受的迫害又为何又把自己搞成容易得手的目标。所以,犹太人擅长宣传民族苦难,以此表达示弱无害,既是称赞,也是诅咒。
明明没有什么戏剧张力,硬是拍出了三个半小时,几乎全程靠争吵和性情节留住观众。2025年能看到intermission的电影真是少见。一流的摄影和表演,三流的成片。这片子留着导演自己回味意淫吧。 ——2025.2.28
用的70毫米vistavision 拍摄,20世纪中期的复古质感还原非常到位,自然光冷色调是真的舒服。Part1让人激昂,道尔镇即轰轰烈烈的美国建国史,配乐一起来就让我想起了《文明6》基建和奇观。一句话:润美才能新生,美帝才是未来!Part2对应美国资本所呈现的压迫和对人的异化,一些狗血情节,不妨看作是美国蛮横的资本强权,而且逐渐腐朽堕落。一句话:资本强奸艺术,美帝无可救药。P2更像是美国梦的破碎。摄影光影构图服化道质感都很匠心,浅焦镜头和手持直观男主迷茫的心灵。败笔在于节奏,材料取舍过于冗长,而且平缓直叙更像是纪实影片,一种静默的枯燥感,一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剧情电影耗在沉冗段落和费镜过多,史诗感就成了便秘感,导演是什么都想加因此很臃肿。ps现代建筑令我深深陶醉,又M了很多建筑书。8.4
这是啥啊 太高级了 看不懂
【NYFF62】今年的Top5。当几分钟的昏暗长镜头终于伴随宏大配乐迎来光明,展现出翻转的自由女神像时,看得快忘记如何呼吸了。真的很喜欢,喜欢这种全然炫技的摄影剪辑和配乐,却完全为不露怯的史诗叙事服务。当然最喜欢的还是Adrien Brody,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痛苦艺术家的脸,太破碎了……演得也好,二十年了奥斯卡也该二封了。以及这片个个选角我都还蛮喜欢的,发胖版的Joe Alwyn演这种无耻b男角色感觉找到了他的正确戏路。
Free Gaza
真的很久没有看这么扎实、流畅的故事片了。主人公的人生在大时代背景下显得那么生动,美国梦的燃起和破碎,家人的离别与重聚…不得不令人感慨在命运面前,每一个人都那么微不足道。70mm的胶片放映,不但让这部野心极大的电影只用画面就能征服观众,更让这种胶片质感为故事和人物增添一份传奇色彩。Adrien Brody奉献了又一次影帝级的表演!
十分钟打片名的时候毙掉导演基本功OK第一个镜头就叠印来到向往的美国后,胜利女神像一直是倒置甚至横着(代表自由美利坚不一定如难民想的那样但是拍男主布罗迪的基本欲望真的可以不拍细节那场,直接跳到和J女做完门口的那场就说明了一切说白了就是不够克制!一直手持摄影,也代表他们的漂泊啦,但是也就那样
这几年少见的电影感。但想说这个甲方简直好到令人发指,以至于我不知道钢琴师大哥在痛苦羞辱啥。以及现在但凡拍意大利为啥都要来点巨物迷幻废墟美学。。。
AMC 导演审美和技术看起来还不错,但后半段不知所云,白瞎了 Part 1 的铺垫和卡司,电影空洞得如同AI设计的那个institute(但是,已经被重复过无数遍的设计语言还是取悦到我了,我喜欢 dramatic 不宜人的空间癖好一点没变。而且做多了木头小房子,看到混凝土和大理石非常满足,老头儿摸着大理石的高潮表情完全可以共情,我现在偶尔有机会摸到做工精良的清水混凝土也是爱不释手)一起去看的朋友看完问我:你们建筑师工作就是这样的吗?我:无语凝噎……
完全没有想说的
混乱的剪辑,混乱的音乐,投机而蹩脚的剧本,难以理解的冗长,烟、酒、毒品和性简直就是某些无能导演塑造人物的典型方式,为奥斯卡量身定制的传记片。这种没有任何真诚内在的电影让我感到很恶心
从一开场倒立的自由女神像便表达出导演强烈的“反美国梦”的主题,在逆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真的还需要关于“美国梦”的电影吗?原本以为会是一部如同菲利普·罗斯《美国牧歌》般讲述一个中产家庭走向灭亡的故事,可惜电影的内容承载量还是不如剧集或文学,但布拉迪·科贝特依然拍出了属于他的史诗感。没有什么比建筑师这个身份更适合讲移民身份了,外国人、移民、异教徒,多重身份却构建一栋屹立的社区建筑,对本地人无疑是强大的入侵。不禁让人联想扎哈在其生涯中不止一次因其身份还引发对其创作的排斥。结尾的双年展也让人想到24年威双的主题“处处是外人”,这一路却花了129年。最后,粗野派对水泥的运用,某种程度上不也是移民?便宜、坚固、而又耐用。
我花了四个小时竟然看了一个以色列宣传片
是有点失望的 因为期待过高 先说喜欢的点:70mm胶片电影质感超绝 音乐和摄影top notch 但剧本真的不行 或者说这样的篇幅讲这样的故事没讲好有点遗憾 想要兼顾的太多 结果全是过眼云烟 一场盛大的史诗级叙事之后我对男主的一切还是知之甚少 最后展览上侄女的发言更是挺无语的吧 很想反驳it's not the destination, it's the journey. 但想想这样的journey也挺食之无味的
建筑师在美国重塑自我与以色列顽强独立形成呼应,由此暗示导演可能会认同一条我们非常熟悉的口号:“强大的祖国是我们坚强的后盾“。抛开犹太复国主义的种种争议不谈,在战后体系行将崩塌之际,布罗迪忧郁的面孔倒使弱肉强食多了几分正当性(吊诡的是以色列今日的强势正是的反对弱肉强食的体系赋予的)。对Brutalism及其共产(社会)主义、平等观念的根源避之不谈,但整个建筑项目的执行打着公共利益旗号欺骗宾夕法尼亚老乡,倒是颇有极权政治之风。对大屠杀的哀悼主题直到最后才揭露,而在社区宣讲会就只大谈建筑和信仰的永恒,对当地居民悼念权的漠视潜藏的是艺术家的自溺。而这种自溺承载着道德的绝对合法性盛行至今,使犹太人身份某程度上变成了加害更弱势者的武器。美国梦是破灭了,民族主义的春秋大梦正以和平之名肆虐。
三小时浓烈的意第绪味无英字英文轰炸,环球是真傲慢啊,很多没看懂的地方,但估计也不会再看了。第一章非常喜欢,胶片的光感跟主角亢进的状态保持了一个合适的距离,以片刻的安宁将美国梦的反面根植。然而之后,明显感觉到建筑师身份带来的信息特质,以及家庭婚姻的加入让主线多次偏轨。结果是仍然会慨叹,但阶级差距导致的身份跌落力量感锐减。大银幕看不失为一种视觉按摩
#BFI #70mm #Preview 长评-美国梦破碎在资本牢笼。电影以角色的内心作为主要驱动,从角色的孤独到社会结构的冰冷逐层深入的呈现,移民建筑师拉斯洛一家在美国的经历展现了资本如何吞噬梦想,人性和生命。结构可分两部分,一以信件作为主线来展现拉斯洛的内心世界,二则是妻子来到美国后两人共同的经历。他被束缚于资本的牢笼,他妻子则是被普渡止疼药毒害。侄女在片中的沉默成为战争创伤和资本吞噬未来的一种具象表达,而开场与结尾的对照也是预示着这些都是历史创伤的不断重演。构图和大量浅焦很棒,手持跟拍呈现的抖动和POV的升格特写镜头也很大成度帮助呈现了男主的内心。广角仰拍体现权力,纪实风格的画面打破现实与虚幻的边界。音效和配乐在两幕变化明显,片尾曲也是极尽讽刺。建筑如同电影,讽刺美国资本想到了《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