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天空》剧情介绍
一个炎热、干燥的夏日,如同过去几年一般。森林火灾是无法控制的。四个年轻人在离阿伦斯霍普不远的波罗的海度假屋里相遇。慢慢地,不知不觉中,他们被火焰筑成的围墙所包围。红色的天空笼罩着他们。他们充满怀疑,他们满是害怕——但却不是因为火灾。是爱让他们害怕:“谁会在坠入爱河时死去 ……!”他们越来越亲近,他们渴望着,他们相爱着。然而熊熊火焰已无限逼近。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深海兽银河守门员篮球冠军2电波少女大恋爱:与将我忘记的你雪花飘落以下事件基于一堆谎言吉米·卡尔:笑点狙击手颅骨印记迷雾刺杀准许你好,我的银色恋人红天鹅在路上基努猫清理门户蛮战第二季拉斯维加斯第二季变身辣妹刺客3秘密的时光新奇孤独的美食家第十季我的恶魔少爷无言性爱大派对黑色星期一第三季铁窗怒火续集第六巴士蜜蜂少女队
《红色天空》长篇影评
1 ) 年度十佳备选,来自疫情期间的夏日春梦
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谈《红色天空》作者:Devika Girish译者:酶原文链接:www.filmcomment.com/blog/interview-christian-petzold-on-afire/就像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导演的众多电影一样,《红色天空》是一个美丽女人与望穿秋水的男人陷入命运旋涡的故事。
《过境》(Transit ,2018)和《温蒂尼》(Undine,2022)诉诸历史来诱捕他们的恋人,《红色天空》则牢牢植根于当下,这是佩措尔德“元素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第一部是《温蒂尼》,讲述了一个水精灵和工业潜水员之间的爱情故事)。
这部电影将年轻的主角们——两名艺术工作者和两名服务员——放置于环境衰溃的边缘,一个被野火损毁的森林里。
盛夏,小说家Leon(托马斯·舒伯特 饰) 和摄影师Felix(兰斯顿·伊贝尔 饰)到达森林小屋准备开展各自的工作,结果发现这间小屋早已被一个神秘的女人Nadja(葆拉·贝尔 饰)率先占领。
Leon像很多作家一样自以为是,正着手准备他的第二部小说,并对Felix悠哉的心态和冰淇淋售卖员Nadja明媚的性情感到恼火,她的生活很充实,每天骑单车工作,笔记本上写着潦草的哲学沉思,与救生员David(恩诺·特雷布斯 饰)过着聒噪的性生活,这些似乎都困扰着Leon。
托马斯·舒伯特和佩措尔德热衷于让这个角色成为悲情的傻瓜(也许对于作家来说是很容易识破的),通过紧锁的瞥视、凝视以及故意挑事的俏皮话来刻画他的不安。
《红色天空》剧照《红色天空》是一部经典的佩式风格的现代主义情节剧。
昏沉的浪漫和毁灭性的灾难简化为资本主义世界无情又空洞的惺惺作态,但这也是这位导演迄今为止最为奇趣古怪的电影,一部将命运的奇诡置换为后现代闹剧的电影。
爱与死,以一种锐利的不协调的方式若隐若现,这部讽刺情节剧关于艺术创作的平淡无味,劳工阶级的感性,以及面对吞噬一切的灾难时的徒劳无功。
今年的柏林电影节期间,在《红色天空》荣获评审团大奖之前,我与佩措尔德见了面并关于电影展开了对话。
佩措尔德凭借《红色天空》获得评审团大奖Devika Girish(以下简称DG):我很好奇这个英文片名Afire,因为它与德语片名Roter Himmel不同,德语名译作“红色天空”。
佩措尔德:我之前从未听说过“afire”这个词,但是我喜欢它发音,我是说,“燃烧”是一个动作,而不是一张彩色照片里的图像,原初题目是《幸福的人们(The Happy Ones)》,但是已经有一个导演用了这个名字,所以我不得不修改,我的答案对你来说有点长,没问题吧?
DG:没问题。
佩措尔德:我今天很孤单,所以很乐意聊一聊。
DG:那太好了。
佩措尔德:三年前柏林电影节结束后不久,葆拉·贝尔和我必须去巴黎为《温蒂尼》做一个展评,那时新冠疫情刚开始,我们坐在餐厅,就像在战争期间一样,音乐被关掉,人们都盯着角落里的电视屏幕,马克龙宣布:“明天将全面封控。
”葆拉和我必须立即返回德国,我们感觉从巴黎的逃离,就像电影一样,两个人租车穿越绿色边境。
我们在巴黎的分销商是来自菱形影业公司(Les Films du Losange) 的玛格丽特·梅内格兹(Margaret Menegoz),她是埃里克·侯麦和雅克·里维特许多电影的制片方,她给了我和葆拉所有侯麦电影的光盘(25 张 DVD)作为礼物。
我和葆拉回到柏林后都感染了新冠病毒。
《红色天空》剧照DG:就是那时候你做了一些狂热的梦。
佩措尔德:嗯,确实是一些好梦。
DG:我记得我们2020年讨论的时候,你就说过这个。
佩措尔德:那时我们购买了乔治·西姆农(Georges Simenon)一本书的版权,那是一个关于在法西斯压迫下年轻人丧失道德文化的反乌托邦故事,但那时我一点也不想拍反乌托邦电影,观赏着侯麦的影片,一些事情跃入脑海。
在美国和法国都有“夏日电影”这种题材,比如说《不眠神话》(The Myth of the American Sleepover,2010)。
在夏天,有两个月的时间,父母都不在身边,青年人找寻身份认同。
在法国有《情感教育》(Education Sentimentale,1962),当你长大成人时,你可能会记得这些伤痕,一些伤害过你的事情,向你描摹过世界的东西。
《不眠神话》剧照DG:这是你经历的事情,还是说在电影中看到的?
佩措尔德:这是在电影中看到的。
但是在德国没有这样的类型,德国的父母总是等待。
在夏季,我们折返退步,然而在法国和美国的家庭中他们稳步前进,所以这些也是我的想法和发烧时梦中的一部分,我做过很多春梦,我都记不得了,但是一直有对夏季、对户外、对触摸(touching)的渴求,当时德国有一些言论表明年轻人受到新冠肺炎压制是个好事,因为他们过着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他们就想吸大麻,去俱乐部,不想工作。
我不喜欢这样的言论,我两个孩子,他们现在都成年了,他们那个时候很沮丧也很厌恶这样的言论,然后我读了契柯夫的短篇小说。
DG:哪一本?佩措尔德:《带阁楼的房子》(The House with the Mezzanine,1896),它是一个关于艺术家的故事。
书中有两个艺术家,一个作家、一个画家,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但是他们中的一个有钱有大房子,他们整日在那所大房子里闲散度日,不作画,不写作,沉溺于思考。
附近有一所俩姐妹和母亲同住的住所,有一个女孩是共产主义者,想要改造社会。
这两个小说中的男人,都是失败者,错失了爱的机会。
我开始带着这些记忆写作,侯麦,里维特,疫情,书写那些叫嚣着“你的假期已结束,你要去工作了”,但反手又摧毁星球的成年人们。
三四天之后,我写完这个故事,起名为《幸福的人们》。
因为每个人都告诉他们,你们是幸福的一代,你们无所不有。
当然,后来我不得不改名。
我想起了我最喜欢的一部来自六七十年代的新德国电影中鲁道夫·托米的《红日》(The Red Sun,1970),它的结局有点像《阳光下的决斗》(Duel in the Sun,1946),在慕尼黑附近的一个小湖边,他们因为深爱对方而互相开枪射杀。
美国片名更好一点,更加情节剧一些。
《红日》剧照DG:是你选的美国片名吗?
佩措尔德:不是,但是他们问过我。
有一部我特别喜欢的电影,霍华德·霍克斯的《峰火弥天》(The big Sky,1952),它有一个场景也像《阳光下的决斗》一样,他们怒揍对方,然后就通过暴力开始了一段友情,我很喜欢这一幕,但我觉得《红色天空》听起来太像西部片,所以我更中意Afire。
DG:你拍这部影片时也有在参考一些恐怖电影吗?
里面有80年代的恐怖元素,两个角色驱车前往森林,车子坏掉了,然后他们看着天空寻找一些火灾引发的不可见的怪形。
佩措尔德:我很喜欢这种类型的电影,比如说《隔山有眼》(Hills Have Eyes,2006),美国关于年轻人的电影经常是恐怖电影,比如《十三号星期五》(Friday the 13,1980),就像《情感教育》中的年轻人,待在他人的车中,他们中有一些是工人阶级,一些有有钱的父母,他们必须一起学习一些东西,在美国恐怖电影中,因为他们没钱,基本上都是通过暴力来学习。
《隔山有眼》剧照DG:在法国他们通过爱学习。
佩措尔德:爱与暴力……夏日时光。
另一件事是当他们到那里时,森林里有个房子。
我给我的摄影指导汉斯·弗洛姆(Hans Fromm)说我们得让摄影机做一点小小的改动,它必须看起来像德国童话故事《汉塞尔与格雷特》(Hansel and Gretel)的房子,然后摄影机的下一个位置要在室内。
当在电影中展示房间时,你只能两者择其一,你可以把摄影机放在室外,角色到了之后拿出钥匙开门,进入房间;也可以在房间里等着他们,这两种拍法有天壤之别,第一个方式表明,这在夏天,这是他们来这儿的第一天,第二种拍摄方式展现的是有些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了。
我是上世纪90年代学到这些的,那时我和朋友哈伦法罗基(Harun·Farocki)在布鲁克林待了两个月,旧金山有一家图画小说店,里面有许多年轻的图画小说家,大卫·拉帕姆(David·lapham)写了《流弹》(Stray Bullets)这样的系列小说,我印象很深,他的图画小说的第一页都是房间里的图景,开始每件事情都很协调安然,突然一个声响“咔哒”,有人用钥匙开门,完好的和谐氛围被惊扰了。
这里的人是惴惴不安的,而房子是完好的。
当人们在屋外时,一切都很好,但他们突然破门而入,就带来了他们的麻烦情感纠葛。
《红色天空》剧照DG:您总是非常关注工作,这尤其体现了现代工作的本质。
在《红色天空》中有许多对话都是围绕工作的构成而展开的,做饭、游泳、写作,你也通过角色Leon来讽刺脑力工作的名不副实,为什么这种主题来说对你这么重要?
这似乎和你认为夏季的悠闲属性这个观点有关联。
佩措尔德: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就得追溯到电影史的第一部电影,电影中的工人离开卢米埃尔工厂,但是你看不见他们工作的场景,只能看见他们离开工厂,所以电影与工作无关。
上周我看了保罗·施拉德《蓝领阶级》(Blue Collar,1978),他展现的确实是工人在工作,这在电影中并不常见,因为没有工作电影,我们对工人的性生活、色情以及生活状态都是漠然的。
五六十年代,老师问青年们,你们长大想做什么?
他们回答“我想成为一名护士”或者“我想成一名美发师”。
现如今,人人都想当作家、演员、创业家,所有生产与涉及手工制作的东西都过时了。
但是40岁时他们想再次从事悠闲的工作,在自家花园里种植一些有机食物。
《蓝领阶级》剧照DG:手工作业。
佩措尔德:没错,《红色天空》中Leon饰演一名作家,他像作家一样抽烟,坐在像舞台一样的工位上,但是这一切都是虚渺。
而且Felix也不想要做摄影师这样的工作,他想重建房屋,想修屋顶,女孩Nadja总在工作,她总说抱歉,我要工作了,她必须赚钱。
在过去的电影中,女孩是半裸地待在泳池边,成为男性主体的欲望对象,我想改变这个,影片中女孩是唯一一个总骑着她的自行车买食物、准备三餐、夜晚有性生活的人,她是主体不是客体,所以他人就被她扰乱了。
他们通过窗户看她高潮迭起,在以往电影中,他们可能会说,我想要她,我想立刻得到。
但在这里,他们尽管被深深吸引却心怀忌惮。
DG:你把Leon描绘成一个吊儿郎当的作家,你写这个角色时是否有想到你作为导演的身份,或者你对艺术作品的感受,以及它与体力劳动或专业劳动相比如何?
佩措尔德:有一部电影,总让我羞于面对,是我自己的,我从来没有用这部电影上过大师课。
这是我的第二部长片《自由古巴》(Cube Libre,1996),不算很差,但是拍电影的时候是我人生跌入谷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拍了长片首作《飞行员》(Pilots,1995),大获成功。
并且大概八个月后,我又为第二部电影筹集了很多钱,我被评论赞赏,又有一些新朋友,坐在像今天这样的酒店里会谈,我信马由缰,我写剧本很快,通常两到三个月,那个时候的我就是一个假内行,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假行家。
比如说我的电影中有很多桥段都来自于我最喜欢的电影,有个情节来自于《绕道》(Detour,1945),我想向世界展示,我是懂电影的知识分子。
《自由古巴》剧照在《红色天空》的拍摄期间,我们排练正在讨论Leon的第二本书《三明治俱乐部》的时候,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自由古巴》和《三明治俱乐部》之间是有一些联系的。
你不需要为此展开精神分析,它就像一份菜单,一份《自由古巴》和一份《三明治俱乐部》,谢谢。
它是Leon第二本书的书名,也是我的第二个电影。
这是我在夏天拍的电影,在这部电影中我学到了一些关于我自身的东西,关于自恋的构造,关于集体工作的价值。
《红色天空》的作者必须去学习,比如说我,是的,是有自传倾向的,但是我不想这样,排练期间,我就说“天呐,怎么是关于我的”;下一部电影是关于一个女人的,不是关于我的。
DG:我最喜欢的一个电影场景是在晚饭时,我们了解到Nadja是一个文学学者,她参考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的中篇小说中的《智利地震》(The Earthquake in Chile,1807),然后朗诵了海因里希·海涅写的一首诗歌《阿斯拉人》(The Asra),使我想起葆拉在《温蒂尼》的两次演讲,在这里她也用无比柔美的嗓音吟诵了两次。
佩措尔德:我学过文学,读过电影中维尔纳·赫德曼(Werner Hamacher)写的的这篇文章,发生在里斯本1970年的一个历史崩溃节点,因上帝在那时弃我们而去了。
如果是上帝制造了这样的地震的话,相信他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康德、黑格尔,他们都讨论了这场地震。
冯·克莱斯特的中篇小说的结构和节奏都是摇摇欲坠的,不只在内容,形式上也是。
就像你在电影节上总是讨论电影的内容,这是一部关于乌克兰,关于土耳其地震,关于伊朗的电影,总是“关于”的电影,你可以从克莱斯特的小说和哈马赫的文章中了解到,不仅仅是讲述“关于…”的事情很重要,作者本人在他所讲述的东西里被深深触动同样也很重要。
当Nadja吟诵《阿拉斯人》时,她不仅仅讨论在相爱中死去的人,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讨论音律,讨论德国。
在德国,我们没有音乐,再看比如说《天堂之门》(Heaven's gate,1980)这样的电影,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欧洲人都把他们的音乐带到了美国:有吉普赛人、波兰人、德国人;非洲人还带来了蓝调音乐,纳粹摧毁了我们民族的音乐,我们失去了自己的韵律诗歌。
我看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采访,她在纽约生活了30年,他们问她做梦是用哪种语言,她说是德语,来源于她小时候读过的所有的诗。
《红色天空》剧照DG:我对你所说的这两篇文章都比较感兴趣,一个是《阿斯拉人》,另一个是《智利的地震》,因为它们都是讽刺亦或瓦解浪漫主义的例子。
在你的电影中,爱通常是一种激进的力量,它让过于理性、过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世界重新焕发魅力。
《红色天空》给人的感觉不一样,它更加愤世嫉俗,在这部影片中,面对灾难和死亡,爱束手无策。
佩措尔德:这部电影中,爱的力量、爱的浪漫、爱的暗夜,这些构造我都没有沉溺,我更加感兴趣的是,集体里、团队里,我们必须要学一些东西。
爱不会一成不变地存在,他们必须为爱付出。
在诗中有爱,景中有爱,夜晚的肉体欢愉中有爱,两个人亲吻时有爱。
你也可以看到爱在渐次累计,是一种爱的耕耘,而不是一种浪漫主义的。
在大多数灾难电影中,角色通常需要一种意外状态,比如高楼大厦的坍塌,这样他们才能找到自己,在那种危急情形下,你可以看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但在这部电影中角色完全都是无辜的,就像现在的年轻一代一样,他们什么都没有做,父母祖父母携手资本主义世界,一起摧毁了所有。
因此当灾难发生时,他们是不会从中学到任何东西的,他没有时间去领悟任何事情。
《红色天空》剧照DG:在电影中Felix对他的摄影作品有一个想法,从人们身后去拍他们看海的肖像,然后再从前面拍摄。
灵感来自苏菲·卡尔(Sophie Calle)的《看海》(Voir la mer)吗?
我读过她在《卫报》上的访谈,他和Leon在电影中说的话很相近,就是她不想从前面拍人们的肖像,因为这样他们就会看着相机,而不是大海。
佩措尔德:是的,没错,我想我们读的是同一个采访。
我们十年前制作《芭芭拉》(Barbara,2012)时,我记得尼娜·霍斯(Nina Hoss)有一张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拍摄女儿的照片,你可以从后面看到某人的身影,开始想他所想,你开始读取信息。
《芭芭拉》剧照DG:你说你现在正在制作一个元素三部曲,《温蒂尼》是水元素,严格来讲这部电影就是关于火的,但是你又绕回到大海,为什么大海对你来说如此重要呢?
佩措尔德:阿涅斯·瓦尔达去世前的三四周,她来上了这些大师班。
她说“海滩是拍电影的主阵地,因为海水、泥土、微风、孤寂,这都是摄影机需要的。
”电影反对孤独,但你必须知道电影的孤独是什么?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样的,但是下一部电影是关于…DG:关于海洋吗?
佩措尔德:是的。
和海洋有关!
(大笑)- FIN -
2 ) 燃烧的寓言!四人行,只有他敢这么拍
热门电影《红色天空》是德国导演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元素精灵三部曲”的第二部,在今年柏林电影节被授予评审团大奖。
第一部《温蒂妮》拍的是“水精灵”,这部则是“火精灵”。
在故事和元素这两者的明晰程度上,两部影片恰好相反。
2023《红色天空》在前作《温蒂妮》当中,虽然故事带有一定模糊性,但精灵元素则非常清晰。
女主角温蒂妮在遭遇背叛之后,迅速与另一男子深陷热恋,当现男友怀疑她依旧对前男友心怀留恋、甚至还因为她成为植物人时,温蒂妮杀死了前男友,并从此沉入水中。
2020《温蒂妮》这里的水精灵指的便是女主角温蒂妮。
但整个故事具有复杂的多义空间,即通过呈现温蒂妮的水妖气息,以及在杀人案中注入蓝色、冰冷的灵异感,使影片脱离现实束缚,带有一丝中世纪神话传说的韵味。
加之女主角“城市发展局顾问”的身份以及她在工作中对柏林历史的解说,使这丝韵味更有迹可循。
《温蒂妮》相反,影片《红色天空》的故事完全落点在现实世界。
一座海边的房子,作家莱昂、摄影师菲尼克斯、冰激凌店店员娜迪亚、海滩救生员德维这四个青年男女,正在度过一个侯麦电影式的浪漫夏天。
房子附近围绕着森林,山火肆虐。
随着老年出版商维尔纳的到来,四人的命运迎来了残酷改变。
影片未将故事或情感引向任何超自然或超验的方向,观众不必怀抱观看《温蒂妮》时留下的“后遗症”,以一种紧张的目光注视电影《红色天空》中的每一个细节,而完全可以放松下来享受这个并不难懂的故事。
但什么是火精灵?
谁是火精灵?
影片却并未明确告知。
如果从火的颜色来辨别,那么可能是经常一袭红色连衣裙的娜迪亚;如果从精灵名字来辨别,则可能是拉丁裔摄影师菲尼克斯(其名Felix与火象精灵中的Phoenix发音近似);而如果从角色之间的区分来辨别,莱昂就是火精灵,因为其他三位青年经常相约去海中游泳,和水关系亲近,唯独莱昂,从不游泳。
直观而言,影片《红色天空》中的火元素即山火,以及山火染就的红色天空,还有火灰飘落如雪的充满色彩对比的气候。
佩措尔德导演曾经解释道,他热衷于两种火,森林中的、气候意义上的火,以及心中的火。
有时候,火是一种保护,它将年轻人同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有时候,火又是一种摧毁,因为山火最终烧死了他们中的其中两人。
这两人是一对同性情侣。
严格来讲,影片《红色天空》并非一部同性电影,而只是拥有同性元素。
但这种同性元素表达的典型性,使这部影片仍可被放进同性影视的分类中进行品鉴。
目前的同性影视,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童话,如《心跳漏一拍》《星条红与皇室蓝》。
这类作品在非真实中刷掉所有令人不适和痛苦的部分,构建一种极度纯洁的幻想,迎合观影群体将同性恋情唯美化的出世心理。
2023《星条红与皇室蓝》第二类为性而存在,如阿根廷导演马可·伯格所有电影。
他只拍同性电影,乍看,他往往都是以细腻的暧昧情思来呈现男性之间的情感递进,但这种递进正是以性为引。
为此,马可·伯格电影里演员们的身体姿势和细节都有非常准确的设计。
比如《夏威夷》当中,两位男主角躺在床上小寐,画面虽静止,但身体的曲峰与凹陷、体位的前进与迎接,都如最高超的摆盘一样,看似随意,实则引出欲望的峰浪与毫颠。
而演员欲藏欲露的着装,更将这份表达推向极致,恰好很符合《红色天空》导演佩措尔德所说的“(漂浮弥漫在)空气中的性”。
2013《夏威夷》但《红色天空》的同性表达与马可·伯格不同。
马可·伯格选择的是一条并不长远的路,导致其后期作品只能依靠重重的肉体堆叠和少量的奇情元素来维持光影情欲,而无法真正触到同性电影的本质魅力。
佩措尔德则不同,他的同性表达有“空气中的性”的成分,但却精炼而严肃。
这正是第三类同性影视的特征。
影片中,菲尼克斯和德维之间的恋情,始于一个“变基喷雾”的故事,其表现只有一个吻、一句“他是我男朋友”(菲尼克斯向出版商介绍德维),以及一场夜晚的几近无声的性。
最后,这种简单竟完结于一场庞贝古城式的殉死,可谓是紧密而悲壮(庞贝古城当年毁于火山爆发,后世考古曾发现有情侣在火中相拥而亡)。
这也恰好对应影片中娜迪亚朗诵的海涅诗歌《阿斯拉少年》的最后一句:一旦相爱,注定消亡。
然而,菲尼克斯和德维的恋情并非《红色天空》的重点,影片的重点是莱昂和娜迪亚之间的关系。
莱昂是一名非常典型的自负的作家,他甚至是完全的自我中心论者。
在如今这个土地和自我都愈发封闭的时代,不少影迷对莱昂的第一感受便是:他是我自己。
他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相当突出,比如他永远号称自己以工作为重,从而拒绝朋友们的所有邀约;对自己的小说《三明治俱乐部》迷之自信,几乎不接受任何批评;以及没有驾照,认为车始终会有别人来开。
还有一点,他热衷于窥视。
初见娜迪亚时,他隐在门边,窥视身穿红裙的娜迪亚自林间小路逶迤而去;初见德维时,他则藏在毯子里,在夜色里窥看德维的裸身消失;即便在经历过山火之劫,一切理应放下的最后,他依然会退到树的背后,窥视娜迪亚在出版商维尔纳的房间进出。
在莱昂看来,即便娜迪亚比他有才华、德维比他性感,朋友们的群聚比他的孤独更令人愉悦;但只要拥有窥视视角,那么他自己就是高于被窥视者的,就是美和艺术的上帝。
这从他批评菲尼克斯的摄影构思即可看出。
菲尼克斯想拍一组看海人的照片,先拍摄他们的背影,再拍摄正面,但莱昂言辞激烈地抨击了这一构思。
因为当相机转到看海人正面时,他们就不会再看海了,而是会看向相机。
背面代表窥视,正面代表交流,莱昂只想窥视,不想交流。
因此,试图与莱昂交流的娜迪亚,往往会如同碰到一颗坚硬的石头。
比如娜迪亚说,我(对《三明治俱乐部》的书评)是不是太苛刻了(她不喜欢这本小说);结果莱昂答道,我不会把那称为书评。
一句如此阴阳怪气的话,显见莱昂既试图挽回自己身为作家的尊严,同时又贬低了娜迪亚的身份,关上了娜迪亚打开的那扇试图交流的门。
即便最后他对娜迪亚说,自己喜欢她,但这似乎也只是一个普信的直男再也无法以自己的高傲来驱动他人时,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和让步。
所以他才会一有机会,便又退回窥视别人的“安全世界”当中。
无论是菲尼克斯和德维,还是莱昂和娜迪亚,他们在森林与海围成的房子中,都如同一枚拒绝尘世的标本,只是标本内部的情感始终在流动。
山火映出的红色天空。
包裹着这枚孤独的标本,仿佛一个永恒的火的精灵。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菲尼克斯和莱昂只能够徒步走近房子,而注定无法驱车前来;当菲尼克斯和德维驾着拖拉机去拖车时,他们则被烧死在途中。
因为,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夏日寓言。
如果你想进来,或者想出去,必受热的灼烧、火的吞噬。
作者| 县豪;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3 ) 柏林学派名导佩措尔德三部曲之二|本周热榜第二
大家好我们是弯弯~今天是9月6日,农历七月廿二,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来自德国的影片《红色天空》,全片时长103分钟。
这是在今年2月柏林电影节上映的影片,内容大致就是四个年轻人阴差阳错的在一个房子里生活,最后山火烧到了家门口,年轻人直接嘎了一半,剩下的年轻人在事情过去后又重逢了。
我们要想真的了解本片,了解导演的意图,了解山火和游泳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了解本片的导演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这位德国导演可不简单,他是德国当代电影思潮“柏林学派”的代表和领军人物,本片是他“元素精灵三部曲”的第二部,猜猜本片中什么是火元素精灵的表现?
那么柏林学派又是什么?
一句话概括:欧洲艺术电影界公认的清流。
如果你对该学派和导演很感兴趣,不妨查查看,但如果只是抱着看电影消遣的目的话,让我们接着往下走。
专业人士去看专业的;就想看个好电影放松的就去单纯欣赏。
本片从路人观者角度来说,没有那么“神”。
主角小哥长相绝对谈不上帅气,甚至性格还很不讨喜;从文化角度来看,本片的冲突,最起码咱们国人很大概率Get不到,看情节只会满头问号;整个影片故事本身,围绕主角“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作家展开,这个故事并不是很“完整”。
本片里有男女、男男、娇喘、海边、绝症、冷笑话等元素,有着满屏幕的焦虑感和写不出东西那种便秘的感觉。
山火贯穿始终,那辆半路抛锚的红车也是头尾相接。
本片中提到了这么一首诗,保留尾句展现出来:“一旦相爱,注定消亡”或许这也寓意着日后这几个年轻人的结局。
我们的男主角似乎有意做一个纯粹的观察者,但是他不知道,从他和朋友进入这个被山火包围的地方后,他就已经陷进来了,点击阅读全文,去看看这场烧在山上的火,以及落在心上的伤。
4 ) 红色天空,蓝色的梦,你说过的话星星听得懂
它比《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隐喻更强,清晰可见。
一个增肥到站在迷路的树林里,野猪都能扛着行李与之一战的男人,首先,他有强壮的身躯,意味着可以抵抗软弱和情绪的不稳定,让人看似可靠、信任、充满性吸引力,敦厚的身材对于男人不是减分项。
菲尼克斯深陷情网,有肢体接触的打打闹闹令他欲罢不能。
其次,这个男人还拥有与生俱来的白皮肤,他几乎站在歧视链的顶端。
他们的车抛锚了,超市的收银员确认附近的修理厂没开工,方圆百里就这一栋孤零零的房子,欧洲电影很爱营造木屋困境,悠闲又带着点悬疑。
远远的火灾,在或近或远处显现,而他们就在这片乐土里,德维和娜迪亚在一起,菲尼克斯爱上德维,他们一同死在森林里,拥抱着。
一切激烈的情感都与里昂无关,他有工作要完成,分配给他的藤架是避风港,事实上,他的第二本书《俱乐部三明治》早就完成了,没有东西要写,他拿着去游泳的菲尼克斯随手扔给他的网球玩,偷偷溜到主卧房间翻看娜迪亚的小本子,他不和超市收银员讲话,不和菲尼克斯去游泳,他什么也不做。
他是无知无觉无感的胖子,只关注自己,具象化为手边可能会出版、成名的书。
他还势力,无意中撞见娜迪亚卖冰淇淋,以为她是路边小贩,不愿意把手稿给她过目,类比如菲尼克斯的保洁母亲,而里昂正免费住在菲尼克斯父母亲的海边房子里度假。
在他眼里,唯有写作、收集作品集才是正经工作,诸如做饭、清洁、修理房屋、售卖冰淇淋不值一提,享受又格外傲慢的男人,傲慢如狮子。
人与人之间感情自然流动,德维和菲尼克斯一起抬着梯子放进仓库,梯子拉扯着彼此的心,裸着上身,是汗水,是协作,是诱惑;出版商赫尔穆特欣赏着菲尼克斯的作品集,真诚建议他除了看海的人正面和背影,加上第三个层次,大海,必要时他会提供文字修饰的帮助;赫尔穆特关心娜迪亚的专业,她的文学研究,海涅与《罗曼采罗》。
这一切,里昂一无所知,他咒骂菲尼克斯难看的作品集,那个卖冰淇淋的女人,他一把推开娜迪亚,以为在四号病区,娜迪亚对赫尔穆特说的只有他的垃圾作品,赫尔穆特把他推给女实习生接手。
他亲眼见证菲尼克斯和德维紧紧握着手,被烧灭殆尽的躯体,他没有眼泪,脑海里转动庞贝古城的画。
没有跳进爱与恨的泥潭,深深搅上一搅,总是隔岸观火的男人,写不出什么好东西。
赫尔穆特念出来的那一段,他望着怀抱婴儿的女人,想的还是那些轻盈的东西,吃汉堡,去外面飞奔,酒吧嬉闹,孩子呢,婴儿粪便,低矮排屋,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里昂是个幸运的男人,他什么都不懂,通过娜迪亚、菲尼克斯、德维鲜活生命的触动,他完成了可以出版的稿子,转瞬即忘的女人,忘不了的故事。
他一如既往以最坏的恶意揣测她人,赫尔穆特联系了菲尼克斯的母亲,他以为他们在讨论改了名字和地点的书是否侵权,不,赫尔穆特想在书里用菲尼克斯拍的那组作品集。
里昂的书根本配不上菲尼克斯的照片,他的傲慢遮蔽了一切,他不懂任何人,他也不会理解,娜迪亚仍和赫尔穆特有联系,来看望他,她们根本没提到他,尝试坐在轮椅,飞转轱辘的快乐,那是心理或身体有部分残缺,需要被人填满的快乐。
他身体很棒,很完全,一个健全健康的人,脆弱感与他完全隔绝,他也与世界的丰富完全诀别。
攻讦、利用、剥削是他的手段和形式,不懂爱的人,多可悲。
5 ) .
Roter Himmel 红色天空 Afire 2023 德国郁郁不得志的新人小说家Leon,在夏日的森林度假屋中,自卑地爱上了正在研究海因里希·海涅文学批判的phd学生Nadja。
夜幕降临,一场大地的震动,一片悄然蔓延的山火,一对在火焰中等待死亡的爱人,和一个“看了我很久,最终离开”的她。
种种失去的代价,终于唤醒Leon对自己的执念,让他看见身边那些曾没离开他的人。
夜幕降临,大地震颤,飞禽走兽竞相逃离。
人却在其中进退失踞。
Nadja寓言般念出海涅的《阿斯拉人》:每天夜间时分,美丽的苏丹公主在喷水池边走上走下,那里洁白的水花轻溅。
每天夜间时分,年轻的奴隶伫立在喷水池边,那里洁白的水花轻溅;他的脸色一天比一天苍白。
一天夜间,公主近前开口疾言:“我要知道你的名字,你的家乡,你的部族!
”奴隶回答道:“我名叫穆罕默德,也门是我的家乡,那些阿斯拉人是我的部族,一旦相爱,注定消亡。
”This is the quake of love, overture of deaths. 暮色降临,爱意渐浓,天边泛起红色,海底翻出蓝色;谁会在坠入爱河的时刻死去…!
我们相爱,我们束手无策。
电影中提及的音乐:Wallners的In my mind。
呼应湮灭了的浪漫主义,和爱在灾难面前束手无策的处境。
6 ) 惹人厌恶的主角却进行了承上启下的塑造
电影本身的节奏是很经典的东欧式先抑后扬,电影的前一个小时是充满压抑和烦闷的,它用尽气力去塑造了一个烦人的主角,再用最后三十分钟去引爆前面的堆砌,这种手法不能说不好,只能说如果题材不合适,只会让人难以下咽。
莱昂其实以通俗点的语言来评价男主角莱昂的话,我可能只会用犯贱来评论他。
而用精确一点的语言来说的话,莱昂是一个完全的自我中心论者,他在电影中呈现的形象已经不仅仅是不讨喜,他是有点惹人厌恶的人。
他自视甚高,以为自己是个作家就目空一切,实际上电影中有个片段,是出版商念诵莱昂的文稿,就单单两三分钟的时间,莱昂的文稿就凸显出了做作、矫情、文字重复没有意义的状况,你听着他的文稿,甚至难以理解这种作品居然还有出版社愿意和他对接。
但就是这样一个名不副实的身份却带给了他傲慢的底气,他称菲利克斯的作品是难看的垃圾、看见娜迪亚卖冰淇淋就将她和贫贱划等号、认为戴维是救生员就等于文盲,哪怕对方能说出在海洋中发光的藻类有什么习性都不愿转变自己的观点。
当最后莱昂因为出书无能和对于娜迪亚的爱与嫉妒而向娜迪亚和出版商恶语相向的时候,娜迪亚的回击和辱骂让我不由得感到舒爽,一整部电影终于骂他了。
其实莱昂的性格要准确评价的话,可以说是作茧自缚。
他困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像个盲人一样看不到自身以外的更开阔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被自身烦恼折磨,对周边的人或事物冷漠、麻木,爱也渐渐消失、深埋起来,越来越多的是对他人的埋怨、猜忌与侵犯。
而他的“侵犯”则体现在电影中极多的“偷窥”镜头里,菲利克斯、戴维、娜迪亚,莱昂偷窥过每个人和每个组合,他把自己的状态比喻为高等的,以“上帝”视角去审视和判断他人。
就像电影前期,菲利克斯拿出自己的摄影作品,表示自己想用任务的“背面、正面”为组合来凸显大海的主题,但莱昂言辞激烈地抨击了这一构思,在他看来,当相机转到看海人的正面时,他们就不是在看海了,而是会看向相机。
背面代表窥视,正面代表交流,莱昂只想窥视,不想交流,他抱着书写世界的愿望,想拉开距离观察,却常常失焦而目迷。
而更加讽刺的是,莱昂对待“冰淇淋车员工”和“文学博士”两个身份的娜迪亚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最开始自己的文章被批判,莱昂整个人的表达就是“你也配”的轻佻傲慢的态度,而娜迪亚身份凸显后,他的状态是“真的吗?
你真的是博士吗?
你不就是个卖冰淇淋的吗?
”的难以置信甚至有些破防的态度。
在莱昂把小说拿给娜迪亚阅读,得到批判,并最终得知娜迪亚并非只是海滩上的冰淇淋售卖员,而是文学博士时,莱昂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同感跌至了深渊。
批评的意义与重要性,因为批评者的身份发生了质的改变。
在此之外莱昂还悲哀地发现,在这个假期里,看似轻蔑一切却渴望着一切的自己,从未真正了解过自己欲求的这些人与物。
他的自我中心论就这样出现了裂缝。
而除开莱昂“成长”的主线之外,作为副线的菲利克斯和戴维这对同性恋人的故事一直游离于主线外,餐桌上的一个吻、暗示意味的性场景。
甚至令观众以为只不过是主人公爱情线的佐料,却在高潮部分让人倍感意外。
两名同性恋人在山火中殉情的情节呼应了女主角背诵的那首海涅的诗歌:一旦相爱,注定消亡。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则是最后一段,将在太平间的影像文字化的突变,简直是神来一笔,它让电影没有落入到伤感煽情的窠臼里,摆脱掉那些廉价的俗套感。
借出版商朗诵文稿的方式,让电影的副线和主线相连接,再次回到文学创作的话题上,也娓娓道出了莱昂在创作与心态上的成熟转变。
在终于懂得观察与关心身边人的重要性,他将同伴的爱情悲剧转为自己的创作,作为献给亡友的一份礼物。
除此之外,在电影的最后一幕,娜迪亚在海边冲着莱昂咆哮的时候,她毫不犹豫的说出“四号病区”是“绝症病区”。
电影中没有任何对此的刻画,那么换个方向想一下,是否是娜迪亚本身就已经身患绝症了,然后正好又和出版商同病相怜,她借来轮椅可能是为了提前适应自己未来无法行走的状态。
7 ) 短评写不下了
4.5 虽然没有《温蒂妮》和《耶拉》那么好,但很惊喜地看到导演在寻求某种转变,不再那么细致、典雅和精准,开始有了一些随性的空间。
最妙的一点当然就是并没有很明显地拍出“红色天空”,除了一个四人远望的镜头。
观众对红色天空就只是轻轻一瞥,剩下的全都是文学性的想象。
男主因为对新作品质量的担忧与焦虑,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很多身边很多明显的变化。
以为女主是和救生员在晚上做爱吵得他睡不着觉,没想到真正和救生员号好上的是他的男同伴;以为女主每天在旅游景点卖冰淇淋,文化水平低,没想到她竟然在准备读学位,研究方向还是海涅的诗歌;以为书商表现出来的忽视与忧虑主要是因为讨厌自己的作品,没想到更多的是缘于得了肿瘤。
男主的这种创作焦虑,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导演自己的呢?
以为风不会把山火吹到度假屋附近,殊不知但灰烬飘雪的时候,一切为时已晚。
山火不仅会在肉体上吞噬一切,比如烧焦的野猪与一同赴死的同性恋人(他们类似庞贝陷落时共赴黄泉的爱人);还会在精神上对人造成沉重打击,促使不羁的女主在结尾选择离开,让男主获得了巨大的成长。
山火也孕育着新生,让男主将这一切写成了新的小说,书商做肿瘤治疗的时候在外等待并合女主重逢。
喜欢导演对焦虑的“素描”(夜里失眠、白天嗜睡、无法真正放松、一直说要工作却毫无进展、在同伴出现的时候假装自己在工作、对他人一些无心的话都试作对自己的攻击、同伴每天都在放松却被灵感之神眷顾并拍出非常有灵性的摄影作品),看似轻描淡写却四两千斤;喜欢导演一如既往对文学的热爱与关注(很多故事通过角色转述出来,并没有真正地通过镜头来展现;剧本本身也是一个当代寓言故事)。
但除了这些以外,佩措尔德的新风格明显还不够成熟,很多地方说不通,也就缺少了说服力。
例如,男主对女主和爱明显到不了“炽热山火”的程度。
期待他的下一部作品。
8 ) 在写实与诗意之间自由流动的当代寓言
德国导演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与柏林电影节的缘分匪浅,其作品先后多次入围竞赛,不仅将两位缪斯女神——尼娜·霍斯与葆拉·贝尔捧成柏林影后,自己也凭《芭芭拉》一举拿下最佳导演银熊奖。
今年更是凭《红色天空》擒获评审团大奖,距金熊奖仅一步之遥。
作为柏林电影学派的领军人物,佩措尔德此前擅长历史政治题材,从上一部《温蒂尼》开始远离严肃沉重的时代气息,转而将历史传说巧妙嵌入爱情故事里,致力于打造“元素三部曲”。
作为“元素三部曲”的第二部,《红色天空》以“火”为题,与《温蒂尼》类似地将背景设置在当下的欧洲。
故事讲述一个年轻男作家和同伴来到后者父亲的度假小屋避暑,结果发现屋里另有租客,打乱了他完成手稿的计划。
蔓延的山火与创作的焦虑,令他心急如焚,身边的朋友外享受美食、嬉水畅泳,他却心生妒忌,看不清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就在眼前……一女三男、夏日海边、悠闲惬意的环境,像极了法国新浪潮大师侯麦作品的格调,不过佩措尔德却未有探索道德与哲学的野心。
说到底,这并不是一个浪漫的男女爱情故事,导演在度假类型的脉络里,将文学创作、嫉妒、同性关系描写得丝丝入扣。
影片以一个心烦气躁的白人男作家切入叙事,炮制出连串幽默的效果,也具有不少讽刺的意味。
幽默感主要集中在他言行不一的表现:一边宣称要趁度假时间完成创作手稿,另一边却在同伴外出玩乐时无所事事;最好笑的是他竟不知同伴与救生员是同性恋人关系。
剧本不仅将直男的性别固化观念揶揄戏谑一番,而且暴露出作家对身边的人与事毫不关心,完全沉浸在闭门造车的空想之中(他手稿中那些干巴巴的词汇与描写足以证明)。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缺乏观察和生活体验明显是犯了创作大忌。
另一方面,他满脑子的阶级固化意识、目空一切的傲慢心态,也阻碍了他与身边人的沟通交流,甚至无法虚心接受他人的见解与批评,这一点在他遇上女主角后,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他与女主角的爱情也因此卡在了停滞不前的状态里,与其说他是不解风情、不懂接受他人好意,倒不如说是情商方面出了问题。
上述饱含讽刺意味的人物塑造,与我们常见的作家形象大有不同,这不仅仅是导演有意对作家人设的去魅,更带有导演的自省意识,对直男创作者、白人知识分子这些性别与身份标签的自我讽刺。
既然是一部以“火”为题的作品,导演最出色的莫过于将环境灾害的现实话题融入到叙事里。
炎热夏日的森林火灾、动物受害的生态问题未必是影片重点,而以熊熊燃烧的山火来衬托人物的心理情绪却是最令人称赞的一笔。
这场逐渐蔓延逼近的山火好比是主人公内心嫉妒情绪的外化表现:他妒忌同伴与救生员坠入爱河,妒忌同伴的摄影集得到赏识,更妒忌女主角原来是研究文学的博士高材生,妒忌她与出版商一拍即合,内心嫉妒与创作焦虑叠加之下,最终迎来一场悲剧。
继上一部《温蒂尼》的都市神话,佩措尔德再将古罗马庞贝的传说不动声色嵌入到同性情节里,惊艳无比。
这是导演初次涉足同性题材,却处理得如此美妙,这对同性恋人的故事一直游离于主线外,餐桌上的一个吻,以及暗示意味的性场景,甚至令观众以为只不过是主人公爱情线的佐料,却在高潮部分让人倍感意外。
两名同性恋人在山火中殉情的情节呼应了女主角背诵的那首海涅的诗歌:一旦相爱,注定消亡。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最后一段文字影像化的突变,犹如神来一笔,没有落入到伤感煽情的窠臼里,摆脱掉那些廉价的俗套感。
更重要的是,影片再次回到文学创作的话题上,也娓娓道出了男主角在创作与心态上的成熟转变。
主人公在终于懂得观察与关心身边人的重要性,他将同伴的爱情悲剧转为自己的创作,既是献给亡友的一份礼物,也有支持同性弱势群体的现实意义。
而从一个自恋自大、刚愎自用的直男转变为观察细腻的作家,其关键正是有女主角——缪斯的出现,正是女主角的提点,他才从中领悟到创作的关键,从而创作出触动人心的作品。
《红色天空》在写实与诗意之间自由流动,不仅靠类型化的元素(夏日、海滩),还有音乐的妙用,一首旋律迷人的 In My Mind 让观众瞬间神经松弛,更掀起一阵神秘气氛,不知不觉走进了主人公的思绪里。
导演用音乐与核心意象(火)模糊了现实与(主人公)创作之间的界线:天空飘落的灰烬、夜晚发光的海、森林中被烧死的野猪,这些神秘的画面让人浮想联翩,有可能是真实的状况,也可能是主人公的虚构创作。
这部夏日度假类型片轻松跨越了爱情喜剧的藩篱,融合了环保意识与性少数群体的话题,更直抵文学创作的核心,使其流露出难以抗拒的魅力。
9 ) 导筒× 导演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再获大奖的他,正在成为德国电影新的旗帜
德国导演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元素精灵”三部曲第二部《红色天空》在第7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斩获评委会大奖,本片由托马斯·舒伯特、葆拉·贝尔、恩诺·特雷布斯、兰斯顿·伊贝尔、马蒂亚斯·勃兰特主演。
在颁奖礼举行前,导筒directube与3家海外媒体一同圆桌专访了佩措尔德导演,作为德国影坛最具创作活力的导演之一,佩措尔德正在有条不紊地带领德国电影开启新的征途。
“因怀才不遇而时常闹脾气的年轻作家,饱读诗书却含而不露的美丽女人,天真烂漫的摄影学生,性格有趣身材火辣的海边救生员。
Petzold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拍青春的爱火,夏季的海边,写坏的小说,酒足饭饱的日常。
每个人的秉性都带着直白与热烈的一面,像火,而燃烧的森林成为墓园前也曾是乐园。
回望被激情燃尽的青春、等木结成炭,一切故事留在心里,像主题曲的标题,“in my mind”,小说已写好了。
Petzold真是才气斐然。
”
佩措尔德专访正文问:这是你在《温蒂妮》之后打算拍的翻拍片吗?
而新冠疫情发生了,你必须重新计划且重做所有的事情,还是说这就是你在被新冠耽误之后应该做的?
佩措尔德:是的,在《温蒂妮》之后,我想做的是一部根据George Simenon的小说改编的反乌托邦电影。
它是关于一个法西斯政权,关于年轻人和压迫。
而他们失去了他们的现实的生活。
他们杀戮,他们不能再爱。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故事。
这部小说的德语版,我买了版权,非常昂贵,叫《The Snow is Dirty》。
这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
20年来,我一直梦想着将这部小说拍成电影。
在我感染了COVID之后,2020年在巴黎,在柏林电影节的4周之后,葆拉·贝尔也被感染了。
当我们回到德国时,我们说这种像19世纪被称为“法国病”的梅毒,但它与梅毒或类似的东西无关。
因此,我不得不在床上躺了四个星期,我必须说,因为没有人可以告诉你现在发生了什么,因为没有这种感染的经验。
有些人正在死亡。
我在巴黎有联合制片人,他们给了葆拉和我侯麦全部作品的蓝光碟。
所以我躺了4个星期,做发烧的梦,我有恐惧,我还有25部侯麦的电影。
所以我又开始看它们。
我年轻的时候都看过了,大部分都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我25、27岁的时候。
而且它们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这些电影。
但在我的记忆中,我认为它们不再起作用了。
我把第一部电影,也就是《夏天的故事》,通过我床上的DVD播放器放在我漂亮的小屏幕上。
我完全被这部电影迷住了。
因为我记得,我们在德国电影学院有一个教授,学院是我开始的地方,离这个地方非常近。
他说,你必须制作电影,让人们在30年后看到这部电影时,知道我们是如何亲吻、爱、背叛、行走的。
我喜欢这样。
我喜欢做这种事情,拍纪录片。
这是与社会的心态有关的事情。
而这一点我在侯麦的作品中发现。
然后我有这个印象,为什么我们德国没有像法国人或美国人那样的夏季电影。
美国人,他们有夏季电影,法国人也有夏季电影。
他们非常重要,这些类型的电影。
它们非常重要,因为在法国的夏季电影中,在海滩上,各阶层混合在一起,工人、富人和大海。
而年轻人不得不学习一些关于他们自己的东西,关于他们的欲望,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忠诚,关于爱情,以及你能做的一切。
他们在这两个月的夏天学到了东西,他们在法语中称之为“感性教育”,因为后来,当你40岁的时候,你会记得你成年前的最后一个夏天,你会记得它,记得这个女孩、这个男孩、这个场景,这是一些东西,对你的传记和你的心态非常重要。
侯麦的电影,我们这部电影,都是关于这个主题的。
在美国电影中,你有一群年轻人。
我喜欢《彻夜狂欢》这样的电影,我非常喜欢它们。
或者你有车,有四五个人,年轻人,三个女孩,三个男孩。
他们中的一些人真的很愚蠢,有一个是操蛋鬼或类似的东西。
然后发生了车祸,我知道这是一条捷径。
还有,森林里的小木屋,有一个有前任的人,他在年轻时有问题。
但这也是一部关于成年的电影。
因为他们也学到了一些关于……
问:或者像《尖叫》那样的电影。
佩措尔德:是的,比如说《尖叫》。
或者《林中小屋》就是这样的电影,或者《黑色星期五》或者《我唾弃你的坟墓》这样的电影,我们昨天谈到过。
我是这样的电影的大粉丝。
因为它们看起来很相似,但它们是不同的。
因为他们使用了森林、小屋、车祸、前任、电锯这些语法,但他们在讲述另一个故事,关于1933年的年轻人,和1993年的其他年轻人。
问:但是(《红色天空》里的)这些人比这要老得多。
他们带着很多包袱。
佩措尔德:在我的电影中,是的。
但他们已经看过这些电影。
所以,我想说,他们不是17岁,他们现在是25或26岁。
他们已经看过这些电影了。
因此,当他们一开始在森林里时,他们知道有一些预先设定,有一个海滩。
我必须说,现在26、27岁的人都很年轻。
我的孩子们的问题是——我已经60多岁了,而我的孩子们是22岁和26岁。
还有……
问:我27岁了。
佩措尔德:是的,所以他们有这样的问题。
当他们去到别处,他们住在自己的公寓里。
但是当他们回家的时候,他们经常是访客。
当他们回家并播放他们的音乐时,我和我的妻子所听的与他们的音乐相差不大。
所以有一些纽约的东西,或者底特律的音乐,技术流的东西等等,我都非常喜欢,非常大声,他们可以从那些音乐里学习到一些人生问题。
我父母的音乐是丑陋的。
所以两代人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现在这几代人有点混合。
因此,当你25、26岁在小屋里或在海滩附近的小房子里时,你就有点像17岁。
这也是一个问题,他们必须比我更早地成为成年人,因为市场在抢夺他们。
他们必须要工作。
资本主义正在要他们工作,他们想摧毁年轻人。
但另一方面,他们在17岁时停留的时间更长,因为他们是40岁,像我一样被嘻哈音乐打动。
我忘了你这个问题……
问:他们身上有很多包袱。
佩措尔德:是的。
接下来的事情是,我总是在想,当你看到人们在旅途中,他们到达他们的目标,房子。
这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道德的问题:摄像机在哪里?
这总是一个道德的问题:摄像机在外面吗?
它在看他们是如何进去的?
还是摄像机在里面等着他们?
这不是电影的主要主题,但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
这所房子在等着他们。
在这所房子里,有些事情正在发生。
有些事情发生了。
这个房子有复杂性,因为它是一个社会的复杂性,有红酒,有洗衣机。
有来自其他人的痕迹。
但是你知道,这些人在度假,他们想到达无辜的地方,你知道,拖车的广告,大篷车,它总是相同的图片。
当你在电视上看到它时,有一个孤独的海滩,你可以开车直接到水边,把你的椅子放在外面,在上面做烧烤。
这是你的,世界是你的。
这是人们度假的梦想。
但现实是你必须处理好这个世界和这个复杂的问题。
因此,这是,例如,决定在复杂的环境中与相机在一起,等待他们,他们认为他们正在期待着纯真。
问:但人们认为他们想要这样,但他们并不真的想要,因为他们不喜欢孤独。
佩措尔德:是的,这只是图片。
例如,在德国的折扣店超市里,那些便宜的超市,他们总是有旅行社。
比如说,我们住在柏林的同一个地方。
有时我们在一家名为Penny markets的折扣店附近相遇。
它对我来说没有任何问题。
但当你要在收银台付款时,你会看到他们自己的旅行社的广告,总是很孤独。
一棵孤独的树和一个孤独的海滩,或者一个没有人的游泳池。
这个游泳池的名字是什么?
是无边泳池?
非常、非常、非常贫穷的人,他们正在购买他们的牛奶和黄油,他们看到这些照片。
这不仅仅是这个广告认为有人可以买这个航程或这个旅程的票,它只是要告诉人们有一个无辜的世界,你可以孤独,但你不能孤独。
问:你似乎对发展托马斯·舒伯特演的莱昂这个角色特别感兴趣。
而他总是有点搁置叙述的意思。
有人说让我们去海边,他总是说:不,我不去。
所以我们也没有看到它,当然,因为我们和他呆在一起。
所以我只是想知道他是否一直有那种作家的障碍。
所以,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如何发展他的,你如何将他与自己关联,并拥抱了人物模板。
问(另一位补充):我可以对这个问题补充一下吗?
因为我有一个男性朋友和我一起看这部电影,他说他完全和托马斯扮演的角色有关,因为他看到自己有点暴躁,有时很不开心,以工作为借口。
你在现实中经常看到这种类型的人,特别是男人吗?
问:我完全和他有关。
那就是我!
佩措尔德:是的。
因为这个角色里面有很多我自己的东西。
一个小时前,我记起2003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幕,我拍了电影《沃尔夫斯堡》。
它被邀请到西班牙的一个电影节,在马德里。
在这个电影节上,有一个与施隆多夫和其他许多导演的晚宴。
那天晚上,来自柏林的DJ Hell正在举办一个有一万人参加的派对。
是的,我们都被邀请了,凌晨3点就开始了。
那是11点,四个小时睡觉时间。
因为我太累了,但我有点像托马斯·舒伯特,像莱昂一样,我说:"我不能加入你们,因为我得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没有说,比如,我太累了。
我说,我必须工作,因为我想给他们一个不好的感觉。
我想给他们的感觉是:你可以开派对,好的,但我必须工作。
第二天,我在普拉多博物馆。
下午,我回来了,让他们被派对完全摧毁,因为它一直到早上六点。
我对自己说,现在不要问他们聚会的情况如何,我想彻底摧毁他们。
他们也想摧毁我,因为他们的身体里有这个奇妙的派对,音乐在身体里。
他们还问:你的工作怎么样?
我说,这很奇妙。
我已经写了20页,像这样一棵树。
他们继续说,我成功毁了他们。
我告诉演员们这个故事,因为它与艺术家有关,与艺术家的男性主体性有关,不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不看到一些东西,扮演一个作家。
所以我知道这些人物身上发生了什么。
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我知道我们演员中的每个人,也知道摄像机后面的人,他们知道关于这些的一切,关于那些站在墙上聚会的人。
而其他所有人都会跳舞,他们也会对他们开玩笑。
但问题是,在写这个的过程中,他让我咄咄逼人。
因为我对自己很有攻击性,因此我需要幽默感。
因为当我可以笑自己的时候,就像你10秒钟前笑自己一样。
他很有同情心,因为他是个白痴,而白痴是有同情心的。
而且他知道他是个白痴。
他知道。
但他不能从他的身体里出来。
问:但他也不是完全的白痴。
我想念那个场景,那个救人的游泳者正在讲那段无休止的谈话。
而且他看起来越来越烦躁。
我支持他,闭嘴吧。
我是说,他是一个非常值得同情的人物。
这让我觉得他可能是你。
佩措尔德:如你所知,葆拉·贝尔这个角色,她爱上了他。
因为她喜欢戏弄他。
在救援的游泳者讲述他的长篇故事时,关于那个让他成为同性恋的阿拉伯人,他是一个很好的讲故事者,而作家不是一个好的说书人,因此他也很嫉妒。
但是那个女孩,她总是在看他,她给人一种新的感觉。
你喜欢看人的形状被打破,你喜欢它。
我喜欢这个时刻,因为它不在剧本里,当编辑在那里,他走进厨房,说我很抱歉,我邀请了我的编辑,现在他正在看这个另一个人的船舶照片。
然后她说,你现在还有几天?
他明天就要走了。
所以她在看他。
在这一刻,她知道,他失去了一切,他将失去他的剧本,没有第二本书了。
然后她对他笑了,而他也想笑。
这就是救赎的时刻。
这是他可以放开自我的时刻,救援的游泳者开着红色卡车过来,一切都消失了。
但是这一刻,你可以看到这可能是一个解脱的时刻。
哦,这本书狗屎。
这是一个女孩,她爱我不是作为一个作家,她爱我是作为一个人。
我可以放松。
在这发生的前一秒,狗屎救援的游泳者也随之而来。
问:我也在想,因为你用德国浪漫主义的元素作为逻辑矩阵。
这部也是在那部《温蒂妮》的三部曲中。
所以在我看来,雷格纳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当然,也被称为Roter Himmel。
我只是想知道在电影和德国浪漫主义者之间的动机方面是否也有联系。
佩措尔德:对我来说,我必须说,我不是一个如此浪漫的人。
在我的生活中,因为我喜欢电影,所以我在电影中看到了许多浪漫的东西。
但是,对我来说,雷格纳是一个逃离浪漫的房间。
他开的是关于浪漫的玩笑。
他是一个拿浪漫开玩笑的人,因为在浪漫中,也有虚荣心。
它总是浪漫的艺术家的虚荣心。
在这之外,我们的社会,他们在寻找鲜花,寻找真正的爱情,女人总是有吸引力的,而且离得很远。
而雷格纳对此开了个玩笑。
这一点我有点喜欢雷格纳。
这些是歌曲,人们在19世纪喜欢雷格纳,因为他们可以把他的诗当作歌曲。
这么多德国人都知道。
直到1933年,他们知道这么多关于雷格纳的事情,法西斯分子摧毁了他们的记忆。
因此,他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而《红色天空》,它是它是这样的,这个剧本的原标题是 "快乐的人",德国的脱口秀。
我不能使用它,因为有人和他的律师说,你不能使用它,因为我在2004年做了同样标题,你可以在亚马逊上买到它。
所以我不能使用它。
但是 "快乐的人",它不是很有创意。
但我对这个人有点生气,因为他想赚5000欧元,而我不喜欢这样。
然后有一部1967年的电影,一部由鲁道夫·托米拍摄的德国电影,名字叫《红日》。
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夏天,湖边,同龄的年轻人试图在祖马所说的压迫和后法西斯结构的德国世界中,做一个爱和欲望的夏天。
这部电影在我年轻时的生活中非常重要。
而且有一个唱片机,我在电影中也有同样的唱片机。
对我来说,《红色天空》与《红日》有一些关系。
还有一些与对大天空的渴望有关,热谈,一些能打开你的思想的东西。
而在另一方面,你有这个作家是封闭的。
因此,打开你的心扉,也打开你的心扉,让你看到围绕在我们身边的气候灾难。
但这不是电影的主题,它是存在的,但它不是主题。
所以这是我们的想法。
问:这就是它成为“元素三部曲”的第二部分的意义所在?
因为你有一个人,然后得到了灵感。
这就是成为第二部分的要点,要找到元素。
佩佐尔德:是的,这是对的。
这个元素。
首先,这是一种夏天的感觉,我们必须做一些事情来反对这个新教的世界,一切都被禁止,所以,然后我记得天空,红色,火的元素,热。
一切都有两个含义。
热是指从身体里出来的东西,《体热》是80年代的一部神奇的电影。
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这种体热是夏天。
皮肤出汗,空气中的性,类似这样的东西。
另一方面,这也是气候灾难的热。
这个时代一切有两面性,你有心中的火和森林中的火,都是对应的,但不是我在剧本内做的对应。
问:说到隐喻,也正如你提到的,事情总是双面的,我一直试图解析火的象征。
它是否更像是一种保护,因为它把这个小屋里的年轻人与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但同时它又是破坏性的。
火摧毁了他们中的两个人。
我想知道你更强调哪种意义,或者它们只是同样的表达?
佩措尔德:是这样的。
他们住在森林里的房子,我们完全是自己建造的,它是如此的符合幻想,每个人都问我,我可以在那里度假吗?
不,它不存在了。
那是一个废墟,屋顶是用颜色做的。
所以,我们也要画草,这用生态环保的颜料刷的。
还有,烧毁森林的灰下的雪,也是完全生态的。
我们必须要求工厂,它正在制造那个火,但是你可以看到,当雪花在下的时候,你知道大自然的爱。
来吧! 来吧!
来吧!
非常好。
但是我们建造了这所房子,还有这套预制构件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建造的。
它被一堵树墙所包围,只有一个洞,就像《猫和老鼠》中的老鼠来的地方,通过那里你可以到达海滩。
所以他们想自己呆着,就像20年前建造这所房子的那个家庭。
是的。
所以他们想自己一个人呆着。
这是德国病。
因为美国人,他们喜欢看街道,他们有露台和门廊,可以看到街道。
德国人则喜欢自己的花园。
所以街道是敌人。
因为他们想自己呆着,火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
因为火正在摧毁墙壁。
它为一些事情打开了你的思想,但打开你的思想也是非常危险的。
这就是建筑的一点意义。
文 / 蓝詹
10 ) 95后国际影后,继续让演技绽放
德国导演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元素精灵”三部曲第二部《红色天空》在第7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斩获评委会大奖,本片由托马斯·舒伯特、葆拉·贝尔、恩诺·特雷布斯、兰斯顿·伊贝尔、马蒂亚斯·勃兰特主演。
在颁奖礼举行前,导筒directube与海外媒体一同圆桌专访了《红色天空》主演葆拉·贝尔,作为老搭档导演佩措尔德元素精灵系列的核心演员,柏林影后贝尔正在最正确的道路上绽放演技。
贝尔专访正文问:我想这是你第三次与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合作了?
这一次的情况如何?
因为当然,第一次是试图从工作过程中了解对方的情况。
但我认为现在你们更多的是……“来吧,我有一个剧本给你,开拍!
”你们之间的工作应该更容易了?
葆拉·贝尔:是的,这是完全正确的。
我认为,来到电影或电影片场,大多数时候,你就是需要很多时间来了解对方。
所以了解你的导演、你的同事、团队,这需要很多时间。
为了有安全感,为了作为一个演员更好地工作,要打开自己,能够信任他们,并且要感到,“好吧,我觉得很安全。
我们开始吧”,这需要很长的时间,通常。
然后到了拍摄的第20天,你会想,“好吧,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
因为现在我认识每个人,我知道在片场如何工作。
”现在第三次与克里斯蒂安合作,对我来说,这真是太好了,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两次精彩的拍片经历,然后他很早就让我参与到这个故事(《红色天空》)当中。
一开始,他只是告诉我这个故事,然后说,“好吧,我有一个想法。
因为在疫情之后,我想要一些轻松的东西。
我真的想拍一部非常、非常轻松和有爱的夏季电影”。
所以第一次,他只是告诉我他的想法。
这已经不同于从一个你不认识的人那里得到一个剧本,然后说:“好吧,让我看看,这就是一个剧本。
我不知道该把它放在哪里,会是什么样的风格。
”我是通过克里斯蒂安自己来了解这个故事的。
当有人向你介绍故事时,而不是“读它,然后决定”,这是很不同的。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投入,真的感觉是一起工作,而不是为某人工作或创造一个画面。
这真的很有趣,感觉就像一个电影家庭,你在一起创造电影,而不是像 “我是你的女演员,告诉我怎么做。
”所以,这也许就像现在看起来的电影氛围一样自由。
问:他有没有让你看侯麦的电影?
因为他在疫情期间重温了侯麦的电影。
葆拉·贝尔:我们都得到了作为礼物的蓝光DVD,所以后来他打电话给我说:“我看了侯麦的这部电影”。
所以我们都看了,我们进入了这种讨论电影的氛围中。
在疫情期间,我们有这么多时间,得了新冠你很头晕,然后就飘到这些来自另一个时代的夏季电影中。
这真的很有启发性。
我们觉得:我们需要这种氛围的回归。
问:佩措尔德盛赞过你。
那么你还记得你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吗?
你们之间的这种特殊联系是什么?
葆拉·贝尔: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最近刚去世的一位很了不起的选角导演的办公室。
克里斯蒂安认真在做他的选角程序。
他不喜欢把人安排来,准备场景,然后测试这些人。
他更像是,“好,我想了解你。
让我们谈谈你可以扮演的角色或你的工作”。
他知道人们的工作是有启发性的。
所以他真的只是友好,而不是那么强地在测试。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只是不停地在谈论所有事情。
然后有一刻,选角导演说,“好吧,也许你想开始谈论电影了。
”然后克里斯蒂安告诉我电影的情况,我们谈论我的角色,玛丽。
然后,在所有这些之后,他就说,“好吧,我希望你能扮演这个角色。
我会把剧本发给你,你就读一下,然后让我知道你对它的看法。
”(我们的合作)真的就那么开始的。
所以,当时真的很平静,不像那种很兴奋的,“天啊,某个大人物给我打电话,我要去准备我的角色,希望我得到这份工作!
”它真的更像是一个邀请,让我们了解对方,然后决定对方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合作对象,真的就看你们是不是在同一水平线上。
问:你和他在一起是否有一些以前和其他导演没有的感觉?
我的意思是,因为你是一个非常希望有时间来准备你的角色的人。
你没有太多的电影或太多的项目在其他导演身上?
所以你需要有一个你信任的人吗?
他和其他导演有什么不同?
因为你选择和他一起做电影,做梦,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对你很重要的导演?
葆拉·贝尔:是的,当然。
实际上就像你说的,对我来说,信任在表演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有更多的信任或信心,或者你觉得有人陪伴,工作就会变得更容易,因为我认为演戏是一件事,但在电影片场,和在电影片场演戏是完全不同的事。
克里斯蒂安真的很棒,创造了一个如此独特的氛围。
我从来没有在这种早上有这么多时间排练的条件下工作过,就只有所有参与演出的人。
你没有处在有压力的情况,人们在等待,看着我们,“好吧,我们到底要不要开灯?
”我只知道克里斯蒂安是这样工作的,这使得它真的很特别,很容易平静下来,专注于要做的事情和场景。
这样的工作很有趣,而不是像“我有10分钟,让它发生吧,我们就那么去做吧。
”和他们一起工作很有趣。
问:这是你正在寻找的那种项目吗?
当你选择一部电影时,你在寻找一些特定的东西,还是?
葆拉·贝尔:我总是从剧本开始,看电影的主题,看角色。
对我这个演员来说,我必须找到对我来说很有趣的东西,因为我总是……我的工作理念是,如果有对我有启迪的东西,我可以把这个启迪给电影。
如果从一开始我就想,“那是角色,但现在不是我要的主题”,我认为这种想法会继续下去,然后电影也会失败。
所以我总是由我的心来决定,什么东西触动了我,然后我会找到力量去创造一个角色。
但当然,就像周围的环境与剧本或角色本身一样重要,与克里斯蒂安的第三次合作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这件事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你有一个好的角色,我还会和你合作。
但是,我还是经常对克里斯蒂安说:不是说我们做了三部电影,所以让我们再做八部吧。
这真的很像,如果你有一个新的想法或新的剧本,我很愿意读它。
但是,我们必须找到方法……问:看它是否有效。
葆拉·贝尔:是的,没错。
要看你们是否又是匹配的。
因为我认为最悲哀的事情是意识到我们有过这么好的经历,然后突然,我们被期望击中,我们对对方感到失望。
对我来说,这对找到项目的关联感总是很重要的。
问:但是,当然,可能你还是要参加三部曲的第三部分。
所以我们期待你会出现在里面?
问:是,我们正在谈论的三部曲……佩措尔德(路过圆桌,对大家打招呼): 这里一切OK吗?
(众人笑,佩措尔德离开了。
)葆拉·贝尔:我们昨天在播客中谈到了这个问题,因为克里斯蒂安被问到:你的三部曲的第三部分是什么?
他就说:“嗯,我上一个三部曲有四部电影,我现在的三部曲有两部电影。
”问:但你正在制作一部。
葆拉·贝尔:是的,但我不确定它是否是三部曲的一部分。
问:在上一部电影《温蒂妮》中,那是一个浪漫的故事,主要是你和Franz Rogowski在对戏。
这一次,情感状态更加复杂,你基本上是与其他三个演员互动。
我想问的是,你如何传达这种复杂性?
处理这个问题是否比前一次更有挑战性?
葆拉·贝尔:嗯,这一次,我们真的有一个很奢侈的条件,我们只在这个房子和海滩上拍摄。
房子是在柏林,海滩是在波罗的海。
所以我们可以按时间顺序进行拍摄。
故事之间没有那么多的跳跃性。
这总是很有帮助,你盯着已经发生的事情,以及将要发生的事情,让你有能量流动。
你通读剧本,你通过剧本发挥,所以这帮助很大。
我不会说处理更多角色之间的关系比处理一个角色的关系更难。
有时只有一个人的时候甚至更复杂,因为那时真的就只有一个人。
而如果有三个或四个人参与,它总是动态的,也是在创造一个场景。
所以,我不会说它更难。
它只是非常不同。
问:你最喜欢的冰淇淋口味是什么?
葆拉·贝尔:我不知道。
取决于冰淇淋店,我想。
问:还有一个关于你的角色的问题是,她是一个文学博士生,那你在进入这个角色之前,有没有准备读一些诗歌,做一些文学方面的准备?
葆拉·贝尔:是的,我在想,对我来说,我的角色有一份工作,这有点新鲜。
我刚刚开始接触有工作的角色。
当然,我在想,当你有了学士、硕士,然后开始在博士项目上工作,关于海涅,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我必须要知道他在写什么,为什么。
那么为什么她这么喜欢这种文学,尤其对他的风格这么感兴趣。
因此,当然,我在拍摄前读了很多海涅的作品,进入了这样的氛围:这个主题是什么样子的?
他在处理什么问题?
也许现在对她来说什么是重要的?
但另一方面,她并不是真的在谈论自己写的论文。
所以她不是这样的人,“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顺便说一句,我正在写我的毕业论文,关于这个题目。
” 她更像是,“我在冰淇淋店工作,我在做这个,我在做那个,如果你想吃点东西的话,我在准备一顿饭。
”所以她在某种程度上真的很务实,真的很简单。
多了解她一点是很重要的,但另一方面,我认为她的行为方式比她的工作更能告诉你她的性格。
海因里希·海涅问:因为她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所以你很难进入吗?
还是你必须建立一些东西?
因为在屏幕上,你和她融为一体,你喜欢深入到你所诠释的角色中去,这和她的神秘感有关吗?
葆拉·贝尔:是这样的,在《过境》的时候我得以了解克里斯蒂安的神秘女性角色,我有点挣扎着去了解玛丽的内在秘密,因为她突然出现在那里,然后她又离开了,你不确定你是否已经看到了她,是真的她还是假的。
这个角色甚至更不明朗,我当时在做这种准备,我觉得玛丽在某种程度上就像,“好吧,我必须这样做。
不,也许这不起作用,我必须朝这个方向走。
”然后,我有点习惯于这个角色,她并不真正符合剧本的通常情节结构,她其实不处在我们习惯的结构中。
实际上,纳迪娅(贝尔在《红色天空》中的角色)也是如此,她并不是个女配角。
你不可能真正了解她,也不可能得到特权评价她说:“哦,她就是那样的。
”对我来说,这更像是一种能量的氛围,一种气氛,什么是莱昂(托马斯·舒伯特饰)不能处理的问题?
或者他在寻找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她能成为什么?
我和克里斯蒂安谈了很多,参考他对这个角色的想法。
当然,与我的其他同事的互动对我创造这个角色帮助很大,她是如此在自己的世界里,但又如此有存在感,可以对她的伙伴作出反应。
问:你以前和他们合作过吗,其他演员?
葆拉·贝尔:是的,我和恩诺(特雷布斯)一起工作过,在我的第一部电影《波尔日记》中,当时我14岁。
那时候他演我的表哥。
我们也在拍摄《温蒂妮》的现场见过。
还有……托马斯·舒伯特,我们在《幽暗山谷》中也曾经是一对夫妻。
那是我们18、19岁的时候。
一开始真的很有趣,当我们在朗读排练时相遇,因为我们坐在一张桌子上,我当时想,这太奇怪了。
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从十几岁起就认识对方。
所以那是非常非常有趣的,我想在某种程度上,它帮助我们彼此之间如此放松,因为如果你知道对方……我和恩诺不是从14岁开始的朋友,当然,不是说我们从相遇的那时起就是最好的朋友了。
但是我们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对方,我认为这会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你们的关系,当你在14岁或16岁时就认识一个人,你们更像学校的朋友,更多地出去玩,你们做不同的事情,你们不谈论,我不知道,政治,或其他。
所以它更像是,“你怎么样?
”这是另一种氛围,就像其他时代的朋友。
我认为与托马斯和恩诺一起,这有助于从一开始就创造一个非常、非常轻松的氛围,只是因为我们从小就认识对方。
问:如果我们说到放松,我很惊讶,你的角色没有任何大惊小怪,她从救生员转移到了男孩身上。
她先是一个情人,然后转向男孩那里,所以你很容易就接受了你在人物之间移动的方式……葆拉·贝尔:嗯,这是我的角色,克里斯蒂安实际上创造了她这样的角色。
所以,我很喜欢她,她不喜欢“什么是爱”或者“恋爱关系是什么样子的”这种经典想法,而是更喜欢:在当下的这个时刻,我们的联系是什么?
我认为那个房子里的夏天,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在人生阶段之间,所以他们都在为下一步做准备,他们的个人发展是想要文凭,写第二本书,准备上艺术学校……所以他们都在准备下一步。
我认为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不在家里,而是在一个不是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家的房子里。
这就像一个自由区,一切都有可能,而且与家里不同。
所以我认为在这些时候,特别是当你在放暑假的时候,这也是克里斯蒂安想做的,一部夏季电影,因为在这段时间你会离开家,离开所谓的一些结构,你可以发现新的结构。
它更容易……比如说,“我现在恋爱了”,以及“事实上,我没有听说他和别人有染,但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很好。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这一点,他们不是彼此的什么唯一。
问:你在片场拍摄的印象最深的一幕是什么?
有这样一幕吗?
印象最深的一场,或者是让你最感动的一场?
葆拉·贝尔:嗯,拍摄都不太一样……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如,灰烬从天空掉下来的场景。
如果你在片场做,那真的是技术性的,有人创造了灰烬,“这太多了”,“这还不够”。
所以这真的让你无法专注于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会想“现在是正确的时间吗?
哦,不合适,我们必须等待。
好的。
现在不行,我们太晚了。
”因此,这真的是在创造场景,与观看它们不同。
我不知道,我只是非常享受看电影的过程,因为我认为我们的剪辑,BettinaBöhler,她做了如此出色的工作。
在拍摄电影时,我认为某些场景很有趣,或者我真的在欣赏托马斯的表演。
但另一方面,我不确定这是否只是我当下的观点,因为我在这个泡沫中,或者它是否会为我留下。
而现在看到电影,我会想,Bettina创造了这个,这个时机,它可能是有趣的。
我只是非常享受看这部电影。
问:你提到当你与导演合作时,有被期望打击的风险。
而你作为一个女演员,从你开始受到赞誉的时候就面临着这种危机,或多或少。
从观众那里得到这些期望是否很困难?
葆拉·贝尔:我会说……我想每个人都有一种倾向,把事情归类来理解它或使它更容易理解。
就像,“如果它适合你,那么我就知道它是什么。
”我想你真的能感觉到它,人们把你放在哪个位置。
但这是一件事,然后我认为下一件事是接受这一点,并且要像“是的,我知道,我适合这个。
我必须实现这一点。
”也许这个想法帮助了我,因为我开始得如此之早,以至于我还没有达到“好吧,我完成了学业。
现在我决定我想接受这种教育,成为一名演员。
然后我希望能成为一名影视演员。
”因此,我进入演艺界是真的是因为儿时对表演的喜爱,它开始得非常早。
然后,突然,我的第一部电影来了,但这对我来说更像是一次冒险。
我当时想,“好吧,现在我想成为一名演员,我喜欢表演。
我已经在舞台上了。
”而现在我在做一部电影。
所以它更像是,“好吧,我想可能这将是有趣的。
”然后我必须完成学业。
所以我的重点并不在建立一番事业上。
我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我想如果只要我喜欢它,我就很高兴去做。
但是如果人们给我一个奖项,是他们来决定给我这个奖项。
他们让我扮演一个角色,是他们来决定让我扮演这个角色。
所以他们更多地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但我不是。
当然,人们会把事情投射到我身上,但我不能阻止他们。
所以……
问:但你不觉得有压力?
葆拉·贝尔:没有。
我知道它就在那里。
但是,我知道也许你对我有所期待,但那是你的事。
问:你提到了火。
那么,你是否参与了对抗气候变化之类的战斗?
葆拉·贝尔:我认为关注政治的那面很难……我认为这是两项工作,就像关心政治……气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对我来说,这只是……我和我的工作是搭上的。
问:有没有你向往成为的男演员或女演员?
葆拉·贝尔:没有。
我的意思是,我真的受到某些作品的启发。
但是……问:能举个例子吗?
葆拉·贝尔:例如,我在电影院里看到的最近一部真正让我大吃一惊的电影是《悲情三角》。
对我来说,往往是整个作品一起(给我冲击),因为我非常知道电影是如何制作的,我认为看电影是不同的,所以我不喜欢表示“这是我最喜欢的演员或女演员。
”但比如,我不喜欢某部作品和某部电影,我会想,“我知道电影是如何制作的,有时最后并没有把效果体现出来。
”例如,我真的很佩服梅丽尔·斯特里普。
但我认为大多数时候,是看整个作品,我受到启发的不仅是演技,还有背后的个性,或者他们如何决定接受一个角色,他们如何创造,如何做他们的工作,或者他们如何谈论电影。
这真的是整个……所以是的,梅丽尔·斯特里普,这些她都有。
问:弗朗索瓦·欧容有没有再找你做一个新的项目?
因为法国是那么好,对他和你来说,因为它给了你一个国际面孔。
我在想,我们要多久才能再见到你们两个一起工作,但自从你开始和克里斯蒂安合作以来,从来没有停止过。
葆拉·贝尔:是的,但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我不会阻止任何人。
如果有人有兴趣再次与我合作,我认为这很好。
但是没有,到目前为止,弗朗索瓦没有给我第二个作品的角色。
问:但你知道那部电影(《弗兰兹》),对他和你都非常重要。
葆拉·贝尔:是的,是的。
问:那好莱坞呢?
葆拉·贝尔:这是个好问题。
我的意思是,我认为作为一个演员,你不可能真正计划你的职业生涯,你总是可以遇到新的人,并问自己“好吧,我实际上对什么感兴趣?
我对表演英语或法语感兴趣吗?
或者我喜欢什么样的电影,以及我喜欢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对我来说,这更像是了解我想在什么领域工作。
然后,我可以看看是否能联系人,或者我可以准备我的语言技能。
但我认为这不是那么容易说,“我很想和他们一起工作。
”我必须等待匹配的角色。
所以我想……五年前我绝不会想到会像这样坐在这里,它是怎么来的就怎么来。
所以……
问:我相信你在漫威的作品中会很出色。
你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葆拉·贝尔:是的,当然。
我想这绝对会与我目前所经历的不同。
例如,在克里斯蒂安的拍摄现场,这就像德国的文艺电影,然后去到那里,我想真的会是另一个世界。
问:所以对你来说,故事和剧本比和谁工作更重要,比如导演,比国家和该国的电影工业更重要?
葆拉·贝尔:不是更重要,但对我来说,一个名字并不是通往好的作品的门票。
所以,只是因为有的导演有非常好的电影,大名鼎鼎,这并不能帮助演员有一个好的拍摄经验或一个好的角色。
当然,我的意思是,我对与有才华和非常有趣的导演合作非常感兴趣,但也必须有正确的角色。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总是用心选择我的角色,如果我觉得与它有联系或有兴趣,因为我认为只有你的心充满了它,你才能真正的好。
如果你内心有一些东西,就像“是的,我想讲这个故事”,就更容易激励自己去做。
所以,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选择。
你有兴趣吗?
因为如果,比如说,人物非常有趣,但你对剧本没感觉,对这个有问题,或者不理解,那么也许我不会做它。
有很多东西可以创造出一个我觉得舒服的工作状态。
问:你能举个例子吗?
你不必提及名字,但你对哪种作品说过不?
葆拉·贝尔: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我觉得我不理解我的角色或角色所处的位置。
我的意思是,很多人都在说,很多女性角色仍然……当然,你可以在其中创造一些东西,但也许它没什么……比如要女性角色为男性角色服务的那种。
当然,你可以演这种角色,但这不是真正的乐趣,也不是真正的新东西。
我不知道用英语怎么说……就像一种锻炼,或要学习或发现的新东西,而我喜欢在每个角色中寻找新的冒险。
有时你被要求的角色与你已经演过的东西非常相似,我喜欢演某个角色,但是我没有必要做第二次。
或者,有一些剧本之外的已知的东西,或者其他……很多因素都可以导致这个方向。
问:你会说你和克里斯蒂安的这次的工作经验是不同的吗?
从我的角度来看,《红色天空》比你以前和他一起拍的作品更现实一些。
你同意吗?
它是不同的吗?
葆拉·贝尔:绝对是。
《温蒂妮》有对童话的巨大依赖,对我来说,有一个巨大的创作方面,创造她时我问自己,当她说她来自于水,当她说她需要回到水的时候,她来自于哪里?
这个水底世界是什么?
她是一个美人鱼吗?
她是什么,一种幽灵?
一种能量?
水下的其他动态是怎样的?
所以这真的很好玩,真的很幻想:她从哪里来,对她来说在地球上是怎样的?
这真的是一个幻想的世界。
现在对于《红色天空》,我认为因为每个演员都来自另一种风格,也许。
所以我认为这使得它真的很真实,不人工,所以这真的很奇怪。
托马斯也是如此,他是如此厉害的喜剧演员,我认为为克里斯蒂安的工作做出了这样一种新的流派。
正如你所说的,它更真实,有一点飞扬。
问:更即兴?
葆拉·贝尔:是的,也许,发自内心的那种。
文 / 蓝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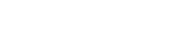











































































































一个好作家的养成:写别人的生活+吃蘸人血的馒头
女的长得有点像瑞秋。那个胖子又怂又闷骚,又刻板又无趣,丝毫都没有作家敏锐的洞察力,真不知道女的怎么就看上他了?两星半
C/ 一度艰涩到怀疑不是佩措尔德,像是在执行一种苦修式的创作榨取,将叙述的语气削平,极度迟缓地达成情境的构建。但还是能从爽利的运动线条与恍如史前时代般的夜色中识别出极其克制的元素暗流,这种暗流重新将观众引回《温蒂妮》中的物候感知。但故事最终似乎仍然将自身归结为一种太过简易的寓言,使得先前的诸多延宕显得无效。
4.5 火(紅)元素之力:引擎「死火」、森林大火、面對誘惑的慾火、男性作家的創作焦慮、Paula Beer的紅裙、相擁纏綿的激情、永不熄滅的愛火。亦步亦趨的山火既作為早已經由廣播宣告的自然災難的外在表徵,同時也成為迫使人物間關係的隱瞞、不安、羞愧和落魄逐漸清晰,讓心房緊閉的自我、僵硬拘謹的肉身不得不向著無常世界敞開,美麗而危險的末日想像。Petzold這次無需配合北歐神話也能找到潛藏於日常情境之下的神秘性,世界的真相,那是一對坦然赴死的同性戀人、跨過烈焰,黑夜中磷光閃閃的大海、恐懼且迷人的紅色天空、Heine的曼妙詩句。
变gay喷雾和林火意像(但没用好)两星
本做足准备接受《温蒂妮》一样的洗礼,啧,就败兴而归,神奇的东西在哪里?男主人物准确却非常讨人厌,女主出场前的几场戏设计的非常有魅力,但这个剖析创作历程的命题着实意思不大。另外,主题曲Wallners《in my mind》好好听~已收藏。
“你注意到周遭世界的任何事情了吗?你什么都没发现。”被这句话狠狠的刺到。相比《温蒂尼》更具文学性和幽默感,#HKIFF 47最喜欢的之一,刷了两遍。“火精灵去海边但不游泳”这个设定越想越好笑。
傲慢自负的男主真有点讨厌,最后竟然还落点在朋友的死亡让他写出了本好书。。。仅仅是写出了本书。。。
别救了
看的时候觉得男主很讨厌,又猛得发觉这就是我们
年度场景:Nadja 拿着透明杯子从小屋走出,置身于悬浮的山火灰烬中,身后是一片蕨,她穿红色。
#HKIFF 映前Cinefan的戈达尔广告很好归纳了这部电影:一个词,关于情感。Petzold把四个青年之间的情感拍得如此微妙,火的隐喻推进并吞噬他们。电影相比《温蒂妮》要轻盈得多,甚至称得上幽默,但丝毫未减情感的浓度。文学性很强,海涅的诗是很好的映射:好的电影(作为再现的一种)也是本身在震动的。
男主写的确实不太行,还爱自我感动(不过貌似我身边的男生们也这样… ) 而且卖冰淇淋怎么了? ??之后还给女主安排一个博士学位才让男主从卖冰淇淋看不懂转到只是自己不行… 一男一女就一定会相爱吗? 女主喜欢男主什么我真的不太懂。以及好友的死让直男癌成长也太惨了… (看到评论区 同志亦凡人表示对此无法共鸣)而且对于男主这种毫无天赋的人来说真正的写作进步还需要大量的阅读和写作练习吧,不是啊 我的好朋友在山火中死了,死前还握着爱人的手。我悟了 会写了 有素材了… 靠 真的想骂脏话了 对这种男文青。 现实里好像也挺多的 油腻自负敏感多疑 自己也毫无才华 处处pua女性 还沉溺于自己的作品中觉得大家都不懂他
有了佩措尔德,柏林电影节就有了锚。230219
男主真的太巨婴了,所有角色都比他讨好……但所有角色都是为了服务男主角的成长……有情的Felix&Devid,有义的Nadja,有学识的Helmut……偶有出神的时刻,山火普天卷来,席卷大地;被火灼烧死去的野兔;深夜在发光的大海……但给我观感还是抵不过一个愚蠢的男主……(但他的焦虑&自我防御还是能同情的,sigh)
【9】不知道为什么,没被电影里的任何情感打动,而是看到Leon看到两俱尸体无动于衷,才潸然泪下。因为那就是过度偏执,自我,敏感,脆弱,寂寞本身。有些电影在拍诗,而佩措尔德的电影已经进化到是诗的本身了。剧情化作流动的时间轴,捕捉一切文本,镜头推进,移动,定格所有美丽,包裹成他自己的故事。山火欲来的暗流涌动,游走抽离于文本(梦境)与现实之间,引用Kleist的诗幻化为火之元素,当他们相爱的时候,他们就会死亡。真真假假,文本与现实,落脚点都可以是In my mind。
什么勾八。
当你以为全世界都针对你时,试问一下自己,是不是过于男本位思考这个世界了?Who asks you?
开始以为红天空的设计和冯提尔的《忧郁症》一个思路 但到头来完全不一样 这不是个神秘形象 更像是红色东德的历史幽灵 它和男主的的头发一样成为症状 困扰思维导致障目 看不见周遭发生的应急事件 这种敏感和紊乱既让笨拙的男主只能退到观看而非参与的位置 而且欲望过剩只能启动超越快乐的原则 因此必然成为和谐环境中的破坏者 他的理念中心位置 也随着女主经历的揭破而一文不值 这就是俱乐部三明治碰上千熬百煮的牛肉汤 充满了各种互文 所谓的爱不过是妄想的占有欲 而他能够制造的 也不过是文本的垃圾 能留的下来的作品 则是止于剽窃
非常不一样的佩措尔德电影,游戏感的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