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快乐》剧情介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事胶着而残酷,不同阶层的人不断的卷入到战争的漩涡之中,徘徊在死亡的边缘。终于,平安夜来临。德国、法国和苏格兰军营宣布在圣诞之夜停战,相互约定度过一个和平安详的圣诞节。每个人都放下了手中的武器,手执蜡烛,互道“圣诞快乐”。应征入伍的德国男高音歌手斯普林克(本诺·福尔曼 Benno Fuehrmann饰)的女友安娜(黛安·克鲁格 Diane Kruger饰)在平安夜来看望他。士兵们被安娜柔美天籁的声音所深深温暖,苏格兰牧师(卡瑞·刘易斯 Gary Lewis饰)也吹响了风笛,划过寂静寒冷的雪夜,久久飘荡在战场上空。 影片根据1914年圣诞节前夕发生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本片荣获2006年第7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2006年第63届金球奖电影类-最佳外语片提名,2006年第31届恺撒奖最佳影片提名,2006年第19届欧洲电影奖...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在下一炷香狩猎行动今日的网漫双响炮美丽村官六兄妹新逃学威龙风之信请让我聆听你的歌鱼跃在花见时光追猎者宇宙战队九连者斯汀格章如果有荆棘银河宝贝我喜欢的妹妹但不是妹妹意能之下恋夏38℃我口袋里的女朋友健将联盟救世第二季我不是药神24小时:救赎狼的孩子雨和雪少女洛荷公路美人12金鸭血腥星期天疯狂希莉娅大江沉重安琪拉的圣诞心愿
《圣诞快乐》长篇影评
1 ) 《圣诞快乐》:朋友,我是杀死你的敌人
一、战争是臭的 战争是臭的。
通过银幕的再现与文字的形容,我们能看到战场上的血肉横飞、硝烟弥漫,能听到炮声轰鸣、厮杀喊叫。
但从来没人愿意重现那种气味。
当一切安静下来,等待下一次进攻的时候,半夜里躺在冰冷的战壕里,能闻到什么?
在1914年的佛兰德,那是血的气味,混杂着茅坑的臊臭,和来不及掩埋的尸体腐烂的味道。
炮弹把大地炸成了蜂窝,纵横着许多撕裂的口子,几次夜间突袭过后就足以把所经之地变成露天停尸场。
生石灰的怪味难以遮掩炮弹的呛味,混在一起更加刺鼻。
赶上雨季就有的瞧了,雨水积在坑里,把尸体泡得发胀,让你分不清楚是冰冷的饭菜本身难以下咽,还是空气中弥漫的毒气令人作呕。
埋尸体的时候稍微挖深一些,就会看到上次战争的遗体,这些层叠的死尸让浮在地面的积水充满了致命的病菌。
就更不用说虱子和老鼠了,战场让它们如沐甘霖,在整个国家都在遭到重创的时候,只有这两样生物繁殖得异常猖獗。
在这片土地上死亡也许不是最坏的事情,死后还有可能上天堂,活着就只能待在这满是泥浆,传播着肺炎、风湿和恐惧的地狱中。
可是,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的时候,没人能看到这些,不论是德国人还是英国人都陶醉于其中。
德国的小学生都会背诵《仇恨英国歌》,人们把诗哼成了遍布街头的流行小调,还煞有其事地给写这首蹩脚诗的人颁发了一枚勋章。
他们声嘶力竭的要这首诗传遍欧洲,让世界都知晓他们“只有一个敌人:英国”。
英国人的反击也毫不示弱,他们也宣称要打倒德国人,挖出他们的眼球,割掉他们的舌头。
今日回首总会发现当年干下的蠢事,但是人们总是会输给群情激昂的时代精神。
93位富有卓越才能的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在《对文化界的号召》上签了名,把歌德、贝多芬、康德等文化名人列入他们支持自己信念的口号中,用名誉担保战争的进行。
更有些适龄的艺术家虔诚地奔赴战场,以此丰富自己的艺术生活。
托马斯•曼也是支持战争的,为此差点和反战的哥哥绝交。
后来,他在持久的战争过程中才慢慢改变了之前的观点。
但是时隔几十年,战争再次在生活中高于一切,一战的批判与反省像过季的流行词汇,没人愿意提及,他们再次高喊“能为亲爱的祖国而战,能为我至今任卫士最高尚的一切而战,我感到骄傲”。
电影“圣诞快乐”(Joyeux Noël 2005)的历史背景是一战中比利时北部战场的伊珀尔战役。
4次战役让这里几乎被夷为平地,只剩墙基,英国先后共计50万军人为了守卫这个地方长眠于此。
这一切开始于什么,又怎么结束的,人们一直在讨论,在研究,光是有关战争为何开始的书籍就有7000多种。
不管最初是如何开始的,反正其中的仇恨肯定的是根深蒂固的。
电影一开始就能看到三个国家的孩子,站在黑板前,分别用母语背诵他们接受的“仇恨教育”:法国人念念不忘的是在普法战争中丢失的阿尔萨斯和洛林,都德的《最后一课》记录了这个开端;英国人则咬牙切齿的说德国人不是人,他们的女人与孩子都该死,这样其后代才不会贻害人间;德国人比较简单,他们的敌人只有英国一个。
英国在职业军人受到重大损失后,成立了业余军队,让充满了冒险精神的年轻人兴奋地走上战场。
影片中苏格兰教堂中的威廉和乔纳森兄弟便是其中的一分子。
这些学生在暑假期间踏上了战场,信心满满地以为秋季就能回来正常上课,却有30%的人再没回来,这个阵亡数字就刻在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历史中。
令社会震惊。
如果他们能听从肖伯纳的建议,也许就能避免大规模的战死,避免英国乡村贵族家庭断后的惨况。
肖伯纳在1941年8月,于《新政治家》周报上严肃建议“各支军队的士兵应该开枪打死它们的军官,然后回家去。
”这个“玩笑”显然没有逗乐英国官员,倒是让他们恨得牙痒痒,盘算着把他送上军事法庭。
在德国,更是举国上下都投入到战争的热情中,大批没毕业的学生虚报年龄,整个年级的去应征入伍,接受身体检查。
德国18到22岁小伙子的阵亡数字是37%。
无数家庭覆灭了,不论在英国、法国、比利时还是俄国、奥地利,新一代的人还未成长就走向了死亡。
不同于英国人的震惊,德国人更愿意将这种死亡塑造为伟大的献身。
军官们把士兵推向死亡,在他们的坟墓边说些不痛不痒的悼词,再由民族主义诗人在把这种牺牲美化成神话, 伊珀尔的第一次战役被一些德国人称为“儿童大屠杀”。
这里所说的并非是在二战集中营中那种,把成批的儿童送往毒气室的事情,而是将近10万刚来到前线的大学生,还未受过任何正规训练的学生们,就这么被爱国激情和军官的号令下,托着枪,大步迈进了死亡。
侥幸活下来的人,会慢慢发现战争和报纸上大肆宣扬的爱国精神渐行渐远,他们的生活只剩下杀人和被人杀。
最初看到死亡的冲击已经变得麻木,腐烂的尸体渐渐成为景观的一部分,战后的人甚至承认当初如果看到一个受伤的同伴被击毙,会暗自庆幸不用去冒险营救他了。
他们已经习惯了在铺满尸体的战场上前进和撤退。
至于打死伤员以免拖累行军这种灭绝人性的做法,有人承认,大多数参战国都否认,法国人则保持缄默。
与战后截然不同的态度相反,每个国家在战时的态度都惊人的一致——都在费尽心机的煽动仇恨。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德国人已经在英国生活多年,接到征召回国时,他们的邻居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敌人,除了各自为了国家卖命外,实在谈不上有什么深仇大恨。
为了让战士们充满斗志,英国政府到处树立德国蛮子嗜血成性的形象,德国人则宣传英国人如何虐杀已经求饶的士兵。
报刊基本被政府控制,发表的言论都得经过审批过滤,那些诉说战场条件艰苦,充满死亡恐惧的诗篇都被忽视(尽管在稿件中这占了绝大部分),登载的都是一些鼓励战争的空话。
每天在他们的命令下,几千人排着整齐的队伍去送死,当一次战役死得人越多,越容易被载入史册,他们的指挥官也会被记住书籍。
不少人就是因此获得的荣誉。
至一战结束,共计900多万人为战火献祭。
英国外交大臣艾德华•格雷爵士的预言成真:“全欧洲上空的灯火已经熄灭,在我们有生之年再也看不见它们会重新照亮。
” 二、平安夜的奇迹 自从1914年8月开战仅仅四个月后,已经没有人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了。
他们也没有力气和激情唱了,剩下的全部力气用来求得生存,无休止的突击让他们筋疲力尽。
西线的无人区是被上帝抛弃的土地。
没有任何事情值得寄予希望,也没有任何值得感恩的东西。
法国少尉在战争日记中写道:“可怜的小爱神,你偏偏出生在今夜,那你怎么去爱人类啊?
” 英德两军都泡在各自的泥浆战壕中,之间相距不过百米,一同饱受巨型老鼠袭击和子弹横飞的恐惧。
那些老鼠从未像现在那样营养过剩,天天悠闲地啃噬成堆的死尸,大得和猎犬一样,连猫都会被它们撕碎了当点心。
曾经是锅炉制造工的亨利希•莱尔施写过一首诗,描述他每天都能看到一名死者,越看越觉得是自己的兄弟,后来他冒着枪林弹雨把这个陌生的伙伴埋葬了——“是我的眼睛看错了——我的心,你不会错的,每个死者都有一张兄弟的脸”。
充满讽刺的是,恰恰是死亡换来了人们的平等,不管是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还是比利时人,都躺在一起,不分官衔、国籍,像是阵亡的兄弟一样。
虽然很难从中预计之后即将发生的事情,但是曾有人说过“一个士兵从别的士兵中看到了自己,仇恨便消失了”。
当仇恨消失了,战争就失去了意义。
谁都没有预想到1914年12月24日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在经历了无数死亡后竟然能有奇迹发生,而战争打响后的第一个圣诞节竟是一个有关和平的奇迹之夜。
在战争史上很难再找到和这次的圣诞夜和平相类似的事情,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过。
刚开始只是一个男声在独唱“静静的夜”,忧伤肃穆的气氛在佛兰德地区扩散开,歌声融化了一扇扇被战争冰冻的心灵,解冻的河流澎湃而下,冲刷着干裂的大地,对面的英国士兵纷纷爬出战壕,而平日里他们连头都不敢冒出来一点,生怕被狙击手夺去性命。
他们用掌声点亮了寂静的夜,和平像几千年一遇的彗星拖着长长的金色尾巴冲向地面。
当最后一个音符隐去,英国士兵们大喊着“好!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他们吹起了风笛,和对面的歌声唱和,他们吹出一个调子,德国小伙子们这边就会传来相应的歌声。
他们说不同的语言,却在音乐的殿堂里交流无阻。
当早已经厌倦了子弹和炮声的轰鸣的人们,听到了音乐,就像着魔了一样,经过险滩的激流终于奔向了大海,麻木的灵魂再次被烫得发烧。
圣诞树整齐地排在德国战壕的边上,蜡烛在夜色里仿佛滴着雾水的金色玫瑰,装点在舞台的四周。
他们用信号弹代替了焰火,被赋予了理解与爱的夜晚让所有的事物都熠熠生辉。
歌声结束后,不同国家的人挤在无人区里,互相交换自己手里的礼物和食品。
罐头牛肉、葡萄布丁、烟、巧克力,对于吃腻了各自食物的士兵,能换换口味简直能比拟美食大餐。
当然法国人对示好的德国人还是充满戒备之心,毕竟受到多年的仇恨教育和大肆宣传后,德国蛮子的凶残形象还是很难一夜之间抹去的。
有些人不敢吃德国人递来的事物,得他们先吃一口才能放心。
很多德国士兵都会讲流利的英语,因为他们原本就住在英国,英国人在高中的时候也大多学过德语,而欧洲中学里普遍教授法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
他们低声提醒对方哪里有地雷,德国人知道英国人没有圣诞树,还主动要送给他们一棵。
有个士兵高兴地说:“我们是萨克森人,你们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两者均属于古代日耳曼人部落集团),为什么我们要互相开枪?
”这简单的逻辑算是道出了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心声,也应了中国那句古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他们在那个夜晚,交谈、大笑、演奏风笛、吹奏口琴,就像一次跨国的联谊会,经过这样的夜晚,没人愿意第二天再端起枪打这些新结识的朋友。
这里不是天堂,但是他们用努力维持和平,建造了一座属于他们的乐园。
于是,我们能看到他们在一起掩埋伙伴,一起默哀,一起踢球,交换礼物和地址,希望以后还能像朋友那样互寄明信片。
电影只能展现一个地区的和平,而1914年圣诞夜的和平是整个战线上的,上级无法制止这么大规模的运动。
一些英国士兵本想在圣诞夜唱几首歌,让德军放松警惕,就能“来个5次袭击”。
但是当他们唱起《夜晚,牧羊人照看着羊群》,意外地得到了德国人热情的歌声回应,气氛一下子变得友好起来,谁也不想打仗,他们相约“圣诞快乐,今天晚上我们不开枪”。
一个德国兵告诉他们自己十分想念自己远在伦敦的妻儿。
这些愉快地谈话持续了很久,促膝交谈比互相杀死对方要令人陶醉得多。
就算在平时也很难看到不同国家的陌生人之间,有这样融洽、友好的关系。
更难以想象的是他们在今天以前都是拚死相搏的敌人。
当走在一起,他们发现对方也都是和自己的一样的普通人,并非是什么凶蛮野兽,比起那些整天指挥他们去送死的军官,他们和眼前的敌人更加亲密。
曾经有一个比利时人想给家里寄信,但是家乡已经都被德军占领,于是他就把信扔给对面的德国人,让他们代寄。
没想到他们真的寄了,而且还带来了回信。
这是任何官方都不会报道的事迹,战争结束后才慢慢被人们发掘出来。
德军也有以杀人为乐,毫不理会“圣诞停战”这种事情。
二等兵阿道夫•希特勒就对此荒唐的停战表示极大的愤怒,强烈反德军和英军在无人区不开枪、共度圣诞。
他的伙伴没有理会他的抗议,认为他中毒太深,不可理喻。
还有一些英国人趁机向毫无防备的德国人开枪,当时就被上级训斥了,他还代表其下属向对方道歉,得到了接受。
破坏和平的事情也有不少,但都无法阻拦大部分人对和平的热切盼望。
停战期间,连麻雀都从四面八方飞了回来,自从开战以来,战士们还是第一次在战壕里看到老鼠以外的动物。
他们清理了无人区,填平了沟壑与弹坑,搭起了简陋的球门,往日作战的工具成了今日游戏的玩具。
美国历史学家斯坦利•温特劳布解释说:“足球是工人阶级的宗教信仰”,是这让他们有了除却上帝之外的同样的激情。
爱人总是比杀人更好。
1914年12月30日,当萨克森士兵们接到命令,“禁止搞和平活动”。
他们没有能力违抗,于是写了一张纸条给英国汉普郡士兵:“亲爱的伙伴们,我不得不告诉你们,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许和你们在外面见面了,但我们永远是你们的伙伴。
如果我们被迫开枪,我们会始终朝上面打的。
”谁都不会忘记,在圣诞夜,当德军恋恋不舍地走回自己的战壕时,英国小伙子们用风笛吹响了《友谊地久天长》。
三、希望永存 面对1914年的和平事件,各国的掌权者虽然措施不同,但是口径十分统一:“不允许”。
在德国,第一年的惩罚仅限于关禁闭和禁止升职,到了第二年,因为参与和平的人一旦被拉上军事法庭,就有可能面临监禁和死刑的判决。
第一年参加了和平活动的德军部队由态度强硬的普鲁士兵团代替,他们则被调往俄罗斯大草原,自此杳无音讯。
这样成千上万人参与的事情,很难保密,在几家英国的报纸头版都刊登了这一新闻,德国人则严令控制不让消息成为正式讨论的话题。
虽然每个国家都有战地记者,但是有关战争惨烈程度和伤亡士兵的照片一律不准外泄,报纸上刊登的都是一些批准过的图片,很久以后他们才能把真实的图片公诸于世。
后方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反战者和民族主义者拉开了阵势。
不过,再怎么讨论,他们都无法了解当时在水深火热中士兵们的处境。
哪怕是士兵的亲人也无法与他们沟通,他们回家探亲的时候都变得沉默寡言,郁郁寡欢。
他们觉得和不了解前线的人在一起,很痛苦。
有很多“被战争捣碎了的人”在医院接受几十次的手术,不断更换人造的肢体、器官,维持生命,他们与世隔绝,连他们的亲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处境。
英国做过一次试验,试验者中只有三分之一经历过战争的士兵才能过正常生活。
大多数的人患了“战争神经官能症”,这是一种心理上的疾病。
多数人终身都无法摆脱耳边的战火声,日日夜夜都忘不了战争的臭气,被炮弹炸碎的哀号,和伙伴惨死的景象。
影片中德国士兵尼古拉•斯布林克,参战前是国内有名的歌唱家。
他的妻子得到了德国皇帝的特别批准能在圣诞夜让他们团聚。
斯布林克并没有妻子预想中的快乐,他想回到战壕,和自己的兄弟们共渡圣诞。
他说:“你必须面对死亡,才能意识到光阴流逝如此之快”。
妻子不会理解,过去的四个月都发生了什么,她的丈夫永远都无法像原来那样过正常的生活。
在前线战区,每个人只有过去,没有将来。
最美好的梦是能看到以前平淡的日子。
人性在战士们的身上一点点消退着,这正是指挥官们乐于见到的事情。
这种状况发展到二战中被称为“命令紧急状态”,即士兵们只是按照上面的命令办事,是他们屠杀的工具。
许多人接受审判时,认为自己杀人没有罪,只是服从命令。
统治者们为了让战士们更好的去战斗,消除所谓的同情心,制定了一套所谓的战争逻辑:“地狱始终在别人那里”,努力让自己的杀人行为变得正义。
在一战中,越往后,情况越惨烈,他们每天都在公开践踏日内瓦公约,杀死战俘和伤员,无数战士不是死于枪炮,而是死于无人救助。
许多人变得野蛮了,但还有一些人还在抵抗,还在坚持骑士精神。
即使在1915年,和平运动遭到空前抵制的时候,还有人在圣诞夜走出战壕,唱起歌。
当时所有人看着那个站起来的德国士兵都惊呆了,但是对面的人没有开火,而是等待他把歌唱完。
和平只是一小会儿,却仍不断呼唤人们的心灵。
士兵们还在写诗,他们没有仇恨,“在吞吃尸体的索姆河畔,我就在你的对岸,任何地方,我都在你对面,你却不知道!
敌人挨着敌人,人挨着人,躯体挨着躯体,温暖又紧密”。
最终一战以德国的失败告终。
比利时从1927年开放了“梅南门”,每晚8点钟,交通中断,车辆全部绕行。
号手在凯旋门下吹响军人葬礼号,仪式将近10分钟,纪念曾经战死在这里的士兵们。
这个仪式延续至今,只有1940年至1944年在德军占领下没有进行。
每晚都有人等在凯旋门下默哀。
“太阳纵然会落山,明早我们还会纪念他们”(《献给阵亡者》劳伦斯•比尼恩)。
如果说如此惨痛的结果带给过世界教训,那么应该是在二战开始时,那些曾经的幸存者,曾经热血沸腾地奔赴一战战场的士兵们,拉着自己的后辈走上街道,举起了反战的大牌。
之后美国还发动过几次战争,都很少有国家愿意参与其中。
在电影的结尾,那些德军战士坐在送往俄罗斯草原的列车上。
长官踩碎了他们的口琴,他们就哼唱着曾经属于圣诞夜的歌曲。
战争能吞噬生命,却无法吞噬他们渴望和平,渴望友谊,渴望爱的心。
转载请注明作者:九尾黑猫 http://www.mtime.com/my/LadyInSatin/blog/1528172/
2 ) 人:扁平的符号?还是鲜活的生命?--电影《圣诞快乐》
圣诞的前夕,想送给自己一个礼物。
挑了一部很早就想看的电影《圣诞快乐》,克里斯蒂安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1914年的一战前线,对峙着苏格兰、德国和法国的三支军队。
三方的战壕就在各自的鼻子底下,前面是躺着尸首的冰冷战场。
平安夜的晚上,响起了苏格兰的风笛,音乐可从不吝啬,她跨过战壕,在每个人的心头泛起丝丝涟漪。
一位本是男高音歌唱家的德国士官,和着对方战壕的风笛,手执圣诞树勇敢地走出战壕,唱起了著名的圣歌《平安夜,圣善夜》,那一刻我想每个战士的脑海中都会浮现一个温暖的画- - 家:无论是包着刚出生的孩子,还是和母亲一起煮咖啡。
不可思议的场景出现了。
徘徊于饥饿,严寒和死亡之间的士兵们在圣诞歌声的召唤下,纷纷走出战壕。
他们放下了枪,相互握手、拿出自己的巧克力和香烟,把妻子的照片递给“敌人”看。
那一刻没有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只有活生生的“人”。
三方的军官商定,私下决定停战一个晚上,他们一起坐在曾经相互杀戮的疆场,由苏格兰牧师主持了一场弥撒。
第二天,他们再次商议,将各自的阵亡士兵领回,为他们举行了集体葬礼。
因为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一样有权力享受他们的圣诞节。
士兵们一起喝酒、踢足球、玩扑克,渐渐发现一直仇恨的敌人,如此有血有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妻儿老小,每个人都有一段有趣的经历,每个人都有个不错的职业,每个人仿佛都曾活在自己的身边。
一些人给新朋友留下住址,邀请他战争结束后来自己家做客,或一起去某个酒吧喝酒。
战场上的流浪猫成了两边士兵共同的朋友,圣诞树成了召唤和平的橄榄枝。
三位军官继续通敌,每当某一方的后方要开炮,他们就通知其他一方,到自己的战壕来躲避。
就这样他们都活了下来,如果没有平安夜,如果没有那首圣歌,他们也许已经各自倒在战壕里血肉模糊。
他们纷纷写信给家人,分享这个夜晚的快乐,信被上级扣了下来,定下罪名—“叛国罪”!
这就是宏大的国家和战争在“芦苇的个人”面前的“正义”嘴脸。
人到底是扁平的符号?
还是鲜活的生命?
在他们那里你就是个拉美特立式的机器,是个雷锋式的螺丝钉。
就在你向枪膛里装上子弹准备冲锋陷阵的时候,你自己却成了国家某个领袖枪膛里的子弹,你的子弹不知埋在哪具尸体中,你自己也不知埋在哪抛泥土里。
我们总是极端地爱着某个个人(领袖、舵手)同时粗糙地爱着某个群体(人民、弱势群体),从来没有想着去爱身边每个鲜活的生命!
我们习惯把擦肩而过的人看做一个符号,就像路过一堵墙或一棵树,甚至有时我们也情不自禁地把身边的家人、朋友和同学开成一个干瘪的符号。
所以当我们来到战场上,对面的敌人就是些十恶不赦的屠夫,就是些禽兽,不杀不足以平己愤。
然而没想到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来自一个温馨的家,也有自己的故事,也憧憬着一些什么!
我们或许没有想过:战壕可以用来栖身,可以用来挡子弹,可是永远挡不住恐惧!
你前面的空地可以是战场,但也可以是舞台,也可以是足球场,甚至可以是教堂!
就这样我们死在彼此“没有仇恨的仇恨里”,我们倒在战场上连一个名字都没留下。
韦伯说国家是对暴力的合法垄断。
而我们却不自觉地成了被垄断的暴力本身!
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当归为每个个体的幸福!
国家为什么怕私人的东西?
因为那些战士的信上,每一字渗透着对战争的反思和对生命本体的关怀!
因为正如《一九八四》中说“做爱就是革命”!
因为如果给我一个灵魂,我的灵魂深处就会闹革命!
电影中的场景在我看来是不可复制的,因为有一种东西在衰微—“信仰”。
从博弈论的角度观之,战争三方处于不完全信息重复博弈状态,三方舍弃了囚徒困境下的“纳什均衡”而选择了“帕累托最优”,均衡的达成需要一种罗尔斯所谓的“交叠共识”。
而这种交叠共识在今天已经恍惚了,一战留给我们更多记忆的是“凡尔登绞肉机”。
想起《太极旗飘扬》的开头韩国人在旧时战场上亲扫遗骨,用DNA和骨像合成技术坚定每个战士的身份。
又想起《集结号》,那47个被视为失踪者的兄弟,最后得到的只是可怜的荣誉称号。
但我们要记住:国家发行“荣誉称号”的边际成本为零,你却为了拿一个儿子的生命、一个丈夫的生命、一个父亲的生命去换,值吗?
荣誉多了也会通胀也会贬值!
何况在另一个国家和另一个朝代可不好使!
谷子地喊“吃饺子还是吃子弹”,这是一种强势下的劝降。
和《圣诞快乐》中大家平等地坐下来祷告是不同的。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中原写给自己的圣诞节
3 ) 无题
看过一本英国人写的圣.埃克苏佩里的传记《小王子的爱与死》,里面写到圣.埃克苏佩里的家族神甫一次在一战的战场上,就是象电影中的晚上。
神甫唱起了圣哥,后来对面战壕里的德国神甫用德语也唱起了圣哥。
看书的那一会儿,眼眶着实热了一会。
想象和平友谊……电影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一个基于战争真实的场景的故事。
不过不知电影后面部分是否属实,应该夸张了吧。
电影里就一个女角,标准的金发女郎(似乎更像丹麦的那种)。
电影戏剧的色彩挺浓。
4 ) 人性
影片的结尾尤其感人。
因为和敌人友好和平地共度圣诞而被换防的德军部队坐在闷罐子车皮里,突然门开了,所有军官士兵起立立正,显然进来的是高级别军官 -- 尽管心情沮丧,意志消沉 -- 但没有忘记纪律。
等待他们的是严酷的俄国前线。
丹尼尔·布鲁赫略显稚气的脸庞(也许是我对他在列宁再见里的表演印象太深了)现在蓄起了大胡子,在受到上级军官的严厉斥责后痛苦地把头低下。
在这一瞬间,他的眼神透露出的是一个经历过血雨腥风洗礼的战斗部队连级军官对于那些坐在后方的大喊大叫指挥的高级军官所发出的严厉斥责的无奈、屈辱和绝望。
士兵们哼起了I'm dreaming of home,一首非常优美动听的圣诞歌曲,在这种悲戚的环境下显得尤其打动人心。
列车缓缓开动,载着他们驶向一个更加残酷的战场。
本片是超越一切文化、种族和意识形态的反战影片。
5 ) 电影原声分析
原声由Philippe Rombi制作。
神奇的音乐的力量克服战争的残酷让敌我走到了一起,这大概也是电影的另一个主题吧。
恢弘的Ouverture,开场就能感受到。
此外,欧洲土地的辽阔感,历史的凝重感(La guerre),还有抒情的温馨感(Hymne des fraternisés)汇聚在一起,可以毫不客气的说,这张原声和LOTR有得一拼!
全苏格兰风笛演奏的“Enterrement des soldats”,主题童声版“Hymne Des Fraternisé -I'm Dreaming Of Home”在片尾出现,非常好听。
“Invitations -I'm Dreaming Of Home-”在军鼓的伴奏下,抒情管乐和人声带我们来到那片土地,之后悠扬的苏格兰风笛倾情而出,男声的低声吟唱带出主题曲。
原声中还收录了片中男女高音演唱的插曲,"Ave Maria" "Bist du bei mir","Stille Nacht"是德语版的Silent Night。
1. Ave Maria 2. Overture 3. Fraternizers' Hymn (piano) 4. Anna and Nikolaus5. War6. Soldiers' Burial7. Bist du bei mir 8. Silent Night 9. Jonathan's Letter 10. Ponchel's Memories 11. The Football Match 12. The Bishop's Sermon13. The Soldier's Mail14. War Adagio15. The Absence Theme16. Fraternizers' Hymn: 'I'm Dreaming Of Home'17. Adeste Fideles 18. Invitations: 'I'm Dreaming Of Home'19. Anna and Nikolaus20. Aria for Violin and Orchestra21. Fraternizers' Hymn (Murmurs and vocalises)
6 ) 小记
这种战争中看似不可思议的冲突就恰好显示了战争灭绝人性开头用三个小孩口中诉说这个创意真的是棒极了 小孩子不可能了解它们口中的含义 明显是别人教的 就像普通的民众们 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他们被国家主义所裹挟洗脑 这个战争不是为了自卫 而是因为欲望战争很常见的是大多数士兵都不想打仗 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 都渴望快快乐乐的生活 “这是老人的游戏却让年轻人牺牲” 他们无非都是政治的牺牲品无论哪个国家的牧师用拉丁文——德英法语的母语布道的时候 真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布道之一 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们都是一样的 坚信平等与爱 虽然我不相信宗教 但是其和平的理念和我的认知是一致的 你可以毁掉我的乐器但是无法毁掉我的歌声 无论多么惨烈的战争 都无法毁掉人性所守护的美好国家主义之下隐藏的是死亡 憎恶 痛苦与爱的反面maybe just be together maybe just forget warmaybe,but war doeant forget us
7 ) 戰場上的溫暖
當軍人走出來慶祝聖誕的一幕,全場觀眾都笑了。
這不是軍人應該做的事,他們做了,所以觀眾才笑吧。
但這是一個人應該做的事——佳節當然要慶祝一番。
每逢佳節倍思親,更何況在戰場孤零零軍人?
他們和「敵人」同是天涯淪落人,大家都掛念家人,緬懷和平時的日子。
德國軍官的改變最明顯。
他的改變是最明顯的。
他外表冷酷,起初不喜歡歌唱家,對殺敵的人加以贊賞,想阻止歌唱家出去。
後來他和其他國家的軍官聊天,開始談自己的妻子,甚至叫「敵人」躲避轟炸……他被人與人之間的溫暖溶化了!
在戰爭之中,這些溶化顯得特別強。
邪的不是敵軍,卻是在上面的將領,還有鼓勵殺人的「神父」。
最後雖然看不到「邪不勝正」的道理,但看到軍人忠於自己,他們想要的不是戰爭,不是徽章,而是和平與關懷。
上級軍官說的叛國罪名,值得在乎嗎?
懦夫是沒有勇氣去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的人,他們不是。
8 )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的历史书上习惯性的采用帝国主义狗咬狗的论述方式,也是因为这场战争给予了东亚文明在列强瓜分下喘息的机会,我们甚至感到庆幸,以至于对它不愿意了解太多。
正如西方人对于抗日战争中我国所受到的牺牲相对陌生一样。
当十余年的战争动员和爱国主义教育将数百万普通人推进暗无天日的堑壕时,王冠的光泽在普通人心中已然黯淡。
1914年的圣诞前夜,敌我双方的士兵走出堑壕,共度佳节,这既是人类对和平美好的渴望,也是整个西方社会对于社会普通人的个体独立性一次认真的思考。
当东线的灰色“牲口”不再想要做牲口的时,他们成为了十月革命最重要的拥护者。
当德国公海舰队被下令出海决战无敌的英国皇家海军时,愤怒的基尔水兵调转了枪口。
当伦敦、巴黎、柏林的命令传达到数百公里长的堑壕中,得到的是无人回应和士兵愤怒的目光时,可耻的人们不得不结束这场可耻的战争。
《圣诞快乐》这部电影讲了个温暖而悲伤的故事,也诉说了如今西方社会珍惜的所在如何而来。
这不是因为物质充盈而造成的富贵病,而是一次血与泪的文明经验。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
9 ) 真正的文艺片
《圣诞快乐》是一部由法国导演克里斯蒂安·卡里翁导演的战争片,它讲述了一战时德国、苏格兰、法国三方士兵在圣诞夜举手言和的感人事件。
本片从结构上讲,更像是一部散文诗的结构,以战争主线和男歌唱家人物副线来推动叙事。
而这两条线的叙事并不像其他战争片那样标准,它们的节点设置更为随心所欲一点,或者说更偏情感一点。
这体现在战争主线中三方言和时并无过大的情节转折和波动,而是情感氛围发展到了最浓郁的地方,然后理所应当地言和了。
这种极度不理性的行为是文艺片中才会表现出来的,不过在本片中,它以一种战争硝烟下被包裹住的美好而直勾勾地表现了出来。
水到渠成、理所应当,这就是本片叙事结构的原理和精华。
所以在影片后半部分,男歌唱家为了逃离战争而投降、德军长官私下帮法军长官送信、苏格兰牧师为所有死者祷告,这些看起来荒诞的部分反而变得合理起来。
因为观众已经开始接受了这种情感设定。
总的来说,我更愿说《圣诞快乐》就是一部真正的文艺片。
10 ) Joyeux Noël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这几年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出现了这样一种可爱的电影,也许可以叫做“欧洲电影”,典型的代表就是The Spanish Apartment(欧式布丁、西班牙公寓)极其续集Russian Dolls(俄罗斯娃娃),还有去年代表法国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这部《圣诞快乐》。
这种电影不是找欧洲几国的演员合拍或者穿越几国取景那么的简单,而是在电影里通过人物和故事体现着欧洲各国文化历史的碰撞和随着时代大潮的逐渐融合,一个角色代表着一种文化,在角色的碰撞之中体现着各国文化的不同,但是却因为相近的那片土地的联合而求同存异,并且渐渐融合出一种欧洲共同的文化和精神。
与《西班牙公寓》的当代年青人背景共同生活的主题不同,《圣诞快乐》讲的是过去,一站的过去,但是这段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看起来都有些荒谬的属于过去的经历却深刻的预见了欧洲的未来。
影片只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靠近法国边境的那么一小块战场,这里英国和法国的军队对抗着德国的入侵,三足鼎立的战事一直延续到那一年圣诞前夜,英军阵营有着一个悲天悯人的苏格兰教士,法国阵营的上尉有着一个怀孕并且濒临生产的德国妻子,而德国阵营有着一对原本是歌唱家却不得不参军的恋人。
于是在这个每个人都被思乡的情绪主宰的夜晚,苏格兰风笛和歌唱家天籁般的声音敲开了自己和敌人的心门,于是我们便看到了根本不属于战场的荒诞一幕,在基督诞生的前夜,这块雪色覆盖的战场上,三方将领握手决定今夜停火,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放下了手中的武器走到了一起,共享香槟和巧克力,分享着彼此妻儿亲人的照片,一起做子夜弥撒,齐声低吟“阿门”。
美好的像一个梦,让人简直不能相信它是真实发生过的一起。
可是它的确是真实的,别相信他们告诉你的,没有战争是正义的,没有战争是属于人民的,它们永远都是独裁者欲望的膨胀,它们永远都是为了龌龊利益的斗争,可是这些利益,永远不属于我们。
可是,还活着的人,都是有心的,所以即使圣诞夜已经过去了,经历了美好的人们还怎么能够向这些新结识的朋友端起刺刀和扣动扳机?
于是便有了圣诞节早上三方将领一起的早茶,一起商量的交换尸体、足球赛等活动,甚至在炮弹袭击之前邀请敌人来自己的战壕避难,这都是真实的啊,我掩面而笑,却有着落泪的冲动。
这是在语言不通下属于音乐的力量,它激发出战场上最真挚的人性,却在真正浑身血腥的战争发动者那里起不到一点作用,因为他们早已经丧失了作为人的资格。
于是教士被遣送回苏格兰,法国上尉被调到另外一个战场,而德国将领和他的部属被送上去苏联的死亡列车,可是当火车渐行渐远,他们的歌声却从车厢缓缓的飘出来,这让我噙着泪水但是却微笑了出来,这是结局,但是他们的歌声他们的感动永远不会消失。
这是我看到的最“可爱”的战争片,不是讽刺的搞笑,不是刻意的煽情,不是场面的恢弘,却是最真实的最动人的可爱,想到去年金球奖它和《无极》角逐一个奖项,我真替《圣诞快乐》觉得不齿。
它的演员阵容虽然也可谓强大,苏格兰教士是《Billy Elliot》中的父亲,法国上尉是《Love Me If You Dare》的男一号,德军将领更是《Goodbye Lenin!》中的主演Alex以及女歌唱家的扮演者是《Troy》中的Helen(不得不说,她选Helen这个角色简直是一失足就……|||),不是好莱坞常见的明星,却都是各国本土演员的中坚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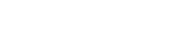




















共同的文化、大差不差的信仰打破了本国上层人刻意制造的民族冲突的谎言,但最具有说服力的,是各方前线的士兵都是各自国家的底层人民,他们在战场上相似的境遇,以及在本国受到上层人的剥削和驱使去充当炮灰,使得他们之间可以高度共情,这才是上层人最害怕的,他们不一定害怕输掉战争,但是一定害怕敌对双方士兵联欢,因为当他们发现彼此境遇一样结成同盟后,这仗就要打回统治阶级自己头上了。影片中这对情侣真的是败笔,虽然两位都是歌唱家的设定可以很快推动战场上唱歌这一核心剧情,但是之后他们的烦恼和最后逃到法国的剧情真的很没必要,甚至是打破这种良好局面的隐患。啊好多电影都是因为硬加感情线进去然后就成了败笔的啊。
手段太拙劣,人物太单薄,美好经不起这样打断筑高台,因为看着就摇摇欲坠。也没有什么信息密度,主打的就是一个概念,欸,就是玩儿。
“国家知道我们受的苦吗!?”
有点失望,过度美化人性了。干净整洁得不能再干净的战场,甚至尸体都没出现几具!
1.25 Humanity.
细细一想,人类用了一个世纪才草草解决了个人与国家的矛盾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个人与资本的问题了。
其实是为了看Diane和Guillaume才看的
非常好看
很温情的一部战争片
可能因为以前就听过了这个故事,所以降低了感染力。欧洲人真是钟爱一战题材
温暖🎄
整部片子给我一种滑稽感,就像吵架气到眼球充血,最后忘了为何而吵。
2015.7.30 0:07
纵使战争布满浓重的阴霾,也挡不住人性光辉的闪耀
这片真没法说了,烂透了的通俗电影,故事本身是改编自一战时敌对双方圣诞节停战并小联欢的史实,这件事就是全片的唯一重点了,之前铺垫的部分毫无看点,僵尸一样缓慢的剧情只是为了杀时间,推进到最后的戏而已,基本和毫无看点的A片没什么区别——一个你知道这是A片罢了,一个你知道要讲战场联欢罢了。
毫无意义的暴力 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出现了一种可爱的电影
忘不了那风笛响起的一刻。
这种故事必须是由真实事件改编。因为它的“离奇”程度超越了观众的对于特定情景下的逻辑预期!雷诺阿的大幻影还只是矛盾烈度相对和缓的战俘营之谊,本片竟然是一战三方浴血沙场间歇欢度了一场有女高音战地助兴的温馨圣诞!完成度颇高,某些情景也颇为感动和引人深思,但就是觉得整起事件……不可思议。
终究是个很难拍坏的题材,不过,“圣诞快乐,先生们!今晚德国佬那边没有动静!”
有我喜欢的演员们,但感觉情节有点太散了,所以看的过半了才分清楚三个国家的军队。